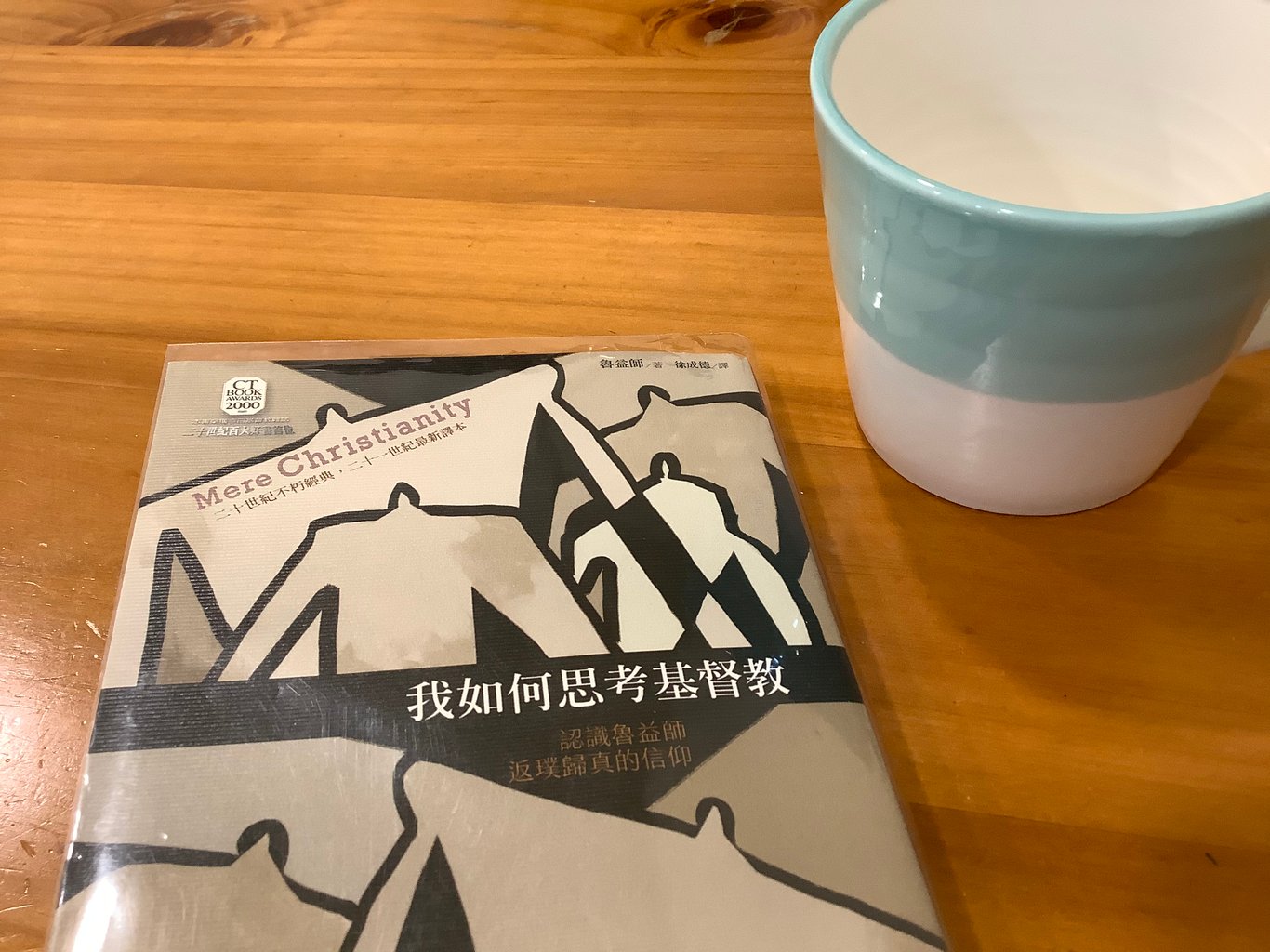佛洛伊德與魯益師的[兩種上帝]
這本書的作者尼可里是哈佛醫學院的精神科教授,[兩種上帝],比較的是現代心理學的巨擘佛洛伊德,和寫下[納尼亞傳奇]的文學與思想大師的魯益師,兩種不同對上帝的看法。可以說這本書是心理學與信仰的大比拚。就像第一章的標題所寫的---[我們應該相信什麼?]
對佛洛伊德來說,宗教是[普世的強迫性精神官能症],信徒的跪地、祈禱、手劃十字的模樣,都只不過是這種病症的表現。宗教是人所創造的心靈麻藥,所謂屬神的智慧只不過是人的智慧,神學的奧祕就存在人類學中。佛洛依德認為,宗教是人在長大以後,內心仍然是一個幼童,渴求一個更強大的力量的保護,因此想像出類似父母的存在,呼之為神。”幼年時,依靠父母為我們處理疑難雜症的慣性,導致成年後,面對無助時依然沿襲這種尋求庇蔭的特質,正是宗教的起源。在他看來,神並沒有依照他的形象創造人,相反的,是人依照自己父母的形象,創造了神。
許多人的信仰終其一生,或許一直停留在這種孩子式的自我中心中,認為神應該按照他們的需求與喜好行事,對他們來說,神應該滿足他們自己對良善的期待,對公義的期待,這樣他才是一位[好神],如果這位神並沒有像他所想的回應他的需求,那麼他就會像對父母失望一樣,對神感到失望。如果他所信仰的,自始至終不過是一位[滿足自己需要]的神,那麼他的確是參與在佛洛伊德所說的[造神的活動]中。
魯益師所描繪的上帝卻並非如此,他並不會因為我們的祈禱、奉獻、或敬虔的行為而被[操控],這位神祝福我們,是因為他愛我們,他愛我們,也不是因為我們本質上值得去愛,而是因為神的本質就是愛。
對魯益師來說,人無法以靠自己的能力[認識]神,因為我們沒有能力認識比自己更大的事物。有限無法認識無限,短暫無法理解永恆,被造物無法理解創造主。關於人類喜歡提出的那個問題:[如果真的有一位創造主,我們為什麼被創造呢?]事實是如果我們真的明白自己被造物的身分,就應該至少明白,這個問題即使被回答了,答案也不是我們能理解的。只有創造主明白。
佛洛伊德說:人渴望有神,所以造了一個。他說,人渴望有神,這是不錯的。人只要活著就會漸漸發現一件奇怪的事----在我們裡面,有一個渴望在尋求這個世界沒有的東西。魯益師對這件事的答案是:[如果我發現自己有個慾望在這世上無法得到滿足,最合適的解釋就是,我是為另一個世界而造的。]
那個無法解釋的[鄉愁]究竟從何而來?我們感覺到裡面有一個懷念的、渴望回去的地方,但是不管在世上的何處,就是無法讓我們感覺到自己真正找到了歸屬,我們為這個幻想中的國度取了許多名字:烏托邦、樂園、天堂……..而我們究竟要做什麼才能回到那裏去?苦修?爭戰?要打敗什麼?要擁有什麼才能歸回?
那些只在世上尋找樂園的人,所能找著的滿足是如此短暫和空虛,而那些希望透過今生的犧牲與禁慾,換取幻想中富足的人,又是否有真正的安息呢?
佛洛伊德的[理性至上]的信念曾經無比吸引我。比起神秘的宗教,理性似乎更容易仰賴,[至少理性不會騙我],我是這樣想的。我和佛洛伊德一起幻想過:[我們對未來所懷抱最美好的願景,就是有朝一日看到理智與科學的精神,還有理性,終能在人類心中建立無上的權威。]
這個[理性能帶來更美好的世界]的想法,在二十世紀遭受了重大的考驗。佛洛伊德逝世於1939年,在他為逃離納粹,從德國流亡到英國後不久。當時二次大戰才剛爆發,佛洛伊德還來不及看到許多大屠殺的發生,來不及看見原子彈事件,來不及看完這場有七千多萬人失去性命,人類歷史上死傷人數最多的戰爭。如果他能夠看見這些,是否會修正理性至上主義會帶來更美好的世界的想法?如今我們至少能夠謙卑地承認,理性未必能解決人類社會遇到的所有衝突,一個理性的人也未必是一個更好的人。人類在尋求未來的生存之路時,所需要的不只是單單高舉理性,我們還需要其他的什麼東西。
魯益師說,理性至上主義,事實上是傲慢至上主義。我們自以為的理性可能是盲目的,只是讓自己更容易陷入在狹隘的看法與眼光中。這個世界上有一種危險,是將自己認為對的事物,賦予宗教的神聖不可侵犯性 ; 這個世界上最可怕的想法,莫過於認為自己的想法就是絕對真理。那些出於自利而起的衝突有其停損點,只要衝突帶來的危害大過於所爭奪的利益,衝突就會自然停止。但那些打著正義旗幟的戰役,卻有可能來難以想像的文明世界的毀壞。因為一個人會為了自己認為對的事物,付出沒有上限的代價。
佛洛伊德說,人類社會的道德規範(善惡的分別),[如果能將神排除在外,安分的承認它們源起於人,那麼,對人類絕對有益。]我相信佛洛伊德是指著那些錯誤地被絕對化的道德規範來說的。如果觀察人類的歷史,會發現對善惡的看法,有一個部分會隨著每個時代而有所不同。耶穌在他的那個時代,也曾經被虔誠的宗教人士,指責為貪食好酒的人。他破壞了許多當時的人以為神聖的宗教律法,例如在安息日不可工作。但是,一個奉公守法的人是否就是好人呢?我們大多數人,應該在內心都不難認定自己是一個[好人]。至少我們沒有違反國家的法律,並沒有被關到監獄裡,被貼上罪犯的標籤。即使偶而會收到交通罰單,那只是[運氣不好],不代表我們比別人壞。我們說謊,但是大多數人都說謊。我們自私、但有誰不是呢?如果我上不了天堂,那麼周圍的人就沒有人上的了天堂。沒有人去的了的天堂,就等於不存在。
認為自己是一個好人並不困難,只要大致上奉公守法,就可以毫不愧疚地認為自己是一個好人。更何況,我們還可以很輕易的就認為自己比別人更好一點。這個想法使我們愉快,一點也不懷疑這個[比別人好]的想法,很有可能就是從我們裡面那個最頑強的罪性來的。
佛洛伊德說,[罪惡感是自我和超我之間一種緊繃的狀態。]並視之為一種應該除去的不健康因子。基督教信仰中的[悔改]和罪惡感不同,悔改需要某種程度的放下自我才能做到。罪惡感則是自我與超我之間永無止息的爭鬥,有時候自我強一點,自我感覺良好,有時候超我強一點,就陷入自我批判的罪惡感中,但是這兩者,其實都是自我的展現。
悔改,是我們放下這個自孩童時就緊緊抓住的自我。這件事並不容易,魯益師說的好:[要放棄多年來受到我們恣意侵占且不斷膨脹的自我意識,肯定令人生不如死。]因為這是我們唯一熟悉,幾乎也是我們以為自己唯一擁有的東西。就像那些勵志的小說或電影會告訴你的,要相信自己!找到自己!忠於自己!這些字句使人情緒激動,內心卻難以掩飾茫然。如果[自己]是我唯一所有可以倚靠的,那麼,誰來告訴我,這個[自己]到底是什麼?我要如何找到它呢?
對我們存在最大的威脅,並不在於外在的壓制與誤解。與什麼爭鬥是簡單的,知道是為了保護什麼而爭鬥才是困難的。成為一個自我的人,不代表就得到自由。一個滿足所有自我慾望的人,也不代表他是自由的,因為他仍然是被內在無法控制的慾望所驅使著。
原來悔改並不是像我們想的,是痛改前非,努力改過,悔改是承認那個我們以為自己唯一能仰賴的自我病了,需要醫生。就像魯益師所說的,[一個有點壞的人會知道自己不是非常好;然而一個從頭壞到腳的人,卻會覺得自己還不錯。]悔改是承認我們擁有的其實是一個敗壞的自我,而以敗壞的自我不可能明白什麼是真正的良善。
當我們更認識神,就會明白這個世界上只存在一種良善,就是神的良善。我們有軟弱,但是沒有關係,他是良善的。我們自己的敗壞並不使我們絕望,因為祂的良善能使我們充滿盼望。
在這個世界上,我們可以努力做一個循規蹈矩的好人,不會壞到哪裡去。但是我們若不悔改,就無法認識神的良善,也無法得到因祂的良善所帶來的盼望。
悔改也是不再用自己的想法和經驗來認識神、定義神。有一件事佛洛伊德是對的,人對神的認識的企圖,受自身與父母之間關係的影響至深。一個人有缺席的父親,對他來說,神也是遙遠的存在,如果一個人輕視自己的父母,他也會論斷神同樣無能,如果一個人曾經被父母拒絕,在他心裡也會對神有相同的恐懼,那就是有一天,在什麼時刻,神也會因為他的表現不如預期而放棄他。
我們對神的[想像],受限於我們在世上所曾經歷過的,與父母之間的互動關係。但假設一個人從來沒有過這種關係的連結,他要認識了解神又會是如何的困難呢?
在不完美的親子關係中想像神,至少能得到零星的碎片,作為材料去拼湊這一位神的形象。在愛情裡、在友誼裡、在施捨、服務與給予裡,在這些我們在世上可以經歷的關係當中,或許都隱藏著這樣的斷片材料,是某種完全的事物的影子,好叫有限的我們,得以想像無限的存在。
神的存在不是建立在論理邏輯中,因此我們永遠不可能以理性,去證明神的存在,或去否定神的存在。魯益師說,最容易認識神的處所,是在我們的內心。
現代人所感受到的無法解決的衝突與痛苦,或許是因為在理性上否定神的存在的緣故。我們被教導要相信科學,相信實證,相信能夠驗證的共同能夠感知的世界。為了不要被認為是一個愚蠢的人,我們對神避而不談,假裝他不存在。但內心我們知道他存在,這是被放置在我們靈魂當中最深切的呼求。因為我們原本就是為了這份關係而造的。我們是為了愛而造。這份關係在對我們說:我愛你。沒有這份愛,若沒有回到這個關係當中,我們內心永遠都有著孤兒的飄泊感,身分的悵然若失。我們會像一個患了失憶症的人,老是在[忘記了那最重要的一件事]的焦躁裡。
許多人為了尋求心理的健康而來到教會,某種程度宗教情懷的滿足,的確能為心靈帶來安舒和慰藉,但這宗教情懷所滿足的,仍然是那個生了病的自我。耶穌所傳的福音說:天國近了,你們要悔改,不是因為天國會帶來審判,而是若不悔改,我們看不見天國,也進不了天國。若不承認我們病得連自己都不知道自己需要什麼,我們無法看見耶穌所帶來的美好。天國的美好,實在是太好了,以至於以我們有限的想像無法看見,更無法活在其中。
神並非為了人的需要而存在,相反的,是人為了神的需要而存在。我們被造的目的,是為了滿足神的渴望、神的需要。神的渴望就是愛。這並不是說他是一個缺乏愛,需要我們給予愛的對象。神渴望愛我們,最類似於這渴望的感受,或許是一個母親對孩子的愛。若沒有這樣的對象,神的心無法被滿足。神迫切地想找回他的孩子,好使他能夠愛他們。
人罪性的自我會這樣說 : 神為什麼不滿足我的需要?他不是愛我嗎?就像一個小孩子懷疑父母對他的愛,因為他們不肯滿足他的期待。但是健康的父母給孩子的不會都是他們所期待的,更多其實是孩子真正需要的。我們就像孩子一樣,對於自己真正需要的事物一無所知。孩子需要父母,才能健康的成長。人需要神,給予他甚至不知道自己需要的幫助。
人罪性的自我會這樣說 : 我只要做了神要求我做的事,換句話說我只要做了[對的事],神就會愛我,至少不會懲罰我。這樣想的人會做出種種的努力,掙扎地與自己的自私的本性爭鬥,但是他們不管怎麼努力,仍然是活在自己所想像出來的,神有條件的愛當中。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比神更知道,什麼是值得被愛的。
而我們需要從罪性的自我中悔改,承認自己對神的愛一無所知。他的愛不是我們可以瞭解,也不是我們可以操弄的。他的愛不像我們所想像的那麼渺小、那麼薄弱,會因為我們的軟弱而被冒犯。神的愛遠遠比我們所想像的要廣大的多、堅強的多。聖經上說,神的愛長闊高深。比我們的生命更長,比我們的罪性還深。我們需要從自己對愛有限的想像中悔改,神的愛遠遠超過父母的愛,超過任何人與人之間的愛,因為這不是兩個被造物之間的愛,而是創造者對被造物的愛。
魯益師說,我們的角色始終都是[承受者]。想要感受上帝真實的,而非自己所想像的愛,需要完全的臣服。降伏是我們在神的面前唯一的姿態。敬拜,不是因為神需要尊榮,而是那是我們的位置。我們在神的面前無能為力,也沒有任何討價還價的空間,我們只能試著接受,他無止無盡、長闊高深的愛。
“神的命令聽在我們天生的耳裡,最像暴君,而非愛人,其實是在引領我們走一條我們若真知道自己要什麼便會去走的路。”
當我們想到神,一定會想要降伏於他。若非如此,那就表示我們所想的其實不是上帝,只是”我們經由思考、幻想而得出最接近上帝的近似物。”有些人一輩子以為自己在敬拜神、服事神,但是當他們到神的面前時,神有可能會對他說:你是誰?我不認識你。
心理學說,人有價值感、成就感、安全感的需求,但是神卻有可能容許我們經歷誤解、否定、與剝奪,當他這麼做的時候,是因為他不要我們將價值感、成就感與安全感,建立在原本脆弱的根基上。我們所仰賴的事物,就像麻藥一樣,只會讓我們不斷需求更多,卻無法得到真正的滿足。神說 :我有更好的要給你,是不會被這個世界奪走的。你的價值感、成就感和安全感,不是建築在這個世界,而是在一個更穩固的根基上。
魯益師在他的奇幻故事[納尼亞傳奇]裡,創造了一個有別於現實世界的奇幻國度。是[在這個世界以外的另一個實存的世界]。隨著故事的進展,主角發現,原來納尼亞王國比他們自以為是真實的這個世界還要真實。[那裡]---納尼亞王國才是他們真正的歸屬。
魯益師也曾經在年輕時,是一個唯物論、無神論者。他只相信此刻這個世界的實存,除此之外別無他物。就像佛洛伊德說的,[宗教信仰只是企圖透過幻想中現實的再造,來獲得快樂、逃避痛苦……不用說,有幻想症的人是不會承認這一點的。]
這個世上有幾種人,對於一些人來說,他們拒絕承認有看不見的神,對於有些人來說,他們雖然承認有神,卻用自己的方式定義神,但對於另外一些人來說,他們相信有神,也願意承認自己不是造神者,乃是被造的。他們讓神所說的話、而不是心理學家所說的話來解釋在他們生命中所發生的事。他們願意謙卑地承認,有些事他們並不理解,甚至也無法得到答案。這些人活在神的愛裡,身上帶著世人無法了解的平安。
魯益師寫下[痛苦的奧秘]這本書以後,才從自身的經歷當中,經歷到對神的順服,和未曾經歷過的平安。在摯愛的妻子過世之後,他陷入極深的哀痛裡,在他最需要神的時候,卻感受不到神的存在。他向神求問,卻得不到回答。
“當你迫切地需要他,當你孤立無援時,等待你的卻是一扇在你面前砰然關閉的門。最可怕的不是自己會得到[原來神不存在]這樣的結論,而是[原來這才是神的真面目]。”在痛苦當中,他感到孤立無援,神並不像他所想像的,會在他需要的時候,給予心靈的慰藉,像注射一劑麻藥,瞬間挪去熬人的苦痛。他經歷過死蔭的幽谷,然後神的同在才”如夏日黎明的曙光,漸漸鮮明起來”。
魯益師問:[為什麼你讓這些發生?]神並沒有回答。當他迫切想要一個可以理解的答案時,神彷彿消失了,但是當他安靜下來,才感受到祂始終沒有離開的同在。
神的愛不是宗教的麻藥,可以挪去我們心靈的痛苦,祂甚至不是心靈的導師,預備好解答我們一切人生的疑惑。但是神本身就是那個答案。就像耶穌所說的,祂就是道路、真裡和生命。祂並不是說:我要給你道路、真理和生命,而是[我],就是那個道路、真理和生命。
人能夠理解神、認識神,因為神先來找我們。這是魯益師的上帝。他不是一個不聞不問的父親,也不是有求必應的神仙。祂深知我們的軟弱與有限,包括那些智性上的限制、經驗上的限制與生理上的限制。祂的拯救不只是為我們現在[帶來快樂],不只是滿足我們有限的此生的需求。當祂對你說:我瞭解你,當祂對你說:我愛你,祂的愛是我們在世上不曾感受過的,是我們甚至無法瞭解的。當我們接受了這份愛,我們才知道自己存在的意義與價值,單單是因為祂,因為我們在祂眼中的意義與價值。
很多人好奇,唯物論的魯益師,是如何成為一個有神論者?他承認:[要我從理智上接受信仰,實在不是一件易事。]他曾經這樣描述自己:[The Most Reluctant Convert],一個最不情願的歸信者。魯益師的人生經歷,被拍成了舞台劇和電影。讀他的故事,或許並不會讓一個未信者成為一個有信仰的人,因為連他自己[都不知道這是怎麼發生的]。他只知道這是[何時發生],但不清楚[是如何發生的]。他用了一個著名的比喻來形容這件事:[這就像一個人睡了一個很長的覺之後,仍然一動也不動地靜躺床上,卻已經知道自己清醒了。]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從夢中醒來時,才知道剛剛在夢裡發生的並不真實。魯益師以此來描述自己歸信的過程。在夢裡我們也可能以為自己醒著,以為所發生的一切確實存在,一直到醒來的那一刻,我們才知道什麼是真正的[真實]。
夢境反映了我們內在各樣的情緒、欲求、想法,是我們被捆鎖其中的自我的展現。很難想像我們如果試著用理智去整理所有這些意識的陰暗處,會不會反而深陷其中,引來更難以控制的混亂與瘋狂?面對噩夢的煩擾,我們所需要的,會不會只是醒來而已呢?
心理學能夠分析我們內在的需求,卻沒有告訴我們,要從哪裡得到這些需求的滿足。也沒有告訴我們,從有缺陷的人身上尋求完全的愛,是否是有可能的。那份沉重的期待如果放在任何人身上,是否都會摧毀那份關係。如果我們知道自己的需要,卻被告知永遠不可能得到滿足,就好像我們好不容易找到了出口,門卻是鎖上的。
佛洛伊德對人性是悲觀的,對生命也是悲觀的。如同巴爾札克的小說[致命的皮革],這本佛洛伊德臨終前最後讀的一本書。主角從魔鬼那裡拿到一張[野驢皮],每一次慾望的滿足都會使這張野驢皮縮小一點,而當皮革完全消失時,也就是生命的終點。但主角愛上了美麗的女孩寶琳,對女孩的渴求讓野驢皮急速的縮小,最後主角在無法控制的慾望與對死亡的恐懼中氣絕而亡。
對魯益師來說,死亡並不是生命的消亡,像拿在手中的一塊野驢皮,隨著時間漸漸縮小消失。在過世前的一個月,他寫信給朋友,說自己正在享受[生命中一個美好的季節]。即使在身體衰弱的老年,魯益師仍然能夠享受人生每個階段的美好。他在過世的那一天,仍然心情平靜、愉悅,因為對他來說,這個世界並非我家,死亡乃是漂泊不定的此生,終於可以歸回天家的時刻。對這個世界的來說,魯益師死去了,肉體消亡了,但是對魯益師來說,他離開去了一個更美的地方。
佛洛依德和魯益師的兩種上帝,也是兩種截然不同的人生。當我讀到佛洛依德的批判,我知道他所說的沒有錯,但他所抨擊的是宗教,魯益師所描述的卻是真實的信仰,是一個人生命中與神獨一無二的、真實的經歷。當你決定不再別過頭去,就有機會可以遇見並認識這一位。不是別人告訴你的,而是你自己所體驗的,過去未曾見過的真實。這時你才恍然大悟,原來我們並不是自己選擇了成為一個有神論者,或無神論者,是祂選擇了我們。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