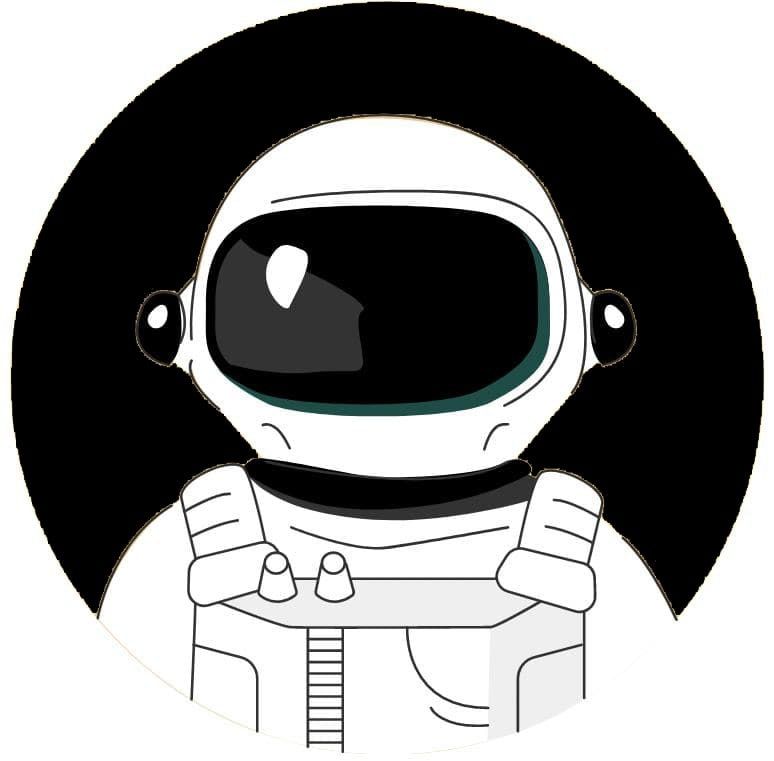【與我去旅行】一份遲了六年的約定,終於兌現

「2024吳哥世界文化遺產探秘」的行程,昨天在旅行社的官網正式上架了。我等這一天,等了六年。
真的要算起來,遠不止六年。
2014年《吳哥深度導覽:神廟建築、神話傳說、藝術解析完整版》出版,此前我花了三年多的時間實地田野、寫作,進出柬埔寨的次數頻繁到,連海關人員都盯著我的護照問候:「你來好多次啊!」
那時還很青春,體能絕佳,體重比現在少了十幾公斤,頭髮茂密烏黑。因為年紀輕,又是女性,三不五時也會遇到被欺負的事情。雖然過程中糟心鳥事很多,這是田野必然的風險,幸好都捱過去了。
調研的時候,已積攢了許多願望。那些美得令人落淚的清晨,得穿著防寒外套穿越森林,隨著晨曦踏破迷霧;氣象萬千的夕照,在遊客散去的傍晚,靜靜降臨蟠蛇殿(Neak Pean)遼闊的水庫,曾經它乾涸如沼澤,當地的古蹟保存團隊,趁著2011年中南半島洪患,將闍耶跋摩七世千年前打造的水庫養了回來。(可參見拙文:將老祖宗的千年水庫養回來──柬埔寨挑戰吳哥水利系統的保存難題)
懸在崖邊上鳥瞰柬埔寨大平原的柏威夏寺(Preah VIhear)、藏在森林中柳暗花明的貢開(Koh Ker),沒有貓但千手觀音像莊嚴絕倫的「貓之城堡」班迭瑟瑪寺(Banteay Chhmar),趁著朝陽的斜射光從門洞照亮豆蔻寺(Prasat Kravan),欣賞紅磚塔中佈滿內壁的雄偉磚雕(必須把握清晨那2小時,之後就沒有光線了),以及數不清的、穿過密林高草,在無人跡處翻越土堆亂石的日子。
回到台灣,我試著向一家家旅行社提案,希望能打造吳哥文化深度主題遊程,但都被打槍。因為當時市面上的柬埔寨行程是非常成熟且刻板的套裝,整個業界都遵循那一套公式在運作:五日行程,扣掉兩天飛機,暹粒的吳哥遺跡密集走三天或三天半(非常趕,一天可以排到6-9個古蹟),一個吳哥寺日出,晚上搭一場歌舞秀,一個崩密列自費行程、一晚或兩晚按摩自費行程,進購物站,結束。
前面我提到的那些地方、那些夢幻絕美的時刻,在既定的套裝行程中幾乎都不存在。
東南亞早就被(業界)做爛掉了(?!)
在一次次的打槍中,我才知道,要弄一個團,安排去到我見過的絕美吳哥,得「客製」。客製的成本全都要重新估價,你得要有超過15個人決定要去,而且這些人沒有預算考量,在這個條件下,兩地的旅行社才會願意多花時間力氣去一一詢價估價、搶機票搶導遊。
在柬埔寨旅遊熱旺爆棚的時候,光是做現有的套裝行程都做不完,除非利潤夠高、前期規劃溝通的成本(即研發成本)能run成固定遊程,誰有空理你做客製?
交情好一點的業界朋友建議:「你的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去考個領隊證,進旅行社任職,人脈打開了,可能會有多一點點機會做自己想做的團,但機會不大就是。因為遊程規畫、線控和領隊,是不同的三個部門。」
名詞解釋:把團帶出去的是領隊,要有領隊證,通常不負責導覽;在當地接團的是導遊,要有導遊證,要負責導覽。歐美線的領隊兼導遊,叫做Through Out Guide,簡稱Through Guide,一人包辦大小事,加上出團天數長,收入最高,也是大多數領隊的職涯目標。能不能做Through Guide要看當地法規,如果法規規定要有地接社和當地導遊,成本結構就要包含給當地旅行社、導遊的費用。這樣的規定沒有錯,保障當地旅遊業的收入與人才培育,由最熟悉當地資源的人來接待,完全合理。做事不能只看獲利數字,共好才能長久。
我聽過最中肯也最殘忍的建議,是這樣的:「做旅遊業,不是把你覺得好、值得推薦的景點安排進去,而是用最少的成本,塞進最多能從客人身上賺錢的環節。」這種作法的極致表現就是「賭團」,最經典的,就是大家耳熟能詳的「零元團」。
東南亞的團因為天數短、利潤低,加上消費者心理預期「東南亞就是便宜」,不得不削價競爭,原則上或多或少都有賭團的性質。你看到團費低到只比機票貴一咪咪的,就是這一類。就算行程看起來塞進一大堆景點,也都是走馬看花,沒有閒工夫讓你細細品味。為了盡量壓低團費,領隊、導遊、司機沒有工作費(沒有薪水),收入完全仰仗客人進站購物、自費遊程的分潤與小費。這種惡質的勞動條件,讓優秀人才不願意留在東南亞線,遊程品質與體驗也無法提升。
2017年底,我準備了一下考試,在2018年考取領隊證,並完成受訓,這個時程大約八個月。受訓時,和同梯的業界同學討論起我要做的事,大家的反應都是:「東南亞早就被(業界)做爛掉了。」「對旅遊業有理想的人都會跳過東南亞。」
但,東南亞那麼大,小小一個台灣怎麼把人家做爛掉?我在當地(不只是柬埔寨)看到的歐美客、日本客,在當地專業導遊的帶領下,都可以在最好的時刻去到我覺得很棒的地方、聽見詳實的導覽解說,為什麼台灣做不到?
不是台灣把人家做爛掉,而是台灣既有的業界生態,自己把自己做爛掉。
而香港的文化遊,是成熟的商業模式
很多朋友以為,我寫了一本《吳哥深度導覽》,這本號稱華文世界最詳實的吳哥文明導覽書,接著就可以靠帶團維生,甚至可以替柬埔寨領隊開培訓課(畢竟去柬埔寨的台灣團那麼多),從此揮別拮据的文人生活。這種想像實在是太天真。
「你知道帶東南亞團的領隊,什麼都不用懂嗎?」領隊訓的時候,回來補受訓的資深導遊同學(她主要接in-band的大陸團,但下定決心轉out-band,所以回來補受訓)跟我講了這句話。以柬埔寨為例,有規定景點講解必須是當地合法導遊,所以領隊完全不必懂那些專業知識。
「所以你懂再多也沒有用。東南亞線的領隊帶出去交給導遊就行了,你要做的就只是把客人伺候好,讓他們願意買買買,不然你賺什麼?」
但我一直不認同這種「就行了」。
2012年,長期與Lonely Planet合作的老友 @鄒頌華 推薦我加入LP的作者群。與她一起工作的那些年,她正與GLO Travel的團隊籌組 「Walk in Hong Kong活現香港」。GLO Travel以文化深度遊開啟了香港文旅市場,而且極具聲量。在媒體採訪中,GLO受訪時都會主張「旅行不應只是吃喝玩樂,更應該是一個深入認識當地政治、文化、經濟的機會,故希望透過設計行程、講解、結連當地人,讓參加者認識一個地方的真實文化。」(GLO Travel:當旅行社不能再辦旅行團,要退場還是前進?)
我一直認為GLO的路線才是對的,從小我對旅行的認知一向如此,從來沒有懷疑過。從少年時使用LP去旅行,到後來加入LP團隊、為LP調研、寫稿時,也是秉持相同的原則,一直都沒有歧義。我不明白為什麼這個原則在台灣的旅遊業界不存在、做不到、台灣的市場不支持。
每次和旅遊業的朋友討論起這些令人沮喪的現象,對方往往會回我一句:「你想做的是回歸旅遊本質,但這很難,消費者看到價格就直接放棄。」
慢慢的,開始有香港的旅行社找上我帶團。因為我沒有香港的領隊牌,他們出領隊,我以隨團導師的身份參與,從遊程規劃到現地導覽,我知道這不是做不到的事情。
帶到2018年底,也是我疫情前最後的一團柬埔寨團,香港另外一家做文化遊的品牌敲定我2019年去主理整個文化遊項目,於是我撤離台灣準備深耕香港。香港做得到,那當然要去。
2019年的年度計畫在我赴任前就已經排妥、公開招募,所以我想做的新計畫,得在2020年才能推出。無妨,要學習、適應與磨合的眉角太多了,順著工作節奏走,我深信,很快我的理念就可以落實。
香港熱衷文化深度主題的人真的很多,雖然他們總跟我說自己這個族群是超級小眾,覺得台灣文化風氣濃厚,一定比香港更能發展文化遊。我搖搖頭,在我看來,比起台灣的旅遊市場,香港有文旅習慣的消費者,規模可說是超級無敵霹靂大眾。別的不說,在香港,出國旅行是剛需,因為城市生活壓力太大,一年總要飛出去N次,每個月都跟團在世界跑的退休人士多得是。但台灣不是,一年能出去一次已不容易,熱衷文化歷史藝術的人更是窮得連生活都難以維繫,兩地的市場基礎是截然不同的。
2019年的夏天,大環境陡變。我在秋天辭職回到台灣,本想在台灣延續我香港的工作經驗,一切籌謀中,找到合作團隊也正在規畫行程,2020年初,疫情來了,全球lock down。
疫情四年,一切重來
GLO Travel在疫情期間靠轉型網上文化講堂挺了過來,我也在台灣四處教課、講學、策展、寫書、做節目,忙得筋疲力竭。而我在香港任職的那個文化遊部門在疫情之中結束,當時接手我工作的同仁,沒多久也辭職,移民來了台灣。
然而,這麼多年過去,我已從衝勁十足的青年變成了疲憊中年,肌肉鬆弛,兩鬢飛霜。
這兩年疫情逐漸解封,旅遊業要恢復卻沒辦法那麼快。企業縮編解編,有經驗的老手轉行,停止營運的產業要重新運作起來,卻什麼都變了。消費者的期待變了,進入旅遊產業的人變了,成本結構變了,產業鏈的運作方式變了,所有的合作默契都要重新培養,規矩也都重來。
對我來說這是好現象,大家的心態變成「只要有機會,不妨試試看新方法」。去年四月我開始籌組踏查隊,因為柬埔寨在旅遊警示的燈號是紅燈,改從越南起步。也有其他夥伴分別從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地出發,各有不同的專長,人類學、文資保存、飲食研究等,大家分頭進行,一起累積經驗與能量。
但是,找不到旅行社合作依然是硬傷。這是法規問題,要合法出團就只能跟旅行社合作,但觀光法規的制約之下,旅行社要負擔的風險非常大,想要有別出心裁的做法,也要考量潛在的風險成本,不能真的像背包闖天涯那樣自由奔放。
很感謝這幾年一起並肩在這段路上奮鬥的夥伴,介紹了同樣懷抱著「回歸旅遊本質」心願的旅行社。
2024年,我會密集上路,期待認同這個理念的你,與我一起去旅行。
最後,要謝謝 @阿良 ,謝謝你記得曾經背著大背包上路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