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爱,一道“仅限女性”的伪命题
本文为“不止身体”专栏文章之一,本文首发于beU Offici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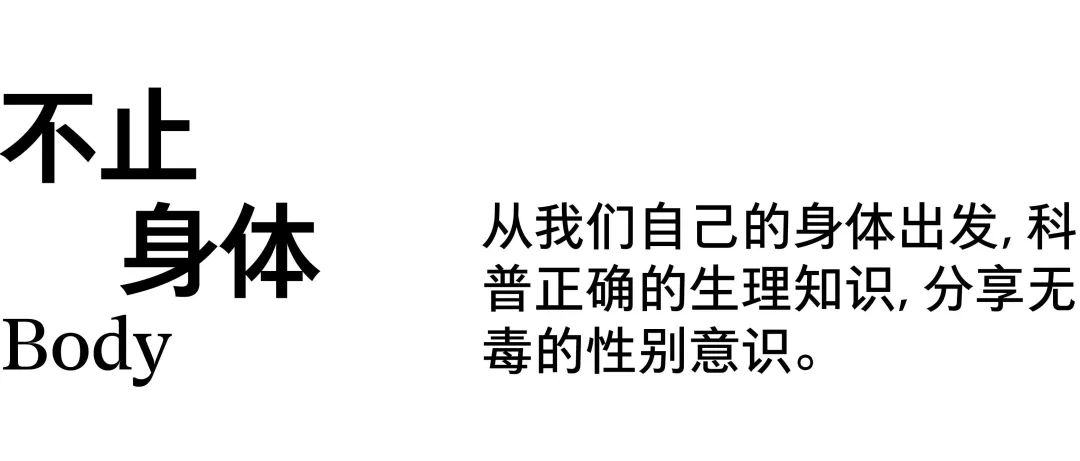


初中的某个夏天下午,我正在房间换衣服,我妈也在。我刚套上一件化纤布料的短袖,她就开口了:“以后不要穿这件了”。我很疑惑,歪头“啊?”了一声,她说:“你现在发育了。”
我:“啊?”她:“你胳肢窝这块有毛了现在。”我没听懂她要表达什么,也没说话。她:“化纤不透气,胳肢窝有味道被别人闻到不好。”我感觉有点莫名其妙,但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她:“女孩子还是要注意这些,要自爱。”
我很不高兴,却不知道怎么反驳。最终,我还是按她的意见换了一件纯棉短袖穿。
直到现在我还是常常想起这件小事,因为那是我第一次被如此直接地提醒“你不再是一个小孩了,你是一个‘女孩子’”。我身体的变化就是我成为女孩子的证据,我的身体“发育了”,我的胳肢窝“有(腋)毛了”。
与此同时,我的身体变化又反过来成为某种要挟:拥有一具女孩子的身体,如果不为此付出一些额外的劳动,就是不好的。如果我还和小时候一样爱跑爱跳爱疯,如果我的腋下因此堆积了汗液,如果我的胳肢窝因此有了气味,如果我还不小心让别人闻到了这种气味,那我就是不自爱的——这就是我妈短短一句“女孩子要自爱”背后所暗示的多重劳动,不可以穿化纤布料的衣服只是最浅表的一层。

随着我长大,“女孩子要......”之类的咒语变得越来越多,咒语内容也越来越和女性的身体有关。
如果不穿bra,我们会听到“女孩子要留心自己的风评”的劝阻;如果有活跃的性生活,我们会收到“女孩子怎么一点都不知道要珍惜自己”的评价;如果穿着贴身的leggings去运动,我们会被教育“女孩子要注意影响”......留心风评、珍惜自己、注意影响,这些隐晦又空泛的说法本质上和我妈的话如出一辙,它们都在重复那句“女孩子要自爱”。
这种“自爱”,到底指什么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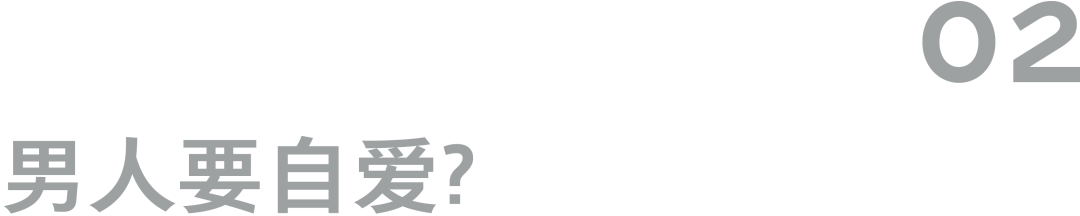
2018年,法国女性导演 Éléonore Pourriat 的电影《Je ne suis pas un homme facile》男人要自爱》在网飞上映,成为网飞的第一部法语电影。这部电影的中文译名是《男人要自爱》,用性别调转的方式还原了所谓“自爱”背后的权力关系。

电影里,男主原本是个普通但自信的中年男人,做着一份极其厌女的工作——为男性用户开发一款打分app,打分对象是他们睡过的女人。某天,他边走路边大肆 mansplain,不小心撞到了脑袋,晕倒了。
等他醒来后,世界全变了:女人是高管和富豪,男人毫无话语权;女人可以随时随地半裸上身展示腋毛,但男人要全身除毛护理头发给丁丁除臭;女人把男人当作物品和性捕猎对象,毫不留情地点评他们的穿衣打扮和性爱表现,男人则要无时无刻地审视自己的姿态和行为,既不能太保守也不能太放荡,否则就是不自爱......

这些情节非常离谱但又非常真实。离谱是男主感受到的,因为在性转前他从未想象过要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日常的管理、修整和包装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但真实的是,女性一直一直像这样主动或被动地“打理”自己的身体,以自爱的名义,以“I am not an easy girl”的名义。
在电影里,两个人主做完爱,男主半盖着被子,露出光滑的上半身和修剪得极为规整的胸毛,半倚在床头,抬眼天真地看着女主说“我希望我们是平等的。”女主则回复“那太蠢了。”

这一幕全方位地还原出了“自爱”话术背后巨大的陷阱:我修毛、除臭、管理自己的身材、穿你喜欢的衣服、在床上为你提供服务......我已经按照你的期待努力成为了一个全方位的自爱男孩,在这之后,我可以要求一些尊重和平等吗?我鼓起勇气问出这个问题,但却忘了那些努力本身就是不平等;我向你表达我希望平等,我向你要求平等,但却不知道平等从来不是你想要的,平等也从来不是向谁求来的。
接受了“男人要自爱”设定的男主很困惑也很痛苦,就像现实里顺应了“女孩子要自爱”的条条框框却依然感到不适的女生们一样,进退两难。
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也夹在这样的进退两难中。就像当年遵循我妈的建议不再穿化纤衣服一样,就像电影中的男主一样,我非常努力地按照别人的标准去审视、要求和改变自己的身体,迎合那些以“女孩子要自爱”或“女人要爱自己”为名的规训。即使与此同时我不高兴、不舒服,肉体和精神上都在挨饿,我也不敢承认主流性别规范下的“自爱”其实是个只传女不传男的伪命题。
电影结束,现实里的“自爱”话术套牢的依旧是女性。

以规训女性为目的的“自爱”假面曾经被艺术家 Barbara Kruger 用下面这份作品毫不留情地揭露过:

这幅作品是 Barbara Kruger 为了凸显堕胎议题下女性的身不由己而创作的:子宫是女性身体的一部分,但如何处置这一身体部位却不由女性说了算。在当年,保守势力也会指责想要堕胎的女性不自爱、不检点,不对自己和生命负责。
Barbara Kruger 复制了一张1950年代的女性脸部照片,画面左边保留原图,精致自如;画面右边反向曝光,阴森诡谲——她故意以此制造出视觉上的强烈反差。再加上红色广告版面和白色粗体字,这幅作品成了当年走上街头夺回身体自主权的女性们人手一份的热门画报。而“your body”包含的对话性,则向每一个看到这张图的人发出犀利的提问:你敢说你的身体不是一个战场吗?
我不敢。
在 Barbara Kruger 的年代,女性因为不能自行决定堕胎与否而过着如图所示的双面人生;在许多被“自爱”或类似话术规训的女性身上,战争体现为我们时而满足于循规蹈矩换来的肯定,时而苦恼于自己的身体为此付出的代价。如果我们在一些时刻安于左半边的糖衣炮弹,那必定有另外一些时刻我们会受困于右半边的阴影。

说实话,直到今天我还是会在必须出席一些主流社交场合时纠结该怎么打扮才能看起来正常和不出格,才能不被评价为随便和不自爱。即使最终我选择遵从自己的心意去穿着、去表现,即使内心对此有过的纠结再短暂、再微小,我还是会提醒自己说:这个纠结的过程也是妥协,是我本不需要付出的劳动——这种察觉是 Barbara Kruger 的作品带给我的,也是我想要通过跟自己对话,去重新定义“自爱”的开始。
“自爱”本该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词。如果可以回到初中,我想跟我妈说“比化纤还不透气的,是你跟我说的那些话”;如果可以,我也真的很想在《男人要自爱》里性转后的世界活一活,体验 topless 地做所有事是什么感觉;如果可以,我也想邀请我妈一起去到那个世界,然后光着上半身对她喊“你不是要透气吗,什么都不穿才最透气!”这些如果,也是我打开自爱想象力的练习。
他们说的“自爱”是只传女不传男的伪命题,现在已被证伪,下一题的解留待女性自己去书写。
Like my work? Don't forget to support and clap, let me know that you are with me on the road of creation. Keep this enthusiasm togeth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