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說很痛,哥哥說很舒服|身心障礙者 的家內性侵風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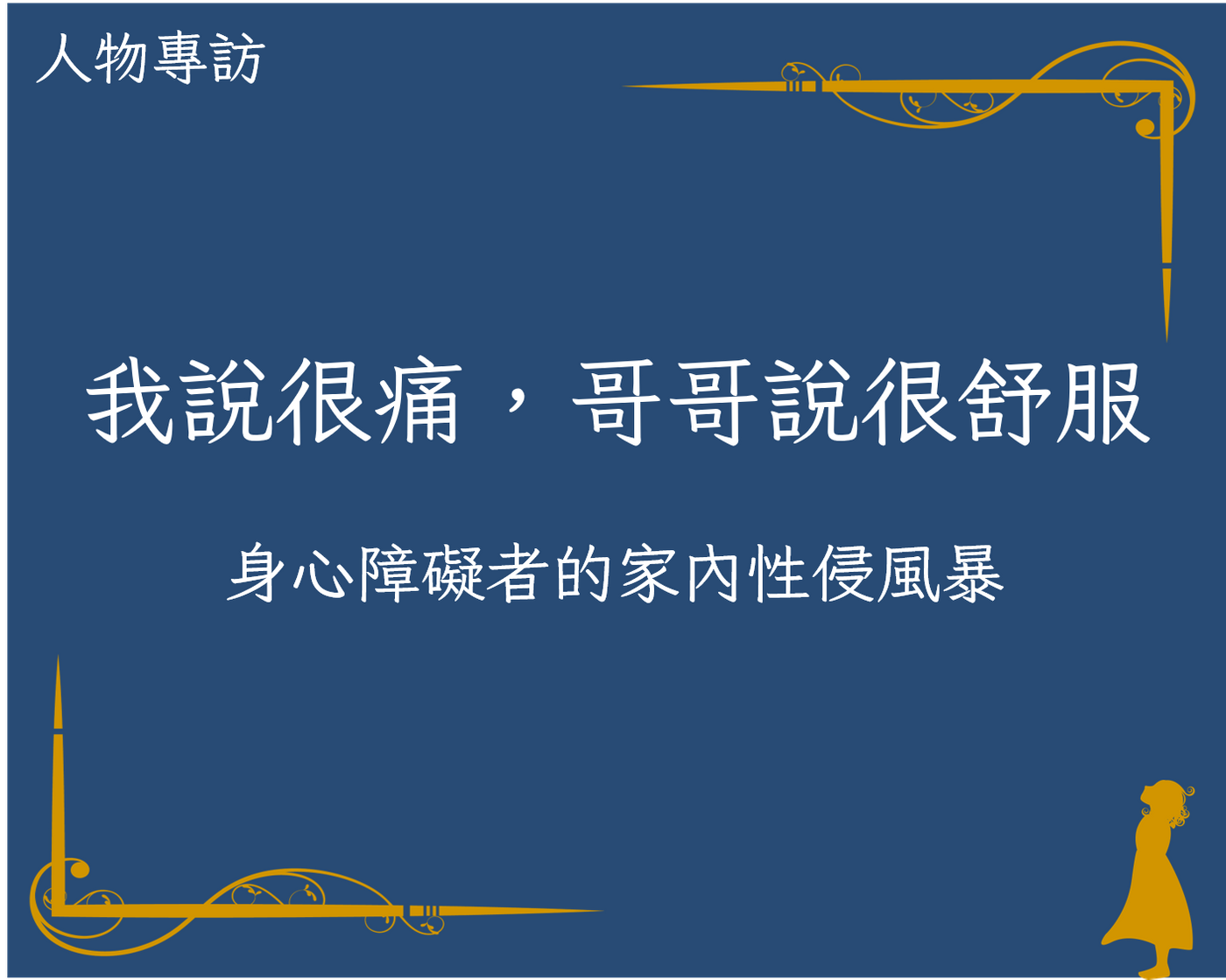
*內容與細節均經部分變造,如有雷同,純屬巧合
「對不…….起,拜託不要罵我。」接起電話,這是我在訪談現場聽到的第一句話,也是我對O第一次產生強烈的印象。當時她錯過上車的時間,急急地打來道歉,語氣像是世界末日。我聽到話裡濃厚的哀求,不知該作何反應。直到真的面對面坐下來訪談,我好像才可以理解O面對世界的姿態。
我是腦麻兒,家人、同學都霸凌我
「除了我有身心障礙,其他人都算滿正常的。」O是一名輕度腦性麻痺的身心障礙者,據她說,可能因為當時的醫療技術不發達,胎兒在生產過程中缺氧,才造成腦部受損。腦麻經常伴隨語言障礙與肢體協調問題,需要旁人的留意與關懷。在O的家庭裡,其他人都是「正常」的,除了她。但家人並未因為O的特殊而給予更多的照護,媽媽不但會在小事上苛責她,還會對她施暴,哥哥、妹妹會凶她,把她視為「什麼事都做不好的廢物」,是家庭中格格不入的那個人。
但在訪談過程中,我觀察到:除了口齒較不清晰、行動較為緩慢,我需要更靠近O,並重述她的話,確保我的了解無誤外,我們的訪談過程並沒有什麼差異。卻也是這點,讓她成了身心障礙者的邊緣人。「我在身障中算是很邊緣的。」在O的情況中,腦麻並未影響她的智力,就學時,家長可以選擇進入一般班或特殊班。然而,不論在哪種班級,O都像個外人。這樣尷尬的處境讓她面臨嚴重的霸凌,在國中時期達到了巔峰。也是那時,O遭受了來自哥哥的侵害。
哥哥說很舒服:為了防衛,我把這一切都忘了
O國一那年,哥哥尾隨她進入廁所,「一開始是用手指一直弄我尿尿的地方,後來就、後來就、後來就逼我,用他的生殖器直接穿透我尿尿那裡。」本能的痛感讓她告訴哥哥:「我很痛」,但哥哥說:「很舒服」,伴隨持續的穿刺。往後在沒人的家裡、房間裡,哥哥一而再、再而三地侵犯她,並在過程中流露少有的溫柔,使得O更加無所適從。在家庭、學校都得不到支持的情況下,O沒有人可以傾訴,也不知道該怎麼面對這件事情,只能任哥哥為所欲為。
直到3年後,O從網路資訊發現:哥哥對她做的事其實很嚴重。她便下定決心,不要再讓哥哥這樣做,拒絕的過程卻沒有這麼順利。哥哥起初將她帶往房間,把房門關上,O想出去,哥哥便擋在門邊,想盡辦法軟硬兼磨,還想要做。「到最後,我坐下來說:『我!不!想!做!』,又哭著說『哥哥我不要!我不要!』哥哥才願意開門。」自此以後,O的哥哥再也沒有侵犯她,O也徹底遺忘這件事,「那時候也是防衛自己,發生完事情我就忘記了」。
如果沒有打官司,我就不會這麼痛苦地活著
同學的霸凌到了高中有所好轉,O在無意觸發中,想起了哥哥對她做的事,便與朋友傾訴。然而,事情遠比她想得複雜。「我一直知道這件事會有點嚴重,但是我沒去重視它。」朋友將這件事告訴老師,開啟了一連串被通報、社工關切、打官司的流程。「我很愛哥哥,我那時候真的沒有、高中不知道怎麼去處理。」開庭前一天,O的家人為此開了會,得出「要判哥哥無罪,所以O要對老師、法院說謊」的結論。儘管O打從一開始就決定原諒哥哥,「我沒有辦法眼睜睜的看他被關進去,我每天都在祈求老天爺,讓他無罪。」家人對哥哥的偏袒仍讓O備受痛苦。「我媽媽那時候ㄧ直罵我,好像是我講出來的,是我的錯」。
開庭前,媽媽跟爸爸說:「我們帶哥哥去自殺。」那個家裡的「我們」,沒有O的位置。另一方面,法官、社工也對O反覆的說詞產生懷疑,「我知道你說謊,我也不能保護你」,讓O處於兩難的境地 — — 不希望哥哥坐牢,但又不被家庭支持,還要面對司法調查的恐懼。將近十年的司法程序讓O罹患憂鬱症:獨自承受所有的痛苦令她幾欲自殺。
如果我是正常人
「對不起我會怕」、「對不起我需要抱抱」、「拍拍我的背」,訪談過程中,O幾度顯露情緒。初次遇到身心障礙的受訪者,老實說我很緊張,我不知道要怎麼捧起這樣的一個人的故事,戳探得太大力,就像在傷口撒鹽,如果太小心翼翼,就顯得我以為她很脆弱。但她說:「如果我是正常人,好像不會發生這樣的事。發生過的事都對我有益處,我想要幫助更多人。」

我們是「暖暖 Sunshine」,
一個由性侵害倖存者發起的「性暴力受害倖存者」匿名分享平台。
說說故事:https://forms.gle/CtbKP3kwVZEYazcc6
聽聽故事:https://medium.com/@2022.nuannuan
追蹤我們:https://www.facebook.com/2022.nuannuan
歡迎註冊免費的Likecoin會員
拍手5下,鼓勵我們為性暴力發聲
成為讚賞公民,用每月一杯咖啡,成為我們持續揭露性暴力的助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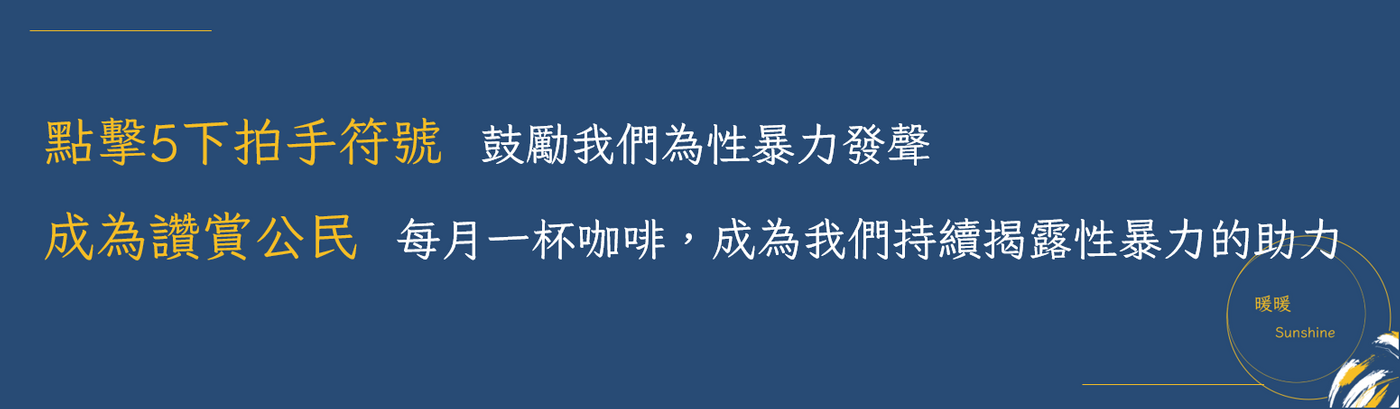
Like my work? Don't forget to support and clap, let me know that you are with me on the road of creation. Keep this enthusiasm togeth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