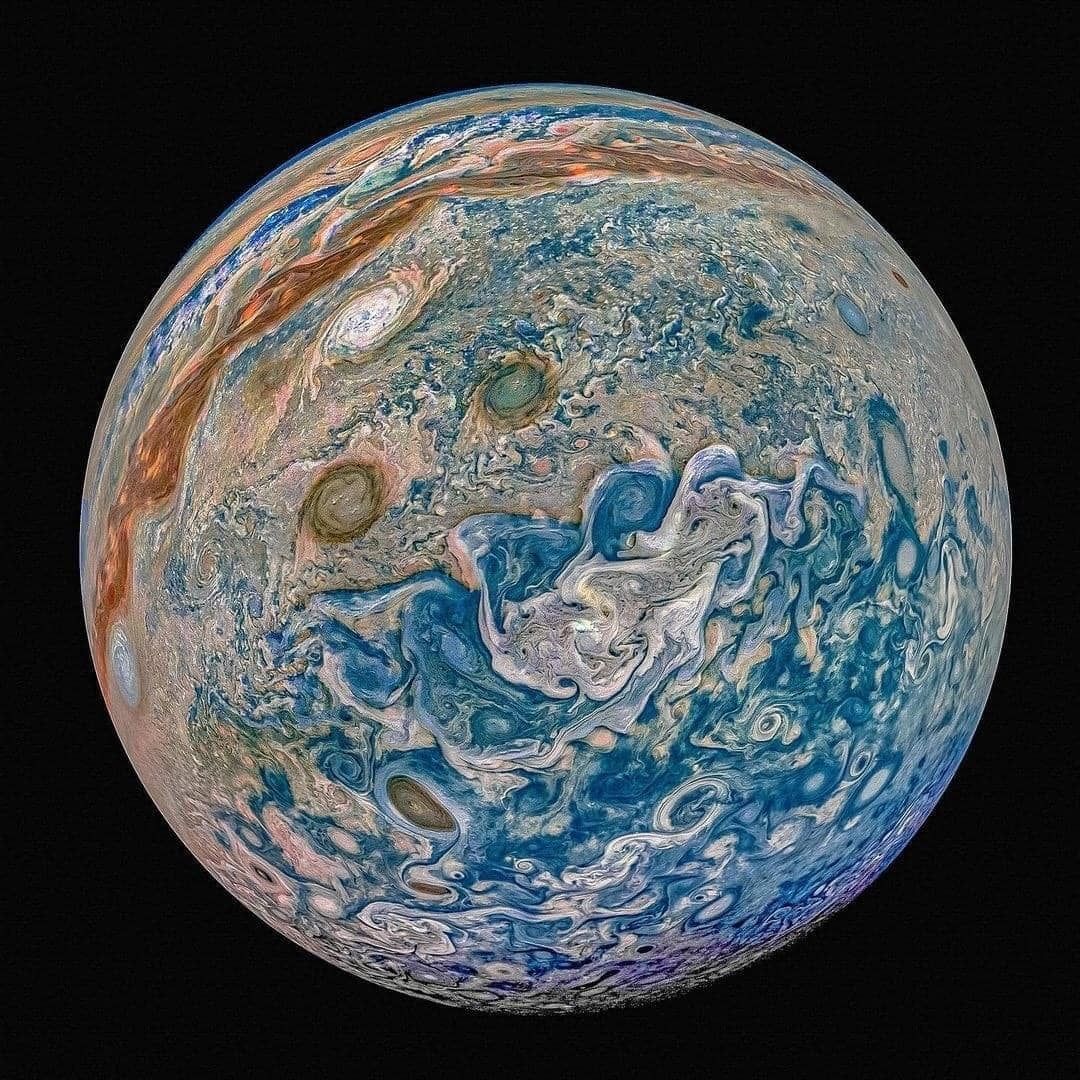個人小寫|蟻路
此文寫作完成後,投遞該年度林榮三文學獎,得一評語曰結尾不符現實,綜合其他因素最後未獲獎。後轉於2018年2月21日《自由時報》副刊登出。
螞蟻什麼都爬。
搬到這之後,家裡的螞蟻換了一種。舊家的螞蟻起先還不太多,偶爾食物忘了收,或該綁的沒綁好,或綁久了橡皮筋彈性疲乏導致門戶大開,才會引來螞蟻搬食。那時的螞蟻是暗褐色的,姿態不慌不忙,但會咬人。其實不咬大家相安無事,也不會知道有什麼食物遭了殃。一咬,等於占地插旗的宣示。一口也罷,兩口三口,四五六口,咬到人心浮氣躁了,便無法再容異種在地盤上如此囂張。循路獲巢,要嘛灌水,要嘛下藥。既然你不把握我罕見的好生之德,我也沒必要跟你客氣什麼。
只是事情從來也沒順利過。殺戒一開,往往不是你想停就停得下來。有時我很疑惑螞蟻彼此的通報機制。照理說世間萬物都該珍惜生命,知道這裡有個瘋婆子卯起來殺蟻殺到眼紅,已經那麼多前線將士壯烈犧牲了,不是應該發出警告電波通知樓上樓下行李款款另覓他處嗎?顯然螞蟻不做如是想。我殺得愈瘋,牠們占得愈狂。本來只在開過的食物沿線流竄,後來,陽台上的盆栽廢土有了(或許牠們嚮往親近自然風土),待洗衣物堆裡有了(不知為何很常咬破內褲),封裝完整的乾貨罐頭也能見到牠們的蹤跡,在密不透風的包裝上著了魔似地環繞,希望找到其門可入,非常堅持。
有一陣子時不時就有螞蟻飛來落在我身上,我怎麼也找不到來源,一度懷疑蟻路延伸到天花板,那些個攀抓力不足的螞蟻便失手墜落。某天我又莫名被咬了幾口,突然福至心靈地盯著一旁搖頭賣力吹送的電風扇看了好一會,按掉開關拔了插頭將風扇大卸八塊,卸到底座,赫然發現螞蟻們從四面八方搬來塵土毛髮,在裡頭築了個好生安適的巢,看得我頭皮發麻。不知道那些螞蟻在風扇內紮營是不是為了某種祕密任務進行高空訓練,乘風而降時卻老控制不住吃葷的口欲,一咬便洩了行跡。
還有一次我順手拿了掛在床頭的毛巾去洗澡,洗完擦身。不擦則矣,一擦全身不對勁,定睛細瞧,手上腿上好幾隻螞蟻亂竄,邊竄還不忘張口啃皮食肉。我驚慌地旋開大水重新給自己刷洗得更徹底,洗完抓起毛巾扯開一看,巾面上密密麻麻毫無邏輯的蟻群。我又怒又躁,顧不得殺生造業,把整條毛巾扔進熱水。望著那一層浮上水面的蟻屍,心想你們何苦逼我至此。
如是我身上常有蟻咬的腫丘,一塊一塊暗自發紅,好似吻痕般羞澀,卻癢到足以令活人崩潰。那也像是人蟻之間的征戰紀錄,以肉體為計分板,一痕得一分,刻畫著蟻類的開疆拓土,與人類的節節敗退。
童年時我常隨母親返鄉,外公外婆在屏東小村種植水果,鳳梨芒果荔枝蓮霧,一片熱帶風情。果園裡什麼沒有,蛇虺蚊蚋無一不缺,最怕就一種紅頭紅身的紅螞蟻。隻隻肥壯,蟻身堅實油亮,一看便知是不好招惹的貨色。常常我在果樹間穿梭玩耍,一不留神踏上蟻路,只要引來一、兩隻上身、只要咬上一口,我們的農村假期就隨著我火速腫脹的手腳畫下句點。那時母親固定帶我在高雄市區昇平街內一處皮膚科就醫,醫師姓吳,候診一小時,看診三分鐘。每每醫師見我脹著一手掌或一腳背步入診間,便笑笑地:「又被紅螞蟻咬啦?」有時挨上一針,通常開三天藥,再加兩扁盒白色藥膏。腫消下後會浮一個水泡,是螞蟻的咬口;水泡褪掉(或被我抓破)則會留一個疤。吳醫師是我永恆的救星,他那藥膏很是神奇,不涼,但擦上便止癢。我總希望他能多給我兩盒存用,彷彿那時便預感自己與螞蟻是一輩子的戰爭。
有時我不免慶幸自己年紀大了皮肉厚了,或免疫力增強了,或螞蟻品種不一樣了。現在被咬,腫還是腫,癢還是癢,咬口疤也還是照留,但已不至於像童年那樣一口換一手(或一腳)。即便如此,去得郊外田間,我依舊不敢掉以輕心。畢竟吳醫師與我一南一北,天高皇帝遠,萬一又被咬了腫成麵包人,只怕我撐不到去見他,就先給自己截了肢。
搬到現在這個住處,室友們和我原本都還挺樂的。新環境新氣象,雖是上看三十年的舊屋,然格局方正、明亮通風,前幾屆房客也將房子維持得挺好,不見老態。覷著農曆年假期工作空檔,我們便歡歡喜喜地住了進來。
歡喜不了幾個月,春分剛過,蟻災便至。先是牆角門邊現了一列一列頗有秩序的蟻路,我們幾個各自觀察了一陣,一時找不到牠們有什麼特別肆虐的行為。尤其我看這批螞蟻不是舊家那種暗褐蟻,頂著黑頭,搖著摻點黃色的蟻腹,個頭更小,不帶一絲會咬人的凶殘樣,便也隨牠們去。
但事情總是這樣的:你想和平共處,對方不見得領情。搬家百廢待舉,平日各自在工作上忙亂的我們,進駐之後草草安定,也不急著全部拆箱就定位。在這方面,螞蟻扮演了皇帝不急急死太監的太監角色。時不時我們便會發現還封著的某一箱某一袋爬上了一列螞蟻,拆開一看,裡頭肯定有個啥貨遭了蟻殃。可能是泡麵,可能是冰糖,無論是什麼都給螞蟻啃破一個小孔,辛辛勤勤地把我們的存糧運成牠們的。
然而,那些螞蟻是有點過分了。
原本想說,好吧,就當牠們是來提醒我們快些把日常打點好,不要一直將就過著紙箱生活。螞蟻看上哪箱,我們就整理哪箱,有時還剛好拆到一時遍尋不著的東西,未嘗不是某種天啟。直到某次,室友苦著一張臉告訴我,她已經好幾天晚上,睡到一半被螞蟻咬醒了。
「而且這種螞蟻很煩,妳把牠們蕊死會好臭!」室友說。
我們討論了半天,一時還沒想到怎麼解決,只好暫且擱置。然室友的抱怨像是按到某種開關,那場對話之後,螞蟻不只上了她的床,跟著爬來我的桌。常常我對著電腦工作,便見螞蟻呼朋引伴地進入我的視線範圍。我桌上零食收得緊,看到螞蟻入侵我更決心盡量把零食往嘴裡塞,一點存貨不留。只要蟻群鬼鬼祟祟在我周邊探頭探腦,我要嘛整理桌子愚公移山,要嘛拍案驚奇製造地震,希望突來的變化能嚇亂蟻路,讓螞蟻們知難而退;更希望牠們去查詢我的殺蟻前科,進而啟動通報系統,不要再來煩我。
過不了幾天,另一個室友的房間也淪陷了。除了房間,浴室也現了蟻蹤,廚房更是重災區,所有生的熟的鹹的甜的乾的湯的全的渣的,螞蟻們無一放過。其見獵心喜的程度讓我好奇牠們到底是餓了多久,或者食指多麼浩繁,得這樣千千萬萬形形色色的吃食才能滿足。
這批螞蟻比舊家的螞蟻更得寸進尺,絲毫不懂適可而止。你抹去這條蟻路,牠們也不費心走遠,就在旁邊另開一條;咬破一包餅乾,還沒搬空,硬要再開一包。你以為牠們什麼都要,豈料牠們專挑好貨。加工太多的不吃,化合物更看不上眼。阿里山手工黑糖夾鏈袋沒壓好開了一小口,牠們趁勢搬得浩浩蕩蕩;一盒蛋卷吃掉三根還留兩根,我只簡單將折起來的袋口夾住,牠們連靠近都沒興趣。那天我拿起蛋卷看了一下成分,一堆有的沒的,想了想,便往垃圾桶扔。連螞蟻都不吃,我為什麼要。
有好一陣子我對這些螞蟻探勘的毅力很是佩服。牠們熱愛尋訪各種未知,即便危及生命也在所不惜。當我發現我的馬克杯裡無論裝的是水是茶,有糖無糖,只要擱一陣子不動,再拿起來要喝時,裡頭都會浮著蟻屍,我的神經便愈來愈靠近臨界點。你搬食物也就算了,偶爾爬來我身上咬個一口、我把你彈掉就是了;但我著實不喜歡我在工作空檔只是想喝個水,還得因為你死在裡面,不得不起身倒掉、清洗、重裝一杯。舉凡任何打亂工作節奏的事情都必須遭到天譴。
一再重複倒水洗杯,很煩。於是我找來一個深盤裝了水,給杯子墊著一盤護城河。水可以隔離味道,隔斷去路,卻隔絕不了這些螞蟻雄兵探勘未知的決心。我以為牠們用觸角點點水面便會知道此路不通,沒想到牠們竟前仆後繼地投身入水,硬是想要知道那湖心之島藏著什麼寶物。到底是什麼樣的執念啊,這是蟻界的泳渡日月潭嗎?就算給你僥倖游上杯島、探到祕境,你形單影隻的又搬得了什麼回去?更何況你游過一灘水,探到的,只是另一灘水啊。
我看著深盤水面漂起一隻又一隻壯志未酬的蟻屍。牠們努力划動六肢、卻不幸於登陸前滅頂,在精疲力竭的最後一刻,牠們會不會懊悔自己選錯了路?我又看見幾隻游過同伴屍體、幸運攀杯的勇蟻,看著牠們發現裡面不過是一樣的水,慌然無措地在杯緣來回踱步(怎麼會這樣?現在怎麼辦?要再游回去嗎?),那是不是一種我常有的、人生徒勞的感覺?
某天我從朋友處得知有種螞蟻藥很是神效,轉身就在網站下了單。突然一陣求知欲,便順勢查了關於螞蟻的身家背景。或可能是某種不想讓你在我的世界死得不明不白的動機吧,總之我得知舊家那種暗褐色螞蟻是中華單家蟻,現在這種蕊死會留下臭味的叫黑頭慌蟻;我還在果園穿梭玩耍的時光,台灣尚未出現令人聞之色變的入侵紅火蟻。維基百科告訴我:入侵紅火蟻源自南美洲,在1930年代傳入美國、2001年左右透過貨櫃運輸及草皮外銷等方式蔓延至台灣。那時外公外婆早已將果園分給舅舅們,我也不再和母親回鄉,算是逃過一劫吧。
而在等待貨到的日子裡,我和室友分頭確認蟻蹤,好決定屆時要把藥往哪投。奇怪的是,原本多到讓人心煩的蟻路,竟一條一條不見了。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