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朵拉的檔案之五|一個法學家的越獄四百週年紀念
我們在之前關於荷蘭奴隸史及早期台灣史的文章裡,曾經談到「檔案之外的歷史」。這個說法乍看明白,似乎人人能懂,但實際設想起來卻又不免模糊。到底什麼是檔案之外的歷史?和我們的檔案學家燕鴴什商討過後,今天就讓檔案學家連同檔案一併退到視野之外,且讓我們從一個人、一座堡壘說起。
今次內容大要
從小書《海洋自由》開始的故事
十四世紀古堡的昨日今朝
為何古堡要慶祝有人逃走四百週年?
法學家的書信與法學家的馬桶

從小書《海洋自由》開始的故事
1609 年,一本名為《海洋自由》的小書在荷蘭萊頓出版了。這小冊子不著撰人,旨在為數年前荷蘭東印度公司的一起事件辯護。事件發生在 1603 年的 2 月底,受僱於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船隻在未獲授權的情況下,在新加坡海域洗劫葡萄牙船《聖加大利納號》。這殺人越貨的海盜行為在歐洲掀起外交風波,更糟的是,當時的葡萄牙屬於西班牙王國的一部分,而獨立的荷蘭(低地七省聯合共和國)正和西班牙慘烈交戰。可以想像這樣一本小冊子的出版很令西班牙人冒火。更令他們冒火的是,這不知名的作者儼然天下第一流的辯士,拉丁論文辭藻優美,辯才無礙,逐字讀去似乎有些狡獪,問題是沒有人能夠以同等的力道和邏輯來反駁這些論點。不久後謠言四起,說這小冊子並非無名之輩所寫,作者其實就是 15 歲時便被法王亨利四世譽為「荷蘭奇蹟」的天才律師,葛羅休斯(Hugo Grotius / Hugo de Groot)。這一年,他 26 歲。
⇩ 圖為 1915 年出版的《海洋自由》,是拉丁/荷文雙語對照版,封面上標明作者為 Hugo Grotius。當初荷蘭東印度公司僱請葛羅休斯為公司辯護,葛羅休斯為此寫出龐然完整的《論戰利品與捕獲法》,不過只有其中一章被荷蘭東印度公司採用,在萊頓以《海洋自由》小冊子的形式出版。

葛羅休斯這個名字在我們的時代更常和另一個美譽連結在一起,那就是「現代國際法之父」,而當初不具名出版的《海洋自由》則被認為是現代國際法奠基之作。葛羅休斯在這本小書裡,力主海洋是國際領域,任何國家都有權利自由從事海洋航行。這個海洋自由的原則至今仍是國際法的基礎。例如從去年起我們常見到美軍船艦通過台灣海峽,或者進入南中國海,舉世皆知那是在向中國示威,但美軍總要強調,美國是依照國際法行使自由航行權,而這個權利的內容在今天和在 1609 年《海洋自由》出版當時,並沒有根本性的變化。
葛羅休斯在世時,他作為神學家、哲學家的名聲其實還過於他作為法學家的名聲。他中年時期的大作《戰爭與和平法》堪稱歐洲法律思想由中世紀轉向現代的標誌之作,不過對後世影響最深遠的還是他年輕時代熱情洋溢的《海洋自由》理論。而葛羅休斯「海洋自由」思想的特殊之處,在於他將一個地理性的空間(海洋)轉化為一個智識上的空間(自由的海洋),而這個思想和理解的空間一旦被創造出來,就再也沒有還原的餘地了。
葛羅休斯年輕時在海牙擔任執業律師,後來跟隨父執踏入海牙政壇,不幸政治靠山在鬥爭中失利倒台,他被牽連逮捕,在海牙受審,以叛國罪被判決「永恆的」監禁。我們從葛羅休斯弟弟的書信中讀到,他面對莫須有的政治迫害,這樣回答法官:
「我以為除了地獄以外就沒有什麼稱得上永恆了!」
在那之後,葛羅休斯就被送往瓦爾河上一處孤立的沙洲古堡,要在那裡服完他「永恆的」刑期。那個地方就是我們今天的主題——路浮堡(下圖)。

十四世紀古堡的昨日今朝
路浮堡大致建成於 1375 年,位在瓦爾河(萊茵河下游流經荷蘭的主流)和馬斯河匯流處的一個沙洲上,自那時起就倚靠水路與外界通聯,至今依舊如此。由於這是一座保存良好的中世紀古堡,在歷史上又曾經充作高階政治監獄,承載豐富的荷蘭歷史,現在古堡及其周遭附屬建物以博物館的形式對外開放,成人票是 14 歐元。
想要造訪路浮堡博物館,遊客只有一條路徑——從霍肯城的碼頭搭船,中間在小城沃里肯上下客,最終抵達路浮堡所在的沙洲。霍肯和沃里肯都是有著防禦工事的堡壘城,這兩座城市和沙洲上的路浮堡以及另一個有著塔樓的符倫堡合稱「堡壘三角洲」,是荷蘭保存得最完整的防禦水道,如今則號稱荷蘭最美麗的觀光水道,遊客在春夏季上船,頓時感覺視野開闊,熱氣全消,放眼是一望無際的蓊鬱綠地,石頭城市點綴其間,沿河可見牛隻與孩童同在河中戲水,隨船逐漸接近古堡沙洲的遊客於是不免好奇:不知道葛羅休斯被押往路浮堡的時候,河上是否也有如此悠哉美景?
不過發思古之幽情永遠都是後人的奢侈,在葛羅休斯被監禁在路浮堡的年代,那裡即便在夏日也陰冷得足以致病。葛羅休斯在路浮堡兩年,確實疾病纏身,所幸他在 1621 年成功越獄,從此奔向自由,而今年 3 月 22 日正是他越獄成功四百年週年,這也成為 2021 年路浮堡博物館的主題活動。

古堡慶祝有人逃走滿四百年的奇怪活動
葛羅休斯在國際上大名鼎鼎,在荷蘭也是家喻戶曉的人物,但多數荷蘭人並不知道葛羅休斯到底有什麼偉大的成就。事實上,葛羅休斯在一般荷蘭人心目中就只是那個「躲入書箱從路浮堡越獄成功的人」而已。這知名(也大致準確)的故事說,葛羅休斯作為高級政治犯,被允許和妻小一起住在路浮堡內,他的妻子可以在堡內自由走動,到廚房為他料理三餐,但他只能在臥室和書房之間活動。葛羅休斯是個高級知識份子,被允許和外界通信,也可以接受外界送來的書籍。他的妻子觀察到古堡守衛逐漸鬆懈,不再檢查進出的書箱,於是設下書箱越獄的計謀。葛羅休斯果然於 1621 年躲入書箱,被當成書籍運出路浮堡,之後他逃離荷蘭,轉往巴黎,成為法王路易十三世的宮廷一員。
葛羅休斯書箱越獄的故事之出名,讓荷蘭各地都有博物館宣稱他們擁有當年裝過葛羅休斯的那個書箱最知名的有路浮堡、位於阿姆斯特丹的荷蘭國家博物館以及台夫特的王庭博物館等,其中又以國家博物館的書箱看來最是逼真,雖然其中究竟早已無從考證。
⇩ 圖為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館藏「葛羅休斯的書箱」。

雖然路浮堡所展示的書箱明顯的太過年輕,不大可能是從十七世紀上半葉流傳至今,但古堡本身所能提供的現實感,絕對能夠從四面八方將想要體會歷史的遊客兜頭籠罩,勝過其他任何主張有「葛羅休斯書箱」的所在。遊客下船登上沙洲之後,後很快就會感受到這一點。
來訪的遊客首先要前往古堡周遭建成年代較晚的磚造建築,在這裡的售票處購票,拿到一本折疊式的導覽手冊和一個可以掛在脖子上的鑰匙,是進入古堡及堡內聽取語音導覽所必須的感應工具。

帶著鑰匙通過護城河上蛛網纏身極其厚重的吊橋,經過隧道般的古堡大門,就來到路浮堡的中庭。光是站在這中庭仰望天空,就讓人感覺氣息迫促。遊客走上一道梯級進入堡內之前,往往會下意識的回頭再看這狹隘的中庭一眼。四個世紀前的葛羅休斯可能也有過這樣的舉動。那是一種一旦踏進門內,此生可能連這囿人的中庭都再也見不到的困苦感。

路浮堡內隨處可見博物館設計之陰險。當遊客走在只容一人既狹窄又陡峭的石梯上,正想抱怨堡內陰風甚慘,下一個轉角就迎面撞上一個刻著字的金屬裝飾箱,從裡面透出的燈光將那一行字投入遊客眼中:
「不要害怕死亡,那就是生活!」

路浮堡內關押過的政治名人不少,堡內有一個寬廣的空間專門介紹這些人物。不過獲得古堡博物館特殊待遇的唯有葛羅休斯一人,因為書箱越獄的盛名之下,路浮堡在一般荷蘭人心中幾乎就等同於葛羅休斯。古堡內保留著他當年的臥室和緊鄰的一間小禮拜堂,也是他當年的書房。遊客踏進他的臥室,會聽到十七世紀荷蘭的音樂,可能是當年葛羅休斯所耳熟能詳。房間裡可能突然出現投影,介紹葛羅休斯在此度過的兩年生活。石頭古堡本來陰冷,十七世紀歐洲又正逢小冰河期,十分寒凍,葛羅休斯經常生病,往往抱病讀書寫作。他在獄中與外界通信十分頻繁,以 1621 年為例,他在 3 月 22 日成功越獄之前,自 1 月 10 日到 3 月 6 日總共寄出八封信,其中有三封寫給他弟弟,越獄前幾天的 3 月 17 日則收到一封信。葛羅休斯寄出的信件視通信對象的習慣,分別以拉丁文、荷蘭文和法文寫成。
除了神學與法學著作,葛羅休斯還留下大量的書信,已經集結出版,總共十七鉅冊,近年來也由荷蘭文學數位圖書館完成數位化的龐大工程,任何人都可以免費閱讀。但儘管資料俱全,如今卻很少有人能讀這些文獻。同時能讀拉丁文、荷蘭文和法文的人或許不算太少,但同時通曉十七世紀拉丁文、荷蘭文和法文的人就很少了。在二十一世紀的荷蘭也只有歷史學家范依塔松一人以「葛羅休斯專家」的身份為人所知,下圖便是經范依塔松校註出版的《論戰利品與捕獲法》,《海洋自由》其實本來是這大書的其中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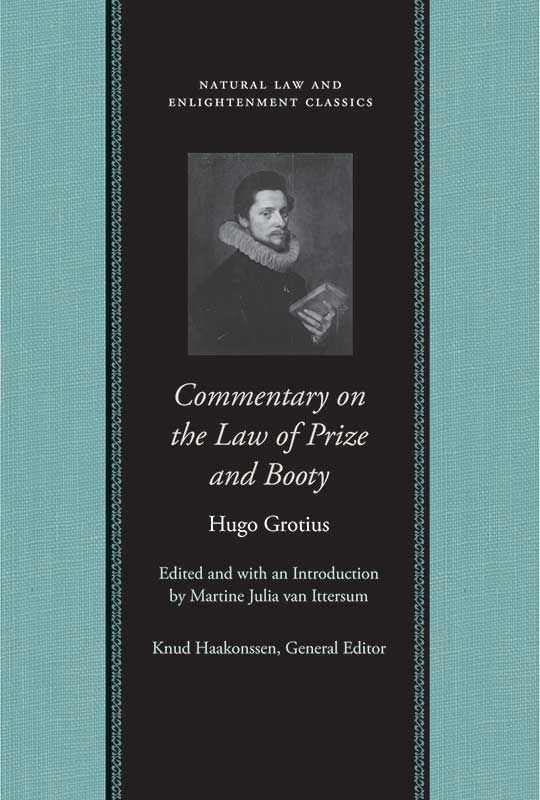
除了十七鉅冊的書信,荷蘭國家檔案館也有兩個葛羅休斯檔案,收藏他的外交書信和個人通訊,但這些文件除了極少數有專業能力的研究者以外,當然也無人能讀,可能也是因為研究的人少,這些文件至今沒有數位化,研究者只能苦哈哈的在檔案館讀傷眼的微膠卷。
能夠閱讀第一手史料的話,當然就能夠對葛羅休斯其人有更貼切的了解,但時間為一切設下了限制。國家檔案館的史料也好,已經出版的書信集也好,對一般人而言門檻都太高了,相形之下,書箱越獄的故事和屹立瓦爾河畔的中世紀古堡,就成了一般遊客體驗歷史的最佳去處。
其實就算是專業的歷史學家,也往往需要這種親身的經驗,才更能在歷史文章中注入一種跨越時代訴諸人性的理解。我自己就有這樣一則關於葛羅休斯的經歷。那是大約十年之前,我為《新荷蘭學》一書撰寫關於荷蘭史的一章,以葛羅休斯作為了解荷蘭獨立建國史的線索。我從當時所在的萊頓大學(也是葛羅休斯就讀的大學)去到葛羅休斯出生的台夫特,踏進他襁褓時期受洗、客死異鄉後還葬的台夫特新教堂,逛過領導獨立革命卻遇刺身亡的奧倫治親王所居的王庭,之後轉往海牙、鹿特丹等他曾經工作過的城市,幾乎踏遍了荷蘭境內與他有關的地點,最後在一個淒風苦雨的十一月天首度造訪路浮堡,當時與我共遊的人也包括我們的檔案學教授燕鴴什先生。
冰冷的路浮堡有一股震懾人心的力量,讓當時走入古堡的眾人都自然沈默下來。我在進入葛羅休斯如今空無一物的臥室後,發現有一個鑿進牆中的廁所。那個只容一人坐上的「馬桶」其實就是一個厚實牆內的豎向坑道,排泄物由此直接落入下方深處連通護城河的不明渠道。我按耐不住好奇,坐上那個十四世紀的「馬桶」,儘管穿著厚重的冬衣,還是感覺一股難以形容的陰冷上襲。我於是比沒有造訪路浮堡之前更加明白,那「永恆的」監禁是何等況味,渴望為戰爭與和平立下正義標準的法學家,又為何非要冒死逃離這座對一切無動於衷的囚牢。

一段時間之後,我和燕鴴什及其他友人循著參觀路徑回到起點。這個起點也是我們旅程的終點。我們再次魚貫通過紅漆的木門,踏進細雨霏霏的中庭,大門甬道彼端就是護城河上的吊橋。那吊橋與我們來時並無二致,但一進一出之間,那暢通無阻的道路已然成了「自由」的具象。我們在碼頭邊等待渡船的時候,也恍然這廣闊的水道不必然代表今日通航的自由,因為它曾經也是監禁與阻撓的手段。「海洋自由」這個看似常理的概念為何晚至 1609 年才被葛羅休斯付諸筆墨,似乎也就不難理解了。
今年是葛羅休斯越獄成功四百週年,許多人期望著 3 月 22 日能有慶祝活動,但目前荷蘭瘟疫肆虐,已經開始實施宵禁,屆時情況如何還未可知。若是路浮堡無法正常舉行活動,想必會有很多人失望,不過葛羅休斯地下有知,應該不會太過介意。因為他影響後世最大的著作《海洋自由》早已告訴我們,智識上的空間一旦被創造出來,就再也不能抹滅,物理性的空間反倒成了其次。自由首要在於人的意念和理解,於是而使海洋成為自由的海洋。
⇩ 圖為台夫特新教堂前的葛羅休斯雕像。台夫特新教堂是荷蘭奧倫治拿騷王室的墓地,葛羅休斯的雕像能夠佇立在這座教堂之前,表明了他在荷蘭歷史上無可取代的地位。

再回到故事一開始的小書《海洋自由》。
如果沒有當年令全歐洲啞口無言的《海洋自由》,荷蘭東印度公司無法在遠方累積大量的財富,在歐陸打贏八十年獨立戰爭,並造就十七世紀荷蘭的「黃金年代」。而 1648 年終結歐洲宗教戰爭的《西發利亞和平條約》,則是葛羅休斯《論戰爭與和平法》的具體實現,雖然他已經在那之前三年因船難病故了。葛羅休斯生於戰火,長於戰火,死於戰火,或許唯有戰爭之子最是渴望和平,最終也以他的法學理論為歐洲奠下和平的基礎。這樣的歷史理解和體驗,我們無法在檔案裡獲得,只能在我們的內心與環境互動的過程中體會。

有了在檔案館外遇見歷史的經驗,接下來讓我們再回到檔案館,談談什麼是城市檔案館?城市檔案館都在做些什麼?(歡迎提問,可以插隊)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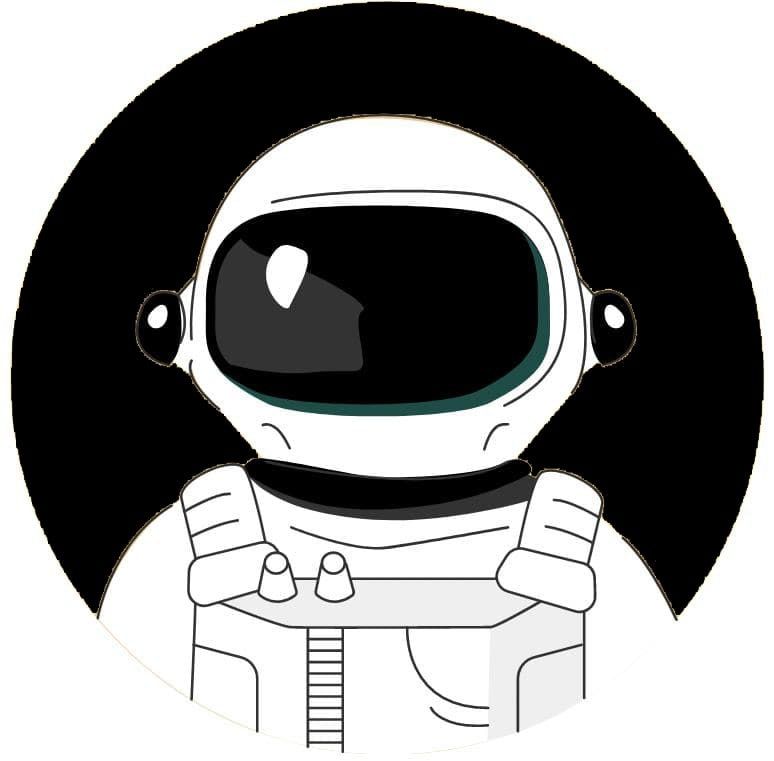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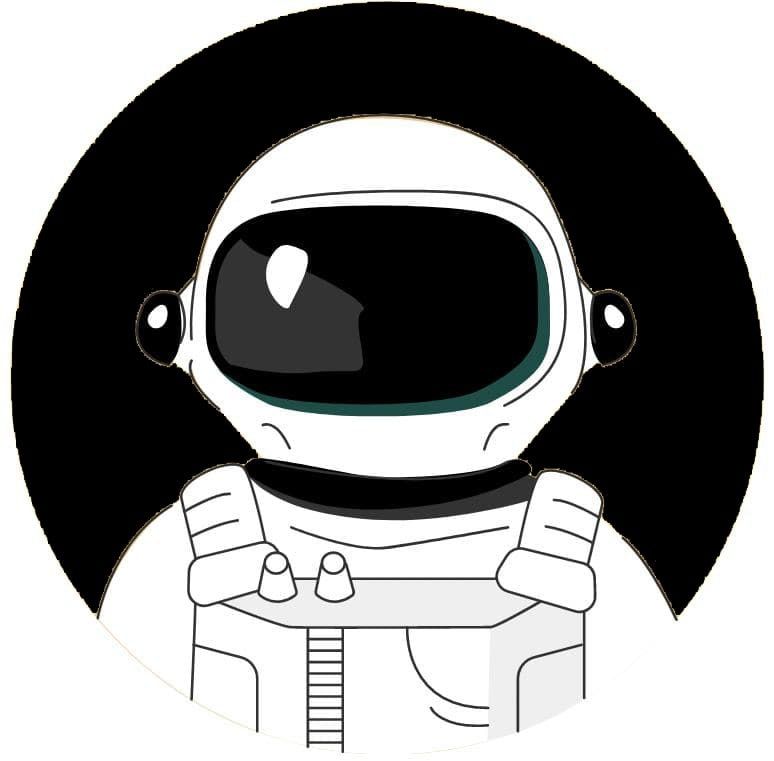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