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的預言之後:讀Katherine Mason《傳染之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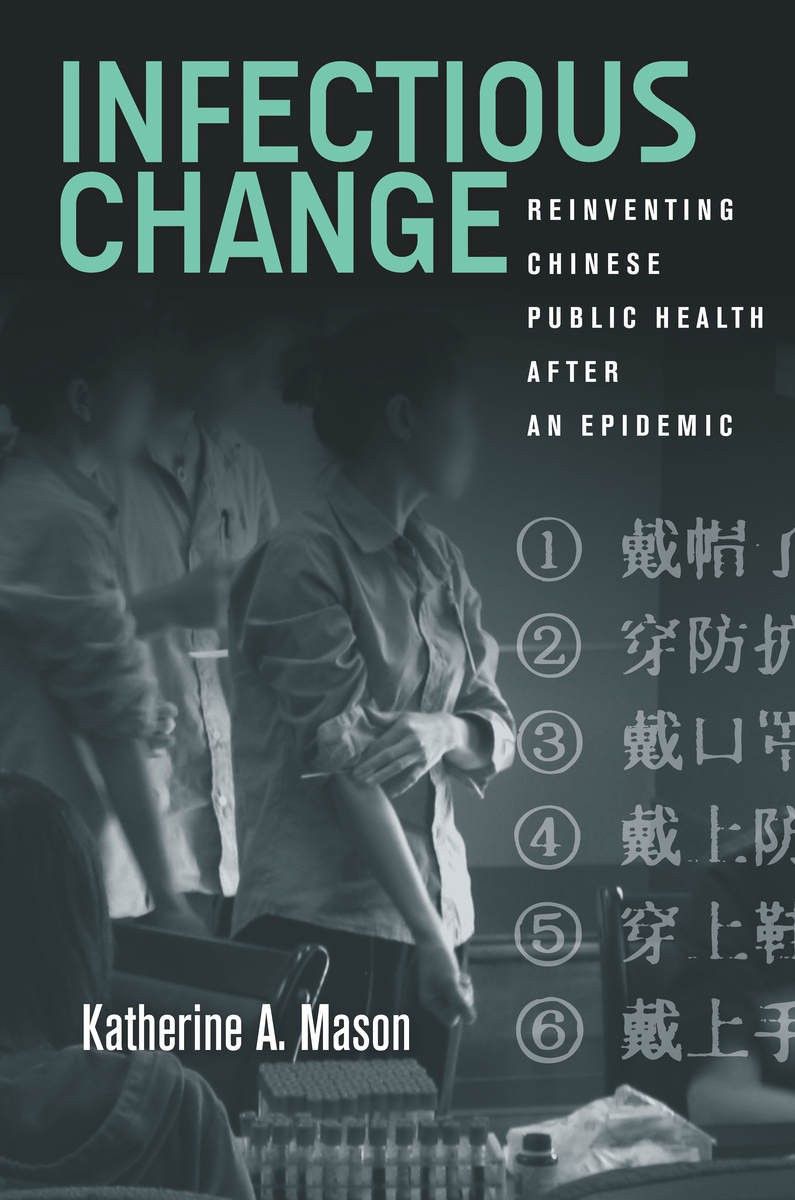
Katherine A. Mason, 2016, Infectious Change: Reinventing Chinese Public Health After an Epidemic.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去年五月,人類學家Katherine Mason在Cultural Anthropology網站上發表了一篇文章,為自己年初信誓旦旦預言「COVID-19不會全球大流行」失敗的事情道歉。她說:「在2000年代末,我花超過一年的時候進到中國當地的公衛組織,觀察第一線的防疫準備,訪談了中國和香港超過百位的公衛專家,也拜訪了WHO以及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的工作人員。如果有任何人能夠預見這場即將到來的災難,那個人應該是我。(……)可惜我在這件事上大錯特錯。」
然而在文章裡,Mason也有點為自己辯護地說,她還有是有說對一些事的。比方說,自疫情以來,歐美國家出現對中國人的無端、污名化想像。或者,她也曾指出武漢的確診人數被刻意少報。只是在最最關鍵的一點上,她錯了。
讀這樣的道歉文,我總忍不住困惑,在失敗的預言以後,Mason要如何自處?我們作為讀者,又要怎麼面對她以往的作品?我們還能夠付出同等的信任,相信書中所記所寫嗎?
正如她自己所述,Mason這本《傳染之變》是她在2008年來到中國珠江三角洲的城市,觀察了中國公衛系統在SARS之後狀況的作品。在這本書中,她的核心問題非常簡單:誰構成了公共衛生和防疫系統裡頭受益的「公共」?
Mason以防疫中「隔離」的例子說明,我們願意接受隔離,不僅因為我們相信這樣有益於「社會群體」,更關鍵是我們知道,這件事情是隨機發生的──今日我願意接受隔離(犧牲),是因為改天我同樣可以接受到其他人因病隔離而帶來的好處。然而Mason問:如果固定都是某群人在享受利益,又是某群人被迫犧牲時,又會是什麼狀況?
以全書第一章為例,Mason討論的是中國城市裡的流動人口──這群從鄉村湧入到城市爭取更好的工作機會與生活的人礙於中國的戶口制度,難以真正定居城市,也難獲得相關權益的保障。自SARS之後,中國也積極借鑑美國的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模式,建立新的公衛系統,並勾勒一個更現代、文明的發展藍圖。然而Mason指出,這些難以落戶的流動人口從未被納入這個文明之夢,長期被排除在中國新的公衛系統之外,成為「城市衛生的潛在威脅」,是「城市疾病的帶原者」。換言之,這群流動人口被視為要嚴格控管的、抹除臉孔與故事的「群體」,透過隔離(或犧牲)他們,換來了一個公共衛生高度進步和安全的城市。

《傳染之變》的每一章,都在處理一個不同的「公共」想像。例如剛提到的流動人口和「文明社會」的對照。又例如一群新晉的年輕公衛人員企圖要破除應酬、人脈等等關係,建立起的「科學社會」。在這個想像裡,機關裡的應酬飯局和關係照應被視為妨礙科學與科技進步的陋習,年輕的公衛人員認為應該要建立一套更客觀、不受干擾的公衛系統運作模式。然而這個夢想因為中國組織的科層架構和人脈網絡,層層掣肘,而往往難以企及。
透過這些「公共」想像,Mason要講的重要一點是,中國自SARS以後努力發展的公衛系統在建立不同現代、文明的進步「公共」社會圖像時,也同時創造了許多被排除在這些「公共」想像外的犧牲者。這些被排除的人群──Mason引用了先前提過的Lisa Stenven的討論──被化為統計數字和「威脅」,不再產生意義。一言以蔽之,Katherine Mason要講的就是,中國新的公衛系統在勾勒進步國家、防疫準備有成的藍圖時,也離實體的、一個一個的人愈來愈遠了。
讀《傳染之變》這本書,看Mason論及中國公衛系統的層層關係網絡,基層人員怎麼「謊報」公衛調查的數字,不同的想像又怎麼分類人群,並創造污名,讀者大概很容易像我一樣困惑:是啊,你既然看見這些問題,為什麼會如此相信武漢的肺炎不會成為新的全球大流行?
端倪或許就在草率結尾的第二章。在講了年輕、懷著「科學」夢的公衛人員和舊有常「應酬」的公衛人員的對抗後,Mason這麼作結:2012年底習近平成為了新的中共領導人後,他展開個人的第一次南巡,並同時宣示了高度反貪腐的訊息。在這之後,應酬飯局不再盛行。雖然來自於國家的力量而非年輕公衛人員們的努力,但終究他們還是獲得了勝利。「勝利終是勝利。」她寫道──Mason在《傳染之變》這本書裡聚焦於城市的公衛中心,看見當地工作人員在SARS之後重建的公衛系統下的掙扎與努力。然而她似乎沒有看見、或不敏感的是,中共政權的力量──對人民生命的治理、地緣政治格局、極權國家的特殊性──遠遠不是單純一句「勝利」就可以概括的。
故事的後續我們知道了,就是2020年的失敗預言。雖然那些強調自己努力和作為的段落讓後來的道歉文顯得有些尷尬,但Mason在這篇文章裡有一點或許講得沒錯:如果有人可以預見這場災難,那個人本應該可以是她的。
可惜。
Katherine A. Mason受業於Arthur Kleinman,在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取得人類學博士,現任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人類學助理教授。Mason因為自己在中國擔任英文教師並遭遇SARS疏散的經歷,而開始進行對中國公衛系統及流行病的研究。Mason長期關注流行病的論述與文化意義,並在COVID-19疫情期間多次公開發表評論與倡議。《傳染之變》是她的第一本書。
關鍵字:醫療人類學、流行病、公共衛生、中國、亞洲研究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