純粹的惡,納粹的集中營-滅頂與生還
善與惡不是二分法可以分得清楚的選擇題,但真正的惡還是能讓人辨識出來,因為它會讓人陷入絕望。
納粹在二戰時期的暴行,對現代人來說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為所有人都從歷史課本裡,或多或少的聽過學過考試過。但陌生,是因為所有人都不清楚,這些暴行背後的影響。納粹集中營真正的惡不只是毀滅種族,也不是刑求虐殺。
而是徹底剝奪人類身而為人的意義,抽乾加害人與被害人的靈魂。
《滅頂與生還》放到現在來看,仍是全世界的警鐘,提醒我們小心那些宣稱組織化、合法化的暴力,以及那些說有其需要的預言家和夢想家。許多人心懷惡意,說衝突才是歷史的常態,說歐洲從來沒有和平超過四十年。這些都是強詞奪理,不管在什麼情況下,戰爭和暴力都是不必要的。預防性暴力也只會引發更多的暴力。
撒旦,不管在任何時候都是不需要的。
這本書也告訴了我們懶得動腦、短視近利的群眾多麼可怕。享受追隨強勢領導者的安全感,並隨著領導者的肆無忌憚而更堅定追隨的信念。與領袖被擊倒時一併被擊潰,沉浸在失落的哀傷、痛苦和悔恨中。然後在短短幾年之後,就又在不公平的政治遊戲中,找到讓自己心安理得不用負責的說法:
我們(這個群體)是被體制蒙蔽的罪人,沒有勇氣的聽從命令的懦夫,只有上帝可以赦免我們的罪。
在現代的時空背景下,人們有很多發自潛意識裡的疑問,很容易拿好萊塢的英雄片做比較,拿那些堅忍不拔、苦難中成長的"英雄"當作心目中的範本,而千篇一律的問受難者們,為什麼不反抗?為什麼不逃離?為什麼不能事前避開?
但這是生活在現代才會有的疑問,在那個無視法律,沒有常規處置的年代,逃脫回家的人更可能被視為間諜。這群囚犯,更多的是老弱婦孺,沒有受過軍事訓練,終其一輩子都在農場、店裡工作。怎麼給予其他人希望團結、如何抵抗而不被殘忍的殺害?就算僥倖逃出鐵絲網,但甚至不知身處何方的他們,要去哪裡?怎麼活下來?親戚、家人、朋友都死光的他們,能怎麼辦?
會有這些問題的群眾們,沒有能力直視罪惡,他們不敢相信罪惡可以如此純粹,又無法被打敗。一定是有什麼環節錯了,才會導致這樣的慘劇;一定是不夠努力,才會承受如此的苦難。
事出必有因,許多人都認為罪惡是互相的,但或許真相就是如此平庸,平庸的決定、平庸的生活。
所以我們才要練習看見真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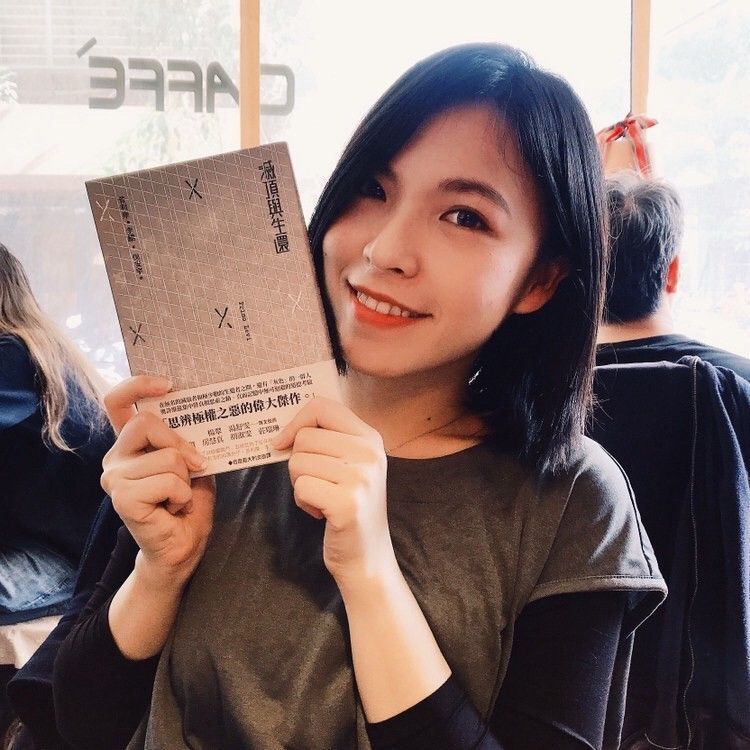
灰色的記憶
納粹親衛隊的軍官以輕佻語氣警告集中營囚犯為樂:「不管這場戰爭最終結果如何,對付你們的這場仗我們贏定了。你們沒有人能活下來作證,就算有人倖免,這個世界也不會相信他。或許會有人懷疑,會有討論,歷史學家會做研究,但是沒有人有十足把握,因為我們會把證據連同你們一起銷毀。即便保留了部分證據,即便你們之中有人倖存,其他人也會說你們陳述的那些事太可怕令人難以置信。他們會說那是同盟國的誇大宣傳,不會相信你們,會相信我們,而我們會否認一切。集中營的歷史將由我們書寫」
歷史都是勝利者撰寫,所幸,這段歷史沒有被淹埋,隨著德軍在史達林格勒的失敗,原本草草執行的湮滅證據計劃,被加速執行,許多資料被摧毀,但百密一疏還是留了許多資料。只是加速湮滅證據的計劃讓納粹的暴行更令人髮指,集中營的犯人被迫挖出自己上百萬同袍的屍體,露天架起柴堆焚燒;關閉原本分散的集中營,不問生死的趕著囚徒遷徙到德國內陸。
集中營另一項恐怖的記憶是,逼迫受害者生存的體制下的共謀。
不可能充足的糧食讓人們在虐待、勞動、嚴寒、疾病下,兩到三個月就會能量消耗殆盡而死,不論是生理或是心理上。為了活下去,集中營的囚犯不得不爭奪所剩無幾的物資。納粹軍官也樂得讓這些人負責管理囚犯,但為了要確保集中營囚犯不會背叛納粹,只能讓這群囚犯的手上留著更多自己同胞的血。
這段歷史讓人絕望的不只是納粹軍官,而是理論上應該還保有人性的德國知情人民,但舉凡工業公司、農場、街訪鄰居,都因為受惠於集中營帶來的利益,而自成一個宇宙,刻意視而不見。這些沒有參與執行卻又知情人民、軍官到了戰後依然留在那個宇宙裡,說著他們自己的語言。
這些人很難否認自己做了某個行為,或否認這個行為發生,但很容易捏造做這些事情的背後心理動機,以及行為發生當下的情緒反應。但這個問題的答案並不可靠,心境總是會變,而要記住當時的心境無異是胡說八道。
這些心理動機最常見的說法是,我身不由已,不得不聽從命令。
無用的暴力
納粹常常使用無用的暴力,為施暴而施暴,只是為了製造疼痛。有時候納粹的暴力有其目的,但往往使用了過多、與目的不成比例的暴力
納粹在挺路運送囚犯時,有許多常態或非常態的要求。常態的要求是虛情假意的建議(命令),讓不知情、面對未知恐懼的人,盡可能的帶所有的財物,甚至是家畜。納粹軍官總是意有所指地說你們都會用到,但那只是監守自盜的謊言,為了更方便的搶奪財產。
運送囚犯的火車都是光禿禿,是真的光禿禿的車廂,沒有物資、飲用水、鋪在地上的稻草,甚至沒有廁所。而這趟火車之旅總計兩個禮拜,中間只會停車兩到三次。只多囚犯在停車的時候來不及到旁邊比較隱密的樹叢,只能就地在月台或是鐵軌旁,像牲畜般被車上的軍官恥笑。
這還只是序幕,進入集中營之後,所有人必須一絲不掛,連毛髮都須被剃除,一周一次。好不容易拿到的便當盒有三種用途:領取每日分配的湯;夜裡不能外出的尿壺;盥洗槽有水時拿來取水盥洗。吃飯的時候沒有湯匙,雖然集中營的倉庫推積了許多搜刮囚犯來的湯匙。
來到集中營的犯人還需要刺青,刺青方式體現德國人分類上的天才,男人次在手臂外側,女人刺在手臂內側;吉普賽人的編號首字母是Z、猶太人是A後來改成B。刺青的過程不是很痛,大概只花了一分鐘,但遺留的心理創傷很大,這是無法抹滅的記號,就像奴隸和要被送去屠宰場的牲畜的記號。
但最可怕的事是點名,每天不論天氣如何,所有囚犯都必須到室外點名,幾萬個囚犯以五個人為一組點名,至少要花一小時,如果人數兜不起來,則要花二至三小時。萬一懷疑有人逃亡,甚至會超過二十四小時。如果遇到下雨或是寒流,這種不知盡頭的慢性折磨,比酷刑還更痛苦。
純粹的罪惡
沒有任何一個宗教能包容追隨魔鬼的人,也不會接受把自身罪刑推諉給魔鬼的辯解之詞。每個人都應該會自己犯的罪行和過錯負責,否則人類文明會從地球上徹底消失,就跟納粹德國一樣
來自義大利、法國、希臘人還有部分猶太人聽不懂德語,也無法溝通,這些聽不懂德語的囚犯往往來這裡的十到二十天內就會死亡。這些人表面是死於寒冷、飢餓、勞累和疾病。但真正的死因是資訊不足,不知道怎麼跟資深的同伴溝通,獲取適應環境、如何找出衣服和鞋子、額外的食物和避開過於辛苦的工作。
最重要的是不知道如何避開危險的軍官,軍官往往認為猶豫不決的人是不想執行命令,而拳打腳踢直到他們聽懂為止,這群可憐的囚犯,只能澀澀的縮在角落,希望苦難有離去的時候。
集中營有一群特殊的「特遣隊」,但他們的特殊之處只在於多幾個月可以吃飽而已。這群由囚犯組成的特遣隊奉命管理焚化爐,就是那群被送進毒氣室同胞的最後歸所,他們還要拔出死者口裡的金牙、剃掉女性死者的頭髮,將衣服、鞋子和行李分門別類的放好。屍體運送進焚化爐後,再把骨灰移出滅跡。
特遣隊一共有接續的十二個,會友前前後後十二組,是因為知道真相的人,都必須死。
模糊的真相
沒有人知道自己的靈魂在屈服或碎裂之前可以撐多久,又經過哪些磨難和考驗。每一個人都擁有自己不知道的潛在力量,這個力量可大可小,或是沒有,唯有在艱困逆境中才有機會衡量。
只是又有多少人能活著衡量到最後。
最可怕的惡,不只是毀滅肉體,同時能摧毀靈魂。被摧毀過的靈魂的世界崩然轟塌,為了保護自己還能活著,生物的本能會自我催眠,就算這裡是地獄,但我是在花園。但這裡究竟是地獄裡的花園,還是花園裡的地獄,亦或是花園還是地獄,都不再重要。
重要的是什麼,失去了靈魂的肉體無法給出答案,是活著嗎?還是為了復仇?但現在只能本能地活著。
因此,身處過集中營的人們都習慣說謊,也可以說是,說出自己心裡的感受,無論是加害者或是受害者。因為在這段時間裡,他們都是活在情感、理智麻木的時空裡,與我們一般認知的世界隔絕開來,尤其是越平庸的人,只能試著說更多的謊來平衡真實與想像的世界。
尤其是在重獲自由後,感受活著的真實與發現真實的那份痛苦,猶太受害者們近乎一無所有,家庭破碎、親友罹難。這讓許多人感受不到真實,只是不知所措的情感空白。他們還需要時間,不過這種空白感會伴隨他們一輩子,時不時的出現。
許多自由的囚犯自殺了,其中的許多人是立刻自殺了。
所以我們必須把納粹的加害人,從自欺欺人的謊言裡揪出來,他們固然是體制下的惡的承擔人,但說自己作為軍人,不得不接受命令是最不負責任的說法。在納粹德國十二年的生涯,選擇加入並妥協的人,就是抱著投機心態,放棄原則的人。
只是缺乏自制力反省的體現。
另一方面,真正的罪,是當年幾乎所有德國人集體性、全面性犯的罪,也在於他們沒有勇氣開口。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