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各宾丨从独自打保龄到独自发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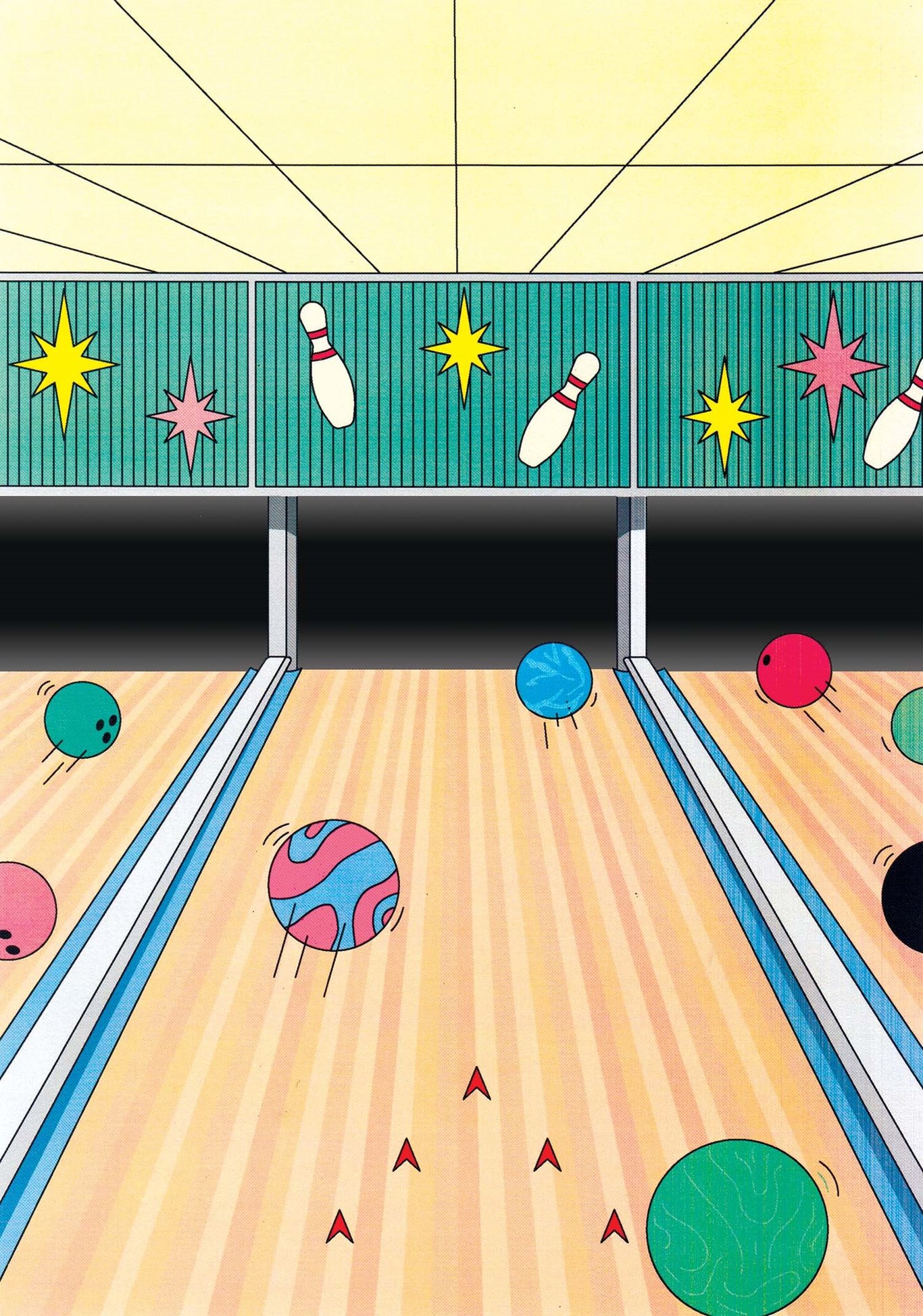

译按
本文作者安东·耶格尔(Anton Jäger),是比利时天主教鲁汶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
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普特南2000年出版的专著《独自打保龄: 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指出,临近二十世纪末,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打保龄球,但他们是独自打保龄球,与此同时,包括教堂、工会在内的社区组织日渐萎缩。本文作者认为,二十年后,美国人的独自打保龄演变成了独自在网上发帖,政党民主的支柱被继续掏空,结社程度的下降对左翼构成了比对右翼更严重的打击。
本文原题“From Bowling Alone to Posting Alone”,见于《雅各宾》杂志第47期(2022年秋季号),2022年12月5日上线。《雅各宾》,是一家反映美国左翼立场的季刊,设在纽约,旗下产品包括印刷版季刊、同名网站等。
正文一万四千余字,其中超链接和绘图为原文所有,摄影图片和图说为译者添加。
译者听桥,对原文有多分段,并对一些段落感到费解。
从独自打保龄到独自发帖
安东·耶格尔(Anton Jäger)
去年,美国生活调查中心(Survey Center on American Life)发表了一项追踪美国人友谊模式的研究。这份一点也不振奋人心的报告记录了某种“友谊衰退”。报告提到美国人是如何越来越孤独和离群索居的: 12%的人眼下表示,他们没有亲密的友谊,而1990年这一数字是3%,近50%的人表示,他们在新冠大流行病爆发期间失去了与朋友的联系。心理后果是可怕的: 心脏病,睡眠中断,患上老年痴呆症的风险增加。友谊衰退已具备可能致命的后果。[去年,是指2021年。美国生活调查中心,隶属于美国公共政策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译注]
该中心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广阔得多的进程的小型化模型,那一进程在过去三十年里已征服了美国以外的国家。作为典型的志愿性结社,友谊圈取代了我们集体生活中的其他机构:工会、党派、俱乐部。法国哲学家让-克劳德·米歇阿(Jean-Claude Michéa)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在他的童年时代,最令人不安的时刻之一,是他发现村里有人不是共产党员的那一天。他回忆道,“那看上去不可想象”,就好像那些人“生活在社会之外”。并非巧合的是,1968年5月,法国学生有时将工人与共产党的关系和基督徒与教会的关系相提并论。基督徒渴求上帝,工人渴求革命,但“基督徒得到了教堂,工人阶级得到了共产党”。(让-克劳德·米歇阿,生于1950年,自由至上社会主义者。——译注)
米歇阿的父母是共产党人,他认为党是一个更基本社会单元的延伸。友谊模式往往充当了更广泛社会趋势的有益指标,Vox 的记者很快将这些数据应用于政治分析。研究人员援引了汉娜·阿伦特的名言: 友谊是抵抗威权主义的最佳解药。在1951年的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结尾,阿伦特假定,一种新形式的孤独已征服二十世纪的西方人,导致他们加入了新的世俗异教团体,以补救他们的灭亡。她声称: “在非极权主义的世界,令男人准备好应付极权主义统治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孤独一度是一种混沌不清的体验,通常是在比如衰老这样的边缘社会条件下才会经历到,但眼下已成为一种日常体验。”
结论是明确的。眼下,随着美国人在新世纪变得更加孤独和离群索居,同样的极权主义诱惑若隐若现。
帕特南的警告
对社会科学家来说,这一评价一定听上去耳熟能详到令人疲乏: 是二十一世纪初政治科学的经典作品之一、罗伯特·帕特南2000年出版的著作《独自打保龄: 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的存货。
本书注意到一个奇特模式: 临近二十世纪末,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打保龄球,但他们是越来越独自从事这项运动,许多保龄球联盟的突然衰落是最清楚的解释。这一危机绝不仅限于体育俱乐部。从教堂到工会,从射击场到共济会会所,所有这些组织都在1980和1990年代经历了会员人数的急剧萎缩,并开始解散。留下的只是一片社交荒地。
帕特南胪列了这一大规模解纽过程的多方面原因。1960年代,诱惑中产阶级从城市中心涌向郊区的潮流鼓励人们过一种私密的生活。离开了美国城市的公民,最终住进了主要为开汽车的人士设计、没有人行道的郊区。在战后的繁荣时期,消费变得民主化。人们将更多时间花在了他们的汽车上,那是一个私人占有的移动公共空间。为给购物中心让路,街角的商店被推平了;火车轨道被高速公路取代。随着女性稳步进入劳动力市场,志愿者协会失去了核心的支持基础。员工开始比他们的父母工作更长的时间,而且发现他们很少有时间做志愿者。晚间,电视将公民锁在了家中: 那里成了战后孤独的墓碑。
帕特南还驳斥了有关这场公民社会危机的一些重大误解。首先,福利国家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这种观点认为,社会服务从社区转向国家层面,会威胁到公民的自力更生。帕特南对此表示怀疑: 强福利国家(北欧)和弱福利国家(美国)都见证了公民能力的衰落。在法国和比利时,“红色”公民社会甚至被允许管理部分社会保障预算。围绕种族融合的争论也证明了一个不充分的解释: 美国黑人和白人都退出了俱乐部,与此同时,各种族群体之间的整体不信任正在减少。
帕特南也不喜欢包治百病的神药。还在2000年,他就预言,互联网将为那些老派协会提供劣质替代品,并强化反社会倾向。2020年大流行病期间,这位在他新罕布什尔州的家中离群索居的社会科学家为新版《独自打保龄》补写了一则后记。其基调是典型的忧郁:“互联网使用与公民参与之间的相关性”是不存在的,未来是“网络巴尔干化”而非“数字民主”。“社会资本”的存货尚未得到补充。
时间的考验
到本世纪初,这一思路的弱点已经显而易见。一方面,《独自打保龄》几乎没有着力调查美国公民社会的结构性转变:新型非政府组织代替群众性会员组织的兴起,新型体育俱乐部的增加,福音派大教堂和学校中结社的复苏。
帕特南还使用了一个非常可疑的概念:社会资本。在这方面,本书论及1990年代后期的市场友好型情感: 公民纽带作为社会流动的一种手段而非集体权力的表达,是有所裨益的。它们可以装饰大学申请表,或帮助人们获得实习生项目,而不是改变国家或发动革命。
这种经济主义也解释了帕特南书中一个明显的豁口:那个世纪结束之际工会实力的急剧坠落。一本超过五百页的著作中,没有“去工业化”这一索引条目。《独自打保龄》绝少触及资本的咄咄逼人如何造成公民社会的衰落,以及对整个公民生活而言工人力量是多么有代表性,有关劳工的讨论也是有限的。工会会员人数的减少不只极大影响到左翼,还令右翼迷失了方向,故事的这一面几乎没有在《独自打保龄》中呈现。
但尽管存在这些明显缺陷,帕特南的著作还是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统计数字仍然显示,许多世俗性的会员组织在持续衰落。尽管公众对工会努力的支持率不断攀升,但2021年,美国的工会化率仍下降了0.5个百分点,仅为10.3%,回到了2019年的水平。从因新冠疫情而实施的封控,到传统政党的规模不断缩小,过去十年的政治发展也证实了帕特南的直觉。不只如此,他的著作现在还被用来解释唐纳德·特朗普时期的不确定性:在特朗普任内,对1980和1990年代公共领域的有控制破坏驱动了一种新形式的怨恨政治。
2010年代的超政治(hyperpolitics)也很难撼动帕特南的论点。虽然交互式的互联网已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独白式的电视机,但新媒体开创的归属感和地位的普遍危机并没有减轻。哪怕在一个愈发高度政治化和被党派冲突严重撕裂的社会,从国家到工会再到社区团体,集体行动的杠杆依旧脆弱。尽管一些部门的激进情绪高涨,但正如丹尼尔·萨莫拉(Daniel Zamora)所论,新冠疫情下的劳动力市场紧张所引发的“大辞职”并没有造就集体发声的政治,毋宁说导致了一种个人的“退出”。欧洲的工会也遭遇了类似的命运,会员流失,成为自雇人士。虽然帕特南注意到,2020年总统选举中投票率上升了,但这是“独自投票”,与十九世纪人们被组织起来,成群结队前往投票地点的情形有绝大不同。
这里既有推动因素,也有拉动因素。自1980年代以来,利用反工会的立法或全球化的劳动力市场,协会主动驱逐了公民。与此同时,廉价信贷、自助、加密货币和在线论坛,这样一些工会和政党力量之外的被动选项却成倍壮大了自己。结果是,一个越来越封闭的世界形成了。正如评论员马修·伊格莱西亚斯(Matthew Yglesias)所警告的那样,在这样一个世界,家已经成为愈发舒适的源头,使得公民可以在不用离开的情况下展开互动。他宣称,“独自在家已经变得不那么无聊了”,这形成了一个我们都可以在其中“独自冲浪”的世界。这在公民那里将造成可怕的结果。
来自左翼的帕特南
这样,以下我们就来到了帕特南命题的理性内核: 1980和1990年代,远在保龄球馆之外,西方社会生活确实早就变得越来越原子化了。这一结构调整的经济理据是显而易见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已被证明是对帕特南支持者观点的有益补充: 个人化是资本的铁律,为让市场找到新的积累途径,必须减少集体生活。到1980年,各州可以要么切断与现有公民社会组织的联系,并摆脱通货膨胀的威胁,要么面对不断膨胀的公共债务。
这严重限制了2008年金融崩溃的应对举措。在信贷危机的短期混乱背后,存在一个漫长得多的过程: 自1973年经济衰退以来,政党民主的缓慢但稳步的衰落。政党也仍然是帕特南笔下解纽的典型受害者。作为建立在个人和他们的国家之间的堡垒,政党机构在整个二十世纪确保了人们对国家的掌控。1930年代,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组织成立了一个剧院俱乐部、一个儿童福利委员会、一个火葬协会、一个自行车俱乐部、一个工人广播和体育俱乐部,甚至还有一个兔子饲养人协会。
在保守派一方,人们哀叹,这笔遗产是一种迈向政治化的危险驱动,而政治化将在意识形态上监督从摇篮到坟墓的个人。不过,加斯帕·米克洛斯·塔马斯(Gáspár Miklós Tamás)这样的左翼知识分子认为,那些新政党不只是社会主义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现代化本身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构成了:
……工人阶级工会和政党的抗衡力量,用它们自己的储蓄银行、医疗和养老基金、报纸、为社会人士设立的热门学院、工人俱乐部、图书馆、合唱团、铜管乐队、介入政治的知识分子、歌曲、小说、哲学论文、博学的期刊、小册子、根深蒂固的地方政府、戒酒协会:所有这些都带有它们自己的传统、礼仪和风格。(加斯帕·米克洛斯·塔马斯,生于1948 年,卒于2023年1月,罗马尼亚裔匈牙利马克思主义者。——译注)
作为“全能组织”,可以预见的是,塔马斯笔下的政党被描述为卓越的现代机构。与中世纪的行会不同,党员身份并非强制:这是一种自由的结社,党员可以加入并捍卫自己的利益。正如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所论,党因此成了深谙权谋的马基雅维利式王子的现代版,他可以用干练和洞见管理复杂的局势。在这里,党自上而下,但也自下而上地发挥作用。
过去三十年里,这些政党民主的支柱已被逐渐侵蚀和掏空。这一过程依旧体现出两大潮流。首先,各党成员人数减少,同时成员年龄中位数上升。在左翼,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员数量,1986年为100万,到2003年为66万; 荷兰社会党的党员数量从9万变为到5.7万。法国共产党1978年党员数量为63.2万,到1998年骤降为21万; 同一时期,它的意大利姐妹党的成员数量,从1753323下降到621670。英国工党在1978年有675906名党员,到2005年下降到20万名。
尽管这一趋势在传统左翼(他们总是更直接地依赖大规模动员)那里更为凸显,但在右翼那里同样引人注目。1973年至1994年间,英国的保守党失去了100万党员,法国的戴高乐主义者则从76万减少到8万。作为欧洲历史上第一个大众政党,不包括(目前已被拒绝)的俄罗斯寡头,保守党眼下从已故党员那里得到的捐款比从活着的党员那里得到的还要多。(戴高乐主义者,所属保守派政党为“保卫共和联盟”。——译注)
美国往往是这些欧洲案例的一个自然而然的例外。1896年以后,美国人从未有过任何真正的大众政党,最后一个重要例证是1850年代的反奴隶制骚乱,以及1880和1990年代的早期民粹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在南方,人民党(People’s Party)选票箱里满是选票和枪支,在北方,人民党败给了自己的选举惰性。人民党落败后,美国的两党精英构造了一个本质上令第三党挑战者丧失效能的体制。但美国的政党在社会内部有形形色色的基础和来源。例如,这些组织实际上使新政时期的民主党成了一个代理型的大众政党,维系代表大众部门的内陆劳工、工会和民间组织。左翼和右翼的工人、雇主和商铺所有者,都在地方俱乐部、委员会、行业协会和辛迪加中捍卫自身利益。
这些基础设施也是引爆1960年代民权革命的那些反叛活动的关键触动装置。1960年代初,底特律劳工领袖沃尔特·鲁瑟(Walter Reuther)与马丁·路德·金并肩游行,而1963年“进军华盛顿”活动的最重要支持者之一是工会激进分子菲利普·伦道夫(A. Philip Randolph),这人最初是依据歧视黑人的法律组织工人的。这些力量与民主党的关系一直是错综复杂、继母式的。但总的来说,它们确保了民主党依旧是一个“由工人构成的党”,而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工人的党。
自1970年代以降,这一同样的景观开始或被动或主动地失水。独自打保龄的现实取代了一代又一代前往北美的欧洲游客所描绘的托克维尔式乌托邦。在华盛顿,志愿者协会组织倡议活动时,越来越多地转向非营利模式而非群众性会员组织。
向非营利组织转向彻底改变了这些倡议团体的构成。它们没有仰赖缴纳会费的会员,而是联络富有的捐赠者,以充实它们的金库。在政府越来越多地放弃再分配角色的美国,这一举动在接受福利的新人那里造就了一批天然的选民。个中逻辑不言而喻: 那些实际像企业一样运营但不想履行对国家的纳税义务的协会,从这一非营利模式中看到了机会。美国政治学家西达·斯考切波 (Theda Skocpol)称它们是“没有成员的倡议组织”: 充当了沉默被告的律师的非营利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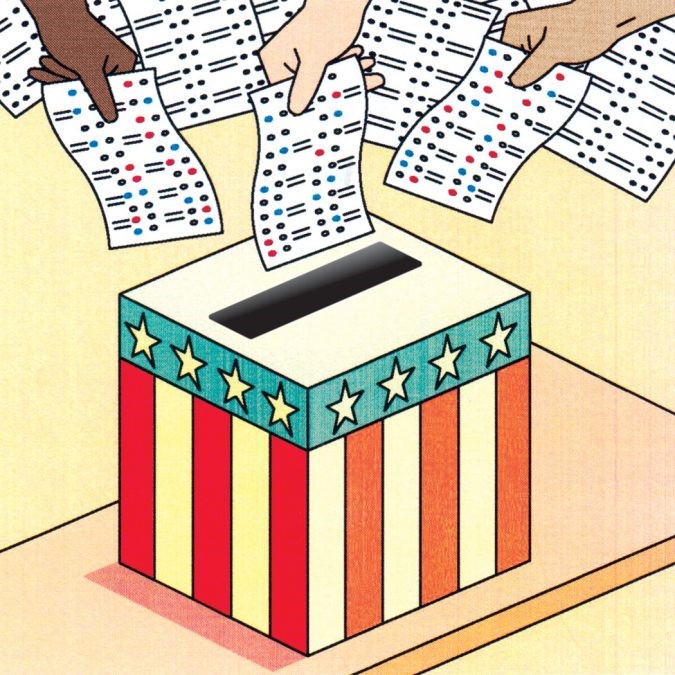
民粹主义时刻
只有电视广告和营销噱头,才能暂时防止对大众政党的放弃和政治家与公民之间的日益疏远。到2010年,显而易见的是,传统的公关和抗议政治都没有兑现承诺。紧缩政策正在全球南方大量削减养老金和破坏公共部门。由私人债务引流的公共债务正在增加。
2013年3月,一群受“愤怒者运动”(Indignados)鼓舞的左翼学者开始在马德里的康普顿斯大学(Complutense University)开会。一年后,在欧洲选举中,他们打着“我们能党”(Podemos)的旗号竞选公职,并赢得了席位。2016年晚些时候,“不屈的法兰西党”(La France Insoumise)的组织者将以西班牙为例,演出同样的剧本。
对社会主义者来说,从大众政党到卡特尔政党的转变充满了模棱两可。一方面,这一转变为激进分子创造了吸引愤愤不平的选民的真正机会,那些选民再也不能在政党内部表达不满。左翼可以政治化流行的反建制情绪,将反政治变成政治。
但这也严重限制了左翼政治自身可以运作的空间。新自由主义改革形塑的社会景观不只意味着与传统政党的疏远,还意味着从公共领域本身的撤退,只是由互联网这一新媒介提供了微弱补偿。左翼民粹主义者必须动员严重去动员的社会。
这一民粹主义转向的第一个信号,从这些力量本身的措辞中就听得见。2012年以后,“人民”这一主题成为不论新潮还是老派的左翼政党的中心参照物。采用跨阶层的语言,对左翼来说并非新鲜事。与此联系最为紧密的理论家,如阿根廷哲学家厄尼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和比利时政治理论家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这样的思想家,几十年前就起草了他们的论文。在这个独自打保龄的世界里,他们终于找到用武之地。(厄尼斯特·拉克劳,生于1935年。尚塔尔·墨菲,生于1943年。——译注)
但2010年代,拉克劳和墨菲的民粹主义在欧洲和美国都采取了一种非常独特的组织形式,包括它试图联合起来的团体联盟。左翼不得不面对一个严重缺乏组织的公民社会,而不是二十世纪的大众政党,这个社会早就将平民完全赶出了政治,并将精英和普通公民之间的关系搞得非常不稳定。因此,2010年代的危机令左翼遭遇了一对困境: 一为实质上的困境,一为形式上的困境。
第一个困境涉及的疑问是,一项左翼计划的天然基础是什么,即:它在哪里,如何组装。对二十世纪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来说,这一谜题总是呈现出一种特定的形态。正如波兰政治学家亚当·普热沃斯基(Adam Przeworski)所见,一个显而易见的门槛是存在的,一旦跨过这个门槛,左翼政党就会用工人阶级讨论交换“人民”讨论。
这一著名的困境是这样的。一方面,社会民主主义者希望产业扩张将迎来一个工人阶级的多数,这将使他们能够获得政治公职并改革他们的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那个阶级的持续停滞和最终收缩造成了一种窘境。扩大基础要求向中产阶级选民做出让步,这些选民不得不继续充当福利国家的财政提供者,并与下层阶级使用同样的公共服务。此外,在消费品方面给予中产阶级的好处越多,国内产业的喘息空间就越小,无产阶级力量和支持的物质基础也会枯萎。于是有了普热沃斯基提出的痛苦选择。
征诸社会民主的整个历史,普热沃斯基的困境收获了一系列不同的答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来说,这意味着承诺重新分配土地以安抚农民。对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这样的改革派来说,这意味着新兴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战术联盟:一座从办公室架到工厂的桥梁。对葛兰西来说,这意味着向意大利的农民伸出援手,这些农民受到法西斯国家的控制,主要生活在在意大利南部。对塞尔日·马莱(Serge Mallet)和安德烈·戈尔茨(André Gorz)等法国思想家来说,这转而意味着关注学生阶层而非昔日的产业无产阶级。所有这些选择都展示出一种民粹主义的诱惑,用工人阶级换取了人民。
2010年代,左翼政党再次不得不接合更年长的工人阶级和受到金融危机挤压的中产阶级。绝大多数左翼民粹主义者从后者那里开始,进而转向前者,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困境。然而,那些群体的构成也与社会主义者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遇到的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大不相同,他们不仅被赶出了工厂,而且被赶出了公共舞台自身。于是,这里就有了帕特南笔下独自打保龄的真正结果,对民粹主义者来讲,这是第二个、甚至更恼人的困境。自1970年代以来,左翼如何应对政治生活的世俗贫困化? 假如有的话,它可能提供什么机会?
这转而成了从一开始就困扰社会民主的谜题的乘数。虽然社会主义者传统上有产业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可以依靠,但左翼民粹主义者可以假定这两个群体都不会支持他们。相反,1980年代的去工业化和随之而来的公民社会危机,在公民和国家之间打开了一个真空,从根本上令精英阶层与他们的社会脱钩。这一真空以一种更加令人迷惑的方式打乱了左翼政治的界限:在一个政治自身处于危机中的世界,左翼的目标往好里说显得微不足道,往坏里说显得主动地不切实际。于是就有了从左翼内部向民粹主义战略的求助: 重新思考一个去动员时代的动员工作,或者如何阻止人们独自打保龄。
这不是一项轻松任务,最终,这一选择让左翼陷入了严重的双重困境。他们可以变成彻底的民粹主义者,争取到那些被社会民主逐出传统政治并变成了敌人的基础更广泛的民众。但这样做有可能掏空左翼的历史承诺,迫使人们“独自发帖”。避免这一左翼策略还意味着一种高度数字化和自上而下的联盟建设。此外,如此战略可能不会赋予左翼足够的组织分量,以在他们自己的地盘上直面资本势力。
另一方面,回归传统的左翼身份也可能吓跑那些对传统左翼的忠诚度正在衰减的选民。部分是因为后者参与了第三条道路并在2008年后要求实施紧缩计划,回归这一传统已成为一种负担。从一开始就困扰着民主社会的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权衡,如今在民粹主义方式和社会主义方式之间的妥协中找到了新的呈现。重构第一个困境的第二个困境与二十一世纪极为特有的政治参与危机密切相关。
如社会学家迪伦·约翰·莱利(Dylan John Riley)2012年指出的那样,“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当代政治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政治几乎没有相似之处”。两次世界大战之前,“在意大利、法国、德国,极度政治化的人们自发组织起来,加入左翼和右翼的大众政党”,而本世纪初是一个“政治危机作为人类活动一种形式”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伯恩斯坦或列宁都不太可能提供直接适用的教训。”(本段据作者所引,对引文和正文略有改写和补充,以便于理解。——译注)
争论法西斯主义
这样,将今天的政治视作2010年代直接产物的观点,使得从更老一辈人那里继承的一系列框架中解放出来成为必要,其中首当其冲者,是一个认为我们的时代是西斯主义复兴时代的版本。自唐纳德·特朗普当选总统以来的六年里,一场关于他是否应该被列为法西斯主义者的激烈辩论已发生在美国和欧洲学术界。事实证明,1月6日骚乱令人震惊,对这些观察人士来说也不足为奇。
帕特南早已警告说,社会资本从来不是一种无条件的好东西,后来的书写者也经常提到“为法西斯主义打保龄”,认为那是对1930年代纳粹力量的充分描述。正如帕特南自己指出的那样: “例如,正是社会资本令蒂莫西·麦克维(Timothy McVeigh)得以向俄克拉荷马城的Alfred P. Murrah联邦大厦施放炸弹。某种形式的互惠维系了麦克维的朋友网络,使他能够完成他无法独自完成的任务。”(蒂莫西·麦克维,生于1968年,美国退伍士兵。1995年4月19日,他在俄克拉荷马州首府俄克拉荷马城实施的爆炸致死168人。麦克维于2001年被执行死刑。——译注)
自这一警告发出后,认为特朗普主义预示着一个新的结社时代到来的解读成倍增加。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三名社会科学家声称,飞越州的选民已从独自打保龄变成了“与特朗普打高尔夫”,他们认为,“支持特朗普的票数增加,是社会资本强大的地区长期经济和人口下降的结果”。结论似乎不可避免: 自1930年代德国人和意大利人第一次为法西斯主义打保龄以来,特朗普眼下配得上同一术语。(飞越州,指美国中西部一些布满平原或山地,美国人在跨越东西海岸旅行时只会乘飞机飞越的州。——译注)
这种解读既有审慎的版本,也有轻率的版本。对历史学家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或哲学家杰森·斯坦利(Jason Stanley)等学者而言,特朗普和雅伊尔·博索纳罗看上去与1930年代的一些强人有完美的连续性,前总统是“美国后奴隶制时代历史的原罪,是迄今为止我们与法西斯主义最近距离的摩擦”。斯奈德认为,这仍是“前法西斯主义”,而“要想一场政变在2024年发生,破坏者手中得有一些特朗普从未悄悄有过的东西: 一个为全国范围的暴力活动组织起来的愤怒少数群体,他们准备为一场选举加上恐吓……四年来不断放大一个弥天大谎,只可能让他们得到这个”。保罗·梅森(Paul Mason)和萨拉·肯德齐尔(Sarah Kendzior)等记者起草了指引我们“如何制止法西斯主义”的文本,与此同时,首席反法西斯官员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出版了《法西斯主义: 一个警告》(Fascism: A Warning)一书。(雅伊尔·博索纳洛,生于1955年,2019年1月至2022年12月担任巴西总统。“如何制止法西斯主义”同时是一本书的书名,初版于2021年。玛德琳·奥尔布莱特,生于1937年,卒于2022年,1997年1月至2001年1月出任美国国务卿。《法西斯主义:一个警告》初版于2018年。——译注)
这一论题的更微妙的版本已经有了。例如,作家加布里埃尔·维南特(Gabriel Winant)和阿尔贝托·托斯卡诺(Alberto Toscano)提出了一个“种族法西斯主义”的框架,以在更宽泛的时间线上解读特朗普主义。在他们看来,白人身份政治和法西斯主义一直是相互纠缠的。如维南特指出的那样,“在托克维尔的美国,社会凝聚的主要因素无非是白人至上。鉴于这种结构持续存在……设想我们的社会曾经有很多结社,但现在失去了,是没有多少道理的。”尽管“在圣路易斯挥舞枪支的麦克洛斯基夫妇或许不是十九世纪流行的那种兄弟会组织的成员……但他们是房主协会的成员”,他们所仰赖的“白人特性(是)一种早期的结社性聚合力量,在特定历史关头,各种更具体的结社可能从中生长起来”。

因此,假如特朗普看起来像种族法西斯主义者,游泳时像种族法西斯主义者,说话时像种族法西斯主义者,那么他很可能就是一个种族法西斯主义者。在这一点上,一些高层人士最近也加入了维南特的行列。在2022年9月1日的一次讲话中,总统乔·拜登严厉斥责特朗普主义的共和党人是“对共和国的威胁”,并认为他们正在走向“准法西斯主义”。
这种解读眼下遭遇了批评声浪。对莱利和科里·罗宾(Corey Robin)这样的学者来说,特朗普主义更适合被理论化为一种波拿巴主义,它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超政治化”的法西斯主义几乎没有共同之处。最重要的是,任何法西斯运动的两个关键先决条件仍然缺乏: 一个处于权力边缘的革命前工人阶级,和人口共同的全面战争经历,这将形成一个体量巨大的群体(mass body)。他们声称,掌权的法西斯主义具有霸权性格,不满足于干预边缘事务。就像基督教世界中的异教徒一样,他们在新秩序中不会有多少购买力。
对这一批评的最经常回应之一,指向了左翼和右翼之间的不对称。1980和1990年代固然见证了左翼公民生活的急剧衰落,但右翼相当牢靠地经受住了帕特南时代的考验,警察工会和社区守护俱乐部挺过了新自由主义的冲击。毕竟,法西斯主义是升级到了国家政策的普通警员的心态,是一种对好斗的工人阶级的反动员。难怪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收获了法国警察一边倒的支持。(马琳·勒庞,生于1968年,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前主席。——译注)
针对英国的保守党,也有类似主张提出。据称,该党在遍布社会的私立学校、牛津和剑桥大学以及体育俱乐部中保留了强大堡垒。正如政治学家约翰逊(R. W. Johnson)2015年指出的那样,“工党选票的原子化和分散化”导致“相当多选民脱离工党,转向苏格兰民族党和英国独立党”,与此同时,“保守党的制度基础,如私立学校、圣公会教堂、富裕的住宅区、壮大了的私人部门、甚至总体上的住房所有权,仍一如既往地健康”。结果是“阶级分裂单方面减退,保守党在其老内陆地区的表现远远好于工党。”从牛津大学的布灵顿俱乐部(Bullingdon Club)到伦敦金融城的行会,保守派政党成功保护了自己的精英孵化器,并留住了更多的人才。(布灵顿俱乐部,是成立于1780年的牛津学生社团,完全由男性学生组成,数量在几十人不等。——译注)
但很难看出这些说法如何证明了帕特南最初假设的错误。例如,反帕特南人士使用的社会资本指标出奇地模糊不清。将非政府组织和房主协会归入与政党和工会一致的类别几乎无助于我们了解公民社会机构的相对实力。非政府组织是作为没有实体的领导者而非公民堡垒运转的,它们发现,吸引捐助者要比吸引成员更容易。
哪怕特朗普和其他民族主义者确实仰赖高密度的结社,这也不会减损他们在其中展开活动的那个去动员的整体背景。作为一个少数主义政治体制中的岛屿,他们只能利用美国宪法的最反多数特征,借以维持权力。这与纳粹的反宪政主义截然不同,纳粹认为魏玛共和国天生带有社会主义的胎记。法西斯主义党派很难是纸牌俱乐部,与特朗普打高尔夫球是法西斯主义新兵训练营苍白的替代品。
那么右翼的其他保留机构呢,从“白人性”到住房所有权?的确,很多右翼机构在新自由主义时代表现更好。但像维南特那样的主张令我们应该如何区分身为白人和身为三 K党成员变得不清不楚,这就好比,身为雇主和向雇主组织缴纳会费不是一回事。在一个法律上的种族隔离已经被废除的时代,种族地位并不像过去的种族隔离制度那样能确保公民的包容性。业主大会不是约翰·伯奇协会(John Birch Society)的分会,就像博索纳罗的 WhatsApp 群组不是墨索里尼的中队一样。(约翰·伯奇协会,成立于1958年,美国右翼倡议团体。——译注)
三K党和其他白人至上组织很可能被视为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西斯组织。但作为机构,它们几十年来一直在衰落,他们不像过去那样为白人的至上地位提供突击队。正如亚当·图兹(Adam Tooze)所论,像骄傲男孩(Proud Boys)和波加洛运动(Boogaloo Movement)这样的激进组织反而作为“个体化的义勇队”蓬勃发展,与1920年代初构成自由军团(Freikorps)或黑棕部队(Black and Tans)的老兵相去甚远。这些都是高度训练有素的编队,有直接战斗经验,不是开车出去保护汽车经销商的笨拙独行侠。(骄傲男孩,2016年成立,美国右翼新法西斯主义组织,成员主要是白人男性。波加洛运动,晚至2019年成型,是一只奉行极右、反政府立场,组织松散的美国极端政治力量。自由军团,是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初存在于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军事志愿者团体。黑棕部队,是1920年代初,英国为镇压爱尔兰独立运动,而为皇家爱尔兰警队招募的一只后备队伍。——译注)
欧洲的情况也是如此。过去的一年里,焦尔吉娅·梅洛尼(Giorgia Meloni)的后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兄弟党(Fratelli d’Italia)迅速壮大,目前拥有超过十万党员,并领导着一个执政联盟。尽管如此,这个党还是不能与其前身 MSI 在1960年代初拥有23万党员的局面相提并论,这形成了一种“没有队伍、没有制服、没有棍棒”的法西斯主义。从数量上和质量上讲,极端右翼仍都是从前自己的影子,中右翼也是如此。(焦尔吉娅·梅洛尼,生于1977年,是现任意大利总理。——译注)
保守党的报春花联盟(Primrose League)于2004年解散,来到不列颠群岛的游客会很快被这个国家乡村小镇上“保守党俱乐部”(Conservative Club)标牌中褪去的颜色所打动。如同旧时的工人协会(Workingmen’s Associations),这些俱乐部绝少再发挥大规模动员者的作用,往往显得更像是养老院(据估计,保守党党员的平均年龄目前为72岁)。正如《新左翼评论》(New Left Review)的塔里克·阿里(Tariq Ali)指出的那样,这种自毁本身就是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产物。撒切尔夫人的市场改革,“历经由她释出的跨大西洋两岸的并购和私有化浪潮”,造成“由地方贵族、银行经理和商人构成的保守党在伦敦以外的基础遭到严重削弱”。
当然,这条规则也有例外:反奥巴马的茶党(Tea Party)活动人士,2010年代初,他们在地下室集会;印度教青年俱乐部,由纳伦德拉·莫迪的印度人民党管理;反移民的“防御联盟”,由北欧的极右翼组织。但总的来说,这一市民化模式在右翼和左翼那里看上去是一样脱节的。

将寡头统治完美化
既然如此,那么何以在帕特南时代,右翼仍比左翼做得更好呢?原因并不令人惊讶: 右翼往往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中有机生长出来的,并仰赖资本创立的默认结社形式。正如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81年在写给英国工会成员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的那样:
资本家是一向有组织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不需要正式的公会、章程、专职人员等等。他们和工人相比人数很少,他们形成一个特殊的阶级,他们之间有经常的社交和商业往来——这就代替了一切。……相反,工人一开始就不能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这个组织有明确规定的章程,并把全权交给它的专职人员和委员会。(译文取自恩格斯《工联》一文,载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译注)
在后一种意义上,公民社会的危机对左翼比对右翼更构成问题,因为任何成功的社会主义政治的基准总是更高。对右翼来说,财产关系的稳定或保全是最充分的。惰性和顺从,而非好战,仍是他们的巨大资产。但房主协会、匿名者Q团体和高尔夫俱乐部无法持久取代这一更古老的市民基础设施。(“这一更古老的市民基础设施”,可能是指“财产关系”。——译注。)
当然,不必将当前形势与1930年代之间的明显相似性最小化。特朗普正如同阿道夫·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是一位明显懒惰的摄政王,乐于将自己的政策交给专家和高级官员;同时像是一位数字拿破仑·波拿巴,会与人群打交道。与那些领导人一样,特朗普的权力,主要源自共和党内一群顺从的保守派,他们试图利用极右翼来离间敌对的寡头。
之后,这一类比很快就弱化了。在由贝拉克·奥巴马和小布什总统松绑的行政权力基础上,特朗普更进一步。共和党人也不认为,他们的权力源自一个组织严密的政党中的群众运动。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总是抱怨该党的马乔里·泰勒·格林(Majorie Taylor Greenes)国会纪律松懈。因此,共和党人更愿意从美国的州那里已有的职位中获得权力,自18世纪以来,这些职位一直表现出咄咄逼人的精英主义特征。科里·罗宾(Corey Robin)正确地提到了“疯狂的宪政主义”(gonzo constitutionalism) ,即:无情地调用美国政治秩序中最反民主的特征。
正如罗宾所述,有关MAGA(重振美国)共和主义,最令人不安的事实是,它不仰赖“民主的这些恶魔,即不仰赖煽动手段、民粹主义或大众,而是仰赖我们在高中公民课中学到的宪法支柱”。只是在2004年,小布什以50.7%的微弱优势赢得总统选举,共和党才赢得了多数选民的支持。此外,共和党加强对国家机器的控制主要是通过少数派机制,即:任命最高法院法官、重新划分选区和冗长议事。
共和党给出的不是法西斯威胁,毋宁说是一种精简后的寡头政治:在美国的古老制度中挥舞着最后的反多数主义杠杆。麦康奈尔去年在国会表示: “将我们的选举国有化只是民主党数十年来不断寻找理由的目标。”这是在公开承认,选民投票率低对他的党来说是一件好事。对这种行为,“准法西斯主义”可能是一个修辞上的感激之语,但归根结底,不是所有的坏事都是一样的。
在线和离线
过去十年间,各政治派别的专家探究了化解帕特南危机的技术手段。毫无疑问,其中最具吸引力的是新的在线世界。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 二十年前,帕特南出版他的著作时,理论家们已经想知道,在美利坚安全国家怀抱中孕育出的互联网的新全球联通能否重塑社会。今天,互联网的孩子们对 Twitter 或 TikTok 的向善能力几乎没有信心,这像极了帕特南的怀疑,即在线参与能够取代旧的公民道德。
这一怀疑态度,被反映到了有关互联网的所谓政治潜力的困惑当中。假如说社交媒体分析的“斯库拉”(Scylla)是二十一世纪之初的天真乌托邦主义,那么它的“卡律布狄斯”(Charybdis)就是我们当前的数字悲观主义。从政治两极分化到性无能,再到识字率下降,数字悲观主义将世界上的许多问题都视为“太多人在线”的原因和后果。(斯库拉,是希腊神话中吞吃水手的女海妖。卡律布狄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大漩涡怪,斯库拉的搭档,会吞噬所有经过的东西。——译注)
显然,只有在孤独保龄球手的世界,互联网才能被理解。在线文化因原子化而蓬勃发展,而原子化是由新自由主义攻势强加于社会的:眼下有大量研究显示,公民参与减少与宽带接入之间存在正相关。与此同时,互联网加速并巩固了社会的原子化。出入这一新的、模拟公民社会的成本极低,而且离开某个Facebook群或某种Twitter亚文化的耻辱感,与工人因在罢工期间拒绝参加罢工而被迫搬出社区无法相提并论。
帕特南笔下1980和1990年代的极端市场化,也令社交媒体的危害容易影响到世界。志愿组织解散,福特主义者工作机会稳定性下降,宗教生活消亡,业余体育协会人间蒸发,“大众崩溃”,由个人构成的各色群体崛起,都是Facebook 或 Instagram这样的产品出现前很久就制造出了社交媒体需求的力量。社交媒体只能在不是它自己造成的空间中成长。

解纽性的资本
于是,解读互联网,最好将其理解为Pharmakon,这是一个希腊名词,既表示一种治疗手段,又表示一种毒药:这种所谓的解药只会加剧疾病。这对右翼也构成敏感议题,尤其是在资本本身在过去几十年间早已日益分裂的情况下。正如保罗·海德曼(Paul Heideman)在《催化剂》杂志(Catalyst)中提到共和党时所论,1980年代对工人阶级组织的攻击,清除了曾将资本家聚集在一起并强加共同政策议程的外部纪律来源。(保罗·海德曼,任教于纽约私立教育机构Ethical Culture Fieldston School。《催化剂》,全名为Catalyst: A Journal of Theory and Strategy,是由美国非营利机构雅各宾基金会出版的一份同行评议季刊。——译注)
没有了这个对手,内部断裂可能加剧。随着“1970年代以来政党力量弱化,以及1980年代以来企业化美国政治动荡”的加剧,如学者凯茜·乔·马丁(Cathie Jo Martin)所论,“美国雇主更加难以考虑他们的集体长期利益”。而且,驱动我们的政治动荡时代的,不是共和党人攫取了工人阶级选票的重组过程,而是“选民抛弃了与先前政党联络的解组过程”(dealignment)的无情推进。(本段第二句中,前半句引文出自上一段所引保罗·海德曼文章,后半句引文出自凯茜文章。凯茜·乔·马丁,任教于波士顿大学。——译注)
相较于非历史地提及1930年代的威权主义,资本的解体为“民粹主义爆炸”提供了一个有益得多的框架。德国作家海因里希·盖瑟尔伯格(Heinrich Geiselberger)提到,没有“社会主义的敌人”,右翼如何“只能召唤幽灵”。盖瑟尔伯格和塔马斯更喜欢谈论后法西斯主义: 那是一种使公民身份不那么普遍,并将其限制在国界之内,但缺乏法西斯主义者在二十世纪展示的组织力量的一种尝试。因此,新的右翼是“原子化、不稳定、群体式的,在严肃和认真、真诚和讽刺之间有着漏洞百出的边界。”
最重要的是,新政治始终是非正式的。在2021年1月6日表示无条件支持特朗普的那些暴徒甚至没有名单。匿名者Q和反封控运动是一种亚文化,主要在博客、Instagram和Facebook 群上兴盛起来。当然,著名的匿名者Q人士,也可以说是网红,多少是有的。但他们的领导地位不是正式的,也不是由选票授权。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受过军事训练的群体,而是一个由自我选择的激进分子小集团鼓动起来的流动群体。
这种非正式性也表现在经济方面。过去一年里,特朗普从他的追随者那里勒索了数千美元,并继续大肆敛财,却从未建立一个明确的政党架构。早在1920年,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就指出,魅力型领导者不会向他们的追随者和支持者支付固定的薪水,而是通过“捐赠、战利品或遗赠”展开工作。毫不奇怪,魅力型领导也是一种完全不稳定的统治模式:王位无法确保留给暴民继承,他们现在必须寻找下一个救世主。
取代这一法西斯主义框架的可行方案会是什么?正如莱利明示的那样,我们在卡尔·马克思对1848年革命的描述中,可以找到一个说服力强得多的先例。那场革命结束之际,拿破仑三世没有屈服于动荡,而是召集了一批冷漠的农民,命令他们平息革命。马克思把这些法国农民描述为“一袋马铃薯”,对他们来说,“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因为农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就是由国王来代表。(本段引文取自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载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译注)
波拿巴的政治不是某种由资本-劳工反对派精心安排,策动工人对抗老板的政治,而是债务人和债权人的政治,这是2010年代的另一个共同特征,当时,转移到公共账户上的私人债务助长了美国和欧洲的债务危机。波拿巴的农民专注于流通和税收,而非生产。我们不能漫无目的地盯着1930年代,而是必须审视古老得多的原始的民主时代,找到与我们的民粹主义时代适当的相近之处。
但法西斯主义框架也带来了更严重的风险: 高估了社会主义的力量。法西斯主义意味着一个大众阵线和与自由主义的战略联盟,包括不罢工承诺。法西斯主义框架不仅不会强行集中精力,反而会扰乱我们对二十一世纪典型政治参与危机的关注,并使我们困惑。
帕特南的正确是因为错误的原因: 社团主义(associationalism)对民主而言至关重要,但对资本而言很难讲重要,甚至可能威胁到资本。对那些考虑2024年伯纳德·桑德斯(Bernie Sanders)竞选总统的人来说,这场竞选留下的遗产似乎比它取得的成就更重要,更不用说它是否会让伯纳德登上总统宝座了。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见证对资本宪法忠诚度的真正考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评估金钱与自由民主的结盟。
在没有社团主义威胁的情形下,在左翼和右翼,我们都将继续独自打保龄。
Like my work? Don't forget to support and clap, let me know that you are with me on the road of creation. Keep this enthusiasm togeth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