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此生而為人:讀Aparecida Vilaça《祈禱與掠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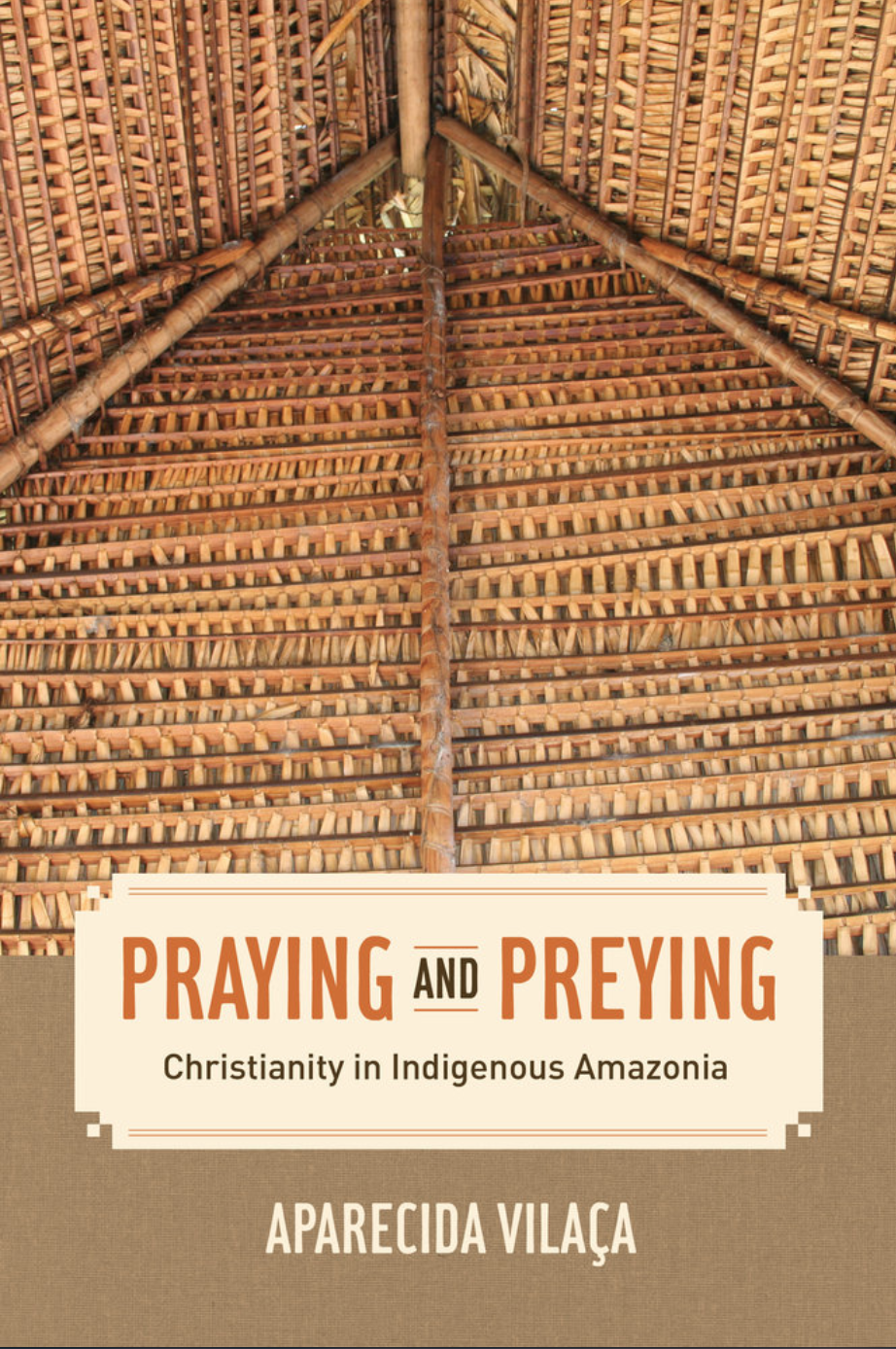
Aparecida Vilaça, 2016, Praying and Preying: Christianity in Indigenous Amazo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年,來自里約的Aparecida Vilaça來到馬莫雷河(Río Mamoré)流域進行田野工作。她和養父Paletó一家人住在一起,研究Wari’人的神話、巫術與傳統信仰。2002年,Vilaça回到村子裡,發現她的Wari’家人變得像是尋常的巴西基督徒。他們上教堂做禮拜、吃米飯、麵食,薩滿也不再與動物溝通。
因為知道養女對傳統文化更感興趣,Paletó甚至瞞著她偷偷上教堂。Vilaça很震驚,但她沒有輕易地把眼前的景象化約為「文化的喪失」,而是更深入地思考「轉宗」對當地人的意義。就像Wari’把自己打造為基督徒,Vilaça也把自己重新發明為研究基督教的人類學家。她下苦功鑽研這個陌生的領域,寫出了第三本書《祈禱與掠食》。
Vilaça進入田野的1980年代末到整個1990年代,其實是兩波轉宗浪潮之間的間歇。新部落福音會(New Tribes Mission)的傳教士在1960年左右來到這個流域。1969年,Wari’大規模轉宗,第一次成為了基督徒。1980年左右,他們集體「放棄了上帝」,薩滿回頭去尋找他們的動物眷族。2001年,所有人在電視上看到九一一事件,Wari’擔心末日要來了,如果沒有信主,恐怕很快就會在地獄中受無盡的折磨。他們決定再度投入教會的懷抱。

重返田野的Vilaça要面對的是一個很棘手的理論難題。一方面,她仍然在意Wari’的傳統、相信她的報導人們並沒有因為基督教而徹底「失根」;另一方面,人類學家也必須放棄長期以來對基督宗教的偏見,抗拒把轉宗簡化為壓迫的傾向。Vilaça認為,人類學家的文化觀念擅長處理延續性,卻很少指引我們該如何分析一場劇烈的轉變。
她決定從基督教怎麼創造新的「關係」出發,觀察神學概念如何轉換人與人、以及人與動物之間的連帶,同時指出轉譯過程中無可避免的模稜兩可,正好讓傳教士與當地人各取所需。 Vilaça對南美洲低地文獻的深厚掌握,為她的分析提供堅實的民族誌基礎。她說,在亞馬遜,傳統與創新往往難以區分,延續和變異其實是一體兩面。因為結構主義而聞名的二元論不只是靜態的觀念,許多亞馬遜人群展現出可以逆轉的兩極擺盪模式。
一切還是必須先回到Wari’的人觀。人(wari’)的對立面是敵人(wijam),這個詞涵蓋其他的亞馬遜人群、白人、 美洲豹、西貒、南美貘、捲尾猴、刺豚鼠、犰狳、魚、鳥與爬蟲類 。在過去,人類與動物之間只有「身體」上的不同,他們共享一樣的「觀點」。換句話說,人類眼中的動物也把自己視為人(wari),而把人類視為敵人(wijam)或獵物(karawa)。
A’ain Tot是一位六十多歲的女性,她向Vilaça說起五十年前的往事。有天,她被大人派到河邊取水,她的「母親」在不遠處叫喚她,她就跟著走了。兩人在路上遇到棕櫚果樹,「母親」從籃子裡拿出玉米,一起配著果實吃。夜裡沒有營火,她在「母親」的懷裡入睡,看到一位「男人」溜進來與「母親」性交。第二天,母女繼續上路,她突然聽到哥哥的聲音朝她大喊。「母親」說自己要去如廁,一溜煙消失在樹林裡。A’ain Tot被家人發現的時候,身上覆滿了豹毛。
人們說,她吃下的「棕櫚果」其實是犰狳的尾巴。對作為人(wari’)的美洲豹來說,犰狳的尾巴是棕櫚果、駝鼠是木瓜、奇洽酒(chicha)則是動物的鮮血。Wari’認為豹有同情心,但美洲貘沒有,他們不會釋放被拐走的人。人獵殺動物為食,動物也「掠食」人類。牠們試圖把人變成自己的眷族,這對人類來說等於死亡,靈魂將永遠跟動物群體住在一起。 對Wari’而言,處於掠食者位置的就是人(wari’),處於獵物位置的就是非人( karawa) 。所有「人」都具有變形的潛力,被捕獲的一方會被轉化成另外一方。只要稍不注意,人類隨時可能把其他動物錯認為人類。

被動物誘拐的故事在Wari’地區非常普遍,Vilaça養母的母親也有類似的遭遇。在被美洲豹誘拐、與動物親密地相處後,她回到村落,成了有「兩種身體」的人。她生吃捲尾猴,喝牠們的血,但在場的人都見證到她吐出來的不是血,而是奇洽酒;她吃下鯰魚,但吐出來的時候卻變成桃椰子酒渣;她在河裡抓到小魚,掌心攤開卻變成幼蟲。她的身體像一本雙語字典。大概從這個時候,她開始為村民治病。薩滿擁有雙重的身體,所以也具備兩種觀點 。他們成為了動物的眷族,卻沒有徹底失去人的身分 。有時候,薩滿們會抱怨自己跟著動物在森林裡鎮日奔走而疲憊不堪。
換句話說,人類的身體並不是與生俱來的 。初生嬰孩要被仔細檢查後才能被確認是「人類」。在亞馬遜的許多地區,嬰孩甚至需要被用手「揉捏」出人形後,才真正被視為一個人。 Wari’必須時時刻刻把自己置身在有親屬關係的人群之中,透過各種身體物質(kwerexi’),包括體液、言語、照護、情感、以及共享的食物,來避免變形成動物。如果「人性」真有所謂的本質,那就是一再嘗試與動物作出區隔的意圖。
Vilaça從傳統人觀切入,不是為了走回封閉的世界。事實上,正是「人」的不穩定解釋了Wari’對基督教的興趣。她注意到村民們特別喜愛《創世紀》。傳教開始的五十年之後,《創世紀》仍然一再被引述。神創論清楚地分離了人與動物、把動物「去人性化」,鞏固了人類的位置 。上帝是萬物之軸、一個最穩固的觀點,祂讓人類當主人、動物則永遠是獵物。成為基督徒之後,Paletó高興地對Vilaça說:「我們之前有時不吃犰狳,遇到白人之後,基督徒說什麼可以吃,因為這些食物是神賜予人的。牠們也不會讓人生病。」村民不再害怕動物的靈,夜晚可以到處遊走、什麼都敢吃下肚。
Wari’版本的聖詩是這樣唱的:「我們天上的父是好的,我們天上的父是好的,他賜予我們很多能吃的獵物(karawa)。我們天上的父是好的。」
同一篇章,葡萄牙語版本卻是:「神是好的,神是我們的父,神是愛。雨落下、落下、落下。陽光燦爛。神是好的,神是我們的父,神是愛。」
Vilaça說,與其說轉宗是靈魂的解放,不如說是腸胃的解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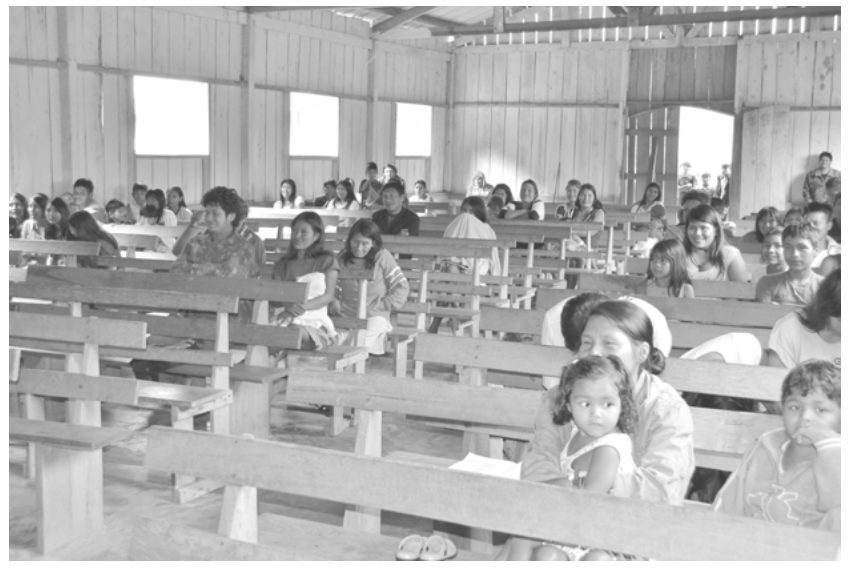
基督教還提供了Wari’解決親屬衝突的途徑。 姻親關係隱含著危險,常常包括了憤怒、爭端、甚至巫術。傳教士說「神愛世人」,但Wari’的語言中沒有「愛」,只有「沒有不喜歡」(om ka nok wa)。愛一個人,意思是控制並且壓抑自己的冷漠與憤怒。看到Wari’對於控制憤怒的興趣,傳教士以為他們意識到了自己的原罪,想要洗心革面。但對Wari’而言,基督教強調的「弟兄姊妹」情懷可以掩蓋姻親關係、讓他們可以極大化親屬網絡──包括成為神的子民,站在祂的觀點──並以此和動物做出區隔。
另外一個Wari’特別感興趣的面向,是《聖經》上對地獄的描述。村民一再對Vilaça強調,在地獄裡,人將會被業火焚燒,像是獵物在烤爐上,而且永遠與親人分離。對親屬的重視解釋了為何幾次轉宗都是以集體的形式發生。 Paletó一再希望Vilaça能信主,Vilaça反問他為何要受洗,她的養父回答:「為了在天堂裡可以喝水 。」Paletó請Vilaça站在他的立場想想,看到女兒在地獄裡受苦卻不能給她水,那該有多心痛?
這幾個例子都指向了內生於Wari’傳統中的不穩定性:隨時可能變形的危機、打造親屬關係避免淪為獵物、親屬關係中卻又隱含著難以調節的衝突。Vilaça認為,新部落福音會版本的基督教義正好提供了一整套新的概念,解決這一系列的矛盾。它讓無止盡的變形告終,也讓人類從此生而為人。同時,這也意味著「人」的定義縮小了。村民對Vilaça說,在天堂裡,每個人都長得一樣、穿一樣的衣服、住在自己的房子裡,沒有血親也沒有姻親。天堂是Wari’對基督教個人主義的終極詮釋,一個不再變換的理想世界。

《祈禱與掠食》有很大的企圖心,它充滿各種令人玩味再三的民族誌細節,卻不是一本很好親近的書。Vilaça對區域民族誌的討論既深且細 、從傳教士的民族學檔案、李維史陀、到本體論轉向的幾位代表性學者,倘若對南美低地的文獻沒有一定理解,有時難免霧裡看花; 在文化理論上,她援引經典的美拉尼西亞民族誌,勾勒出比較的框架,卻也設下了很高的閱讀門檻。
三十多年來,人類學者驚嘆於Wari’面對變化的能力。他們彷彿可以隨時切換頻道,像是過去好幾次的轉宗與反轉。Paletó曾說:「動物的靈已經消失了。我們現在是完全的白人了(wijam)」然而,同一位Paletó,在養女Vilaça提到Wari’正在被同化的時候,卻又出聲反駁:「你一直說我們變白人了。我們仍然是wari’、徹徹底底的wari’。」
──擺盪在非此即彼之間、恆常不穩定的二元論。或許這就是 Wari’。
Aparecida Vilaça是巴西人類學家。她在里約熱內盧聯邦大學( Universidade Federal do Rio de Janeiro)取得人類學博士,目前也在同一所大學擔任人類學教授。Vilaça長期關注西南亞馬遜的Wari’人群,除了《祈禱與掠食》,她的英語專書包括Strange Enemies: Indigenous Agency and Scenes of Encounters in Amazonia (2010)以及剛出版的Paletó and Me: Memories of My Indigenous Father (2021)。
關鍵字:基督教、轉宗、人觀、觀點主義、亞馬遜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