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憐的東西》:男人幻想的女性 / 電影

文|朽木
今屆奧斯卡罕見有兩部以女性成長(coming-of-age)為主軸的電影為大熱,一部是我由《凡事哈》(Frances Ha)已放在心頭的才女導演 Greta Gerwig 破紀錄之作《Barbie 芭比》,另一部是《單身動物園》(The Lobster)導演尤格藍西莫(Yorgos Lanthimos)新作《可憐的東西》(Poor Things)。兩部電影均有提及父權社會如何壓抑女性 ,《可憐的東西》女科學怪人貝拉的成長源自情慾覺醒,芭比卻連性器官都未有。由是,同樣說女性成長,不少人將兩部電影相提並論,甚至有人說《可憐的東西》比《Barbie 芭比》更加「女權」,畢竟前者涵蓋了身體與思想上的自主,更有外國網民笑說《可憐的東西》大概就是芭比去看婦科醫生的後續。
在我看來,《可憐的東西》其實志不在此,不過就是經歷了《Barbie 芭比》一整個夏天的粉紅風暴後,被煞有介事的扣上「女權」帽子。導演的動機其實更加開放,更加純粹——摒棄所有記憶,重新想像一個最古老的故事:拋開道德枷鎖、社會規範,我們會如禽獸一樣活著,還是可以毫無束縛地建構一個更合時宜的伊甸園?

無性別的腦袋
當科學怪人成了「上帝」,這次他不造亞當,轉為女屍植入腹中嬰兒腦袋,先創造「夏娃」,她有一個代表美麗的名字——貝拉。電影從來沒有道破嬰兒的性別,貝拉究竟是男是女?我們無從得知,答案或許都不重要。我們與生俱來的身體,將我們置入性別角色的無形框架之中,其實腦袋又有否性別之分?

從伊甸園走到失落園
貝拉是一個自由的靈魂,「它」藉由一個女性的身體去接觸世界。然而,她的世界僅限於上帝為她建構的伊甸園,這時候的「她」還未完全感受到自己身為女性的角色,直至上帝帶來「亞當」要跟她成婚,引來了滿身誘惑的「蛇」——額頭寫着渣男二字的律師鄧肯。
初嘗禁果(蘋果?)以後,她突然意識到自己與身體的關係,提出要跟鄧肯出走,開首固然是縱慾橫流,世界由黑白變成彩色。其後因為鄧肯的佔有慾被綁上賊船(有趣的是貝拉與芭比同樣被電影中的男人嘗試去 put in a box),巧遇上古靈精怪的老奶奶與年輕人哈利,一起看書、思辨,我思故我在。明明是被困在船上,貝拉卻覺得思想如大海一樣,無邊無垠。此時,貝拉已走出雙腿之間(between the legs)原始的歡愉,轉而追求雙耳之間(between the ears)知識與精神上的滿足。這段旅程也讓貝拉首次目睹人世間的千瘡百孔,千金散盡,墮落凡間。流落煙花之地,在形形色色岩岩巉巉的逢場作戲之中,見盡花都蒼穹下,原來眾生皆可憐。

God is a Woman?
繞了一圈,風塵僕僕,恍如隔世。貝拉由失樂園走回伊甸園,上帝早已奄奄一息。上帝離開之前,向貝拉告解了她的身世。為何母親要選擇了結自己(和自己)的生命?要得到答案,她決定正面面對上輩子的情人——父親。這位父親一言不合就開槍的性格,是父權 / 極權的代表。為了讓失而復得的維多莉亞能安份守己的留在身邊,他悄悄地安排了一場去勢手術。只是,他不知道,眼前的維多莉亞,已經重生成為貝拉。蛻變成新時代獨立女性的她直搗問題癥結所在,有樣學樣的為這個十惡不赦的父親換上一顆羊腦,從此,陽具變成羊懼(笑死)。
上帝給予「夏娃」孕育生命的能力,她卻選擇成為「上帝」,投身醫學,親手創造新生命⋯⋯這是否又稍稍呼應了「God is a woman」的想像?
後記:男人的終極幻想
在我看來,貝拉代表了男人的終極幻想——有著性感美麗標緻的胴體,卻又有著孩童的天真可愛(其實是腦囟未生埋),身邊所有男人趨之若鶩(除了象徵「上帝」的性無能父親),全都想把她佔有,與原作《科學怪人》的男性「怪物」被世人唾棄的待遇有天淵之別。這個設定,少不免帶一點男性凝視,幾乎讓我想起幾年前我看得咬牙切齒的《三夫》,不過貝拉有思想、有腦袋、有自己的聲音,她對肉體歡愉的追求是自發性而非被迫的,倒不如《三夫》的小妹一樣「肉隨砧板上」。單看貝拉這個角色,的確不難聯想到《可憐的東西》導演、編劇,甚至是故事的原作者也是男性。例如,為何貝拉可以一點懷孕和生產的痕跡都沒有?沒有一絲贅肉、沒有妊娠紋橙皮紋、沒有鬆弛的肚子⋯⋯只有「上帝」給她一條完美的疤痕,這應該也算是一個頗為「直男」的設定吧(笑)。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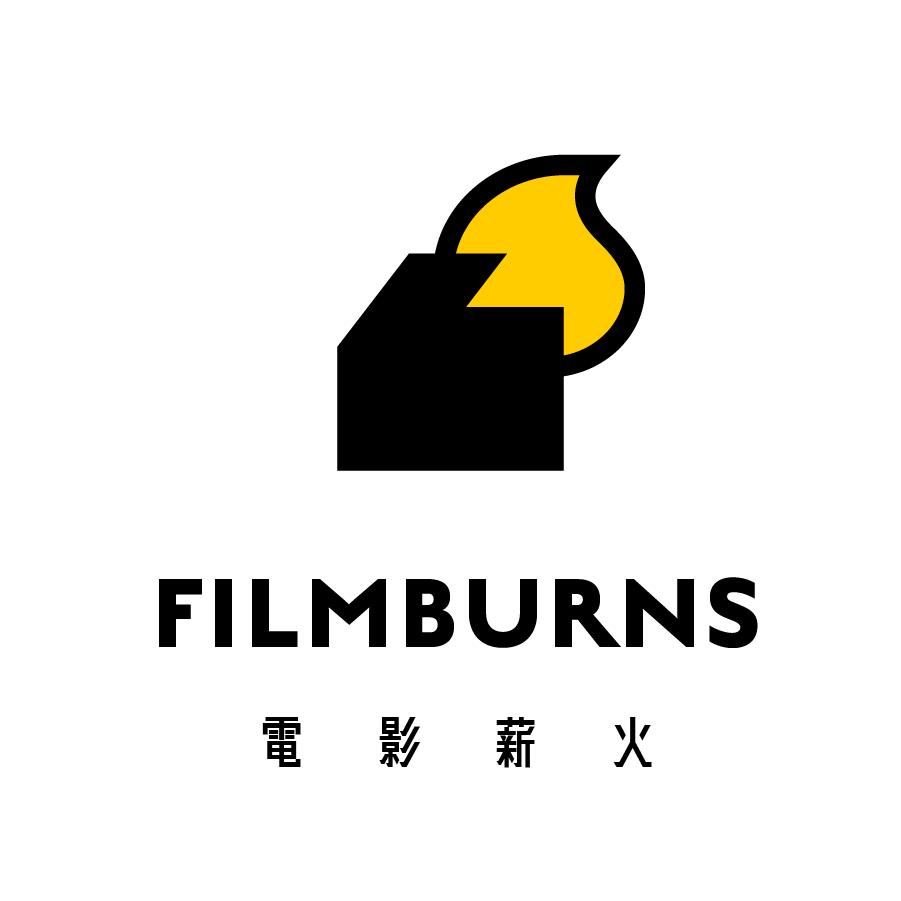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