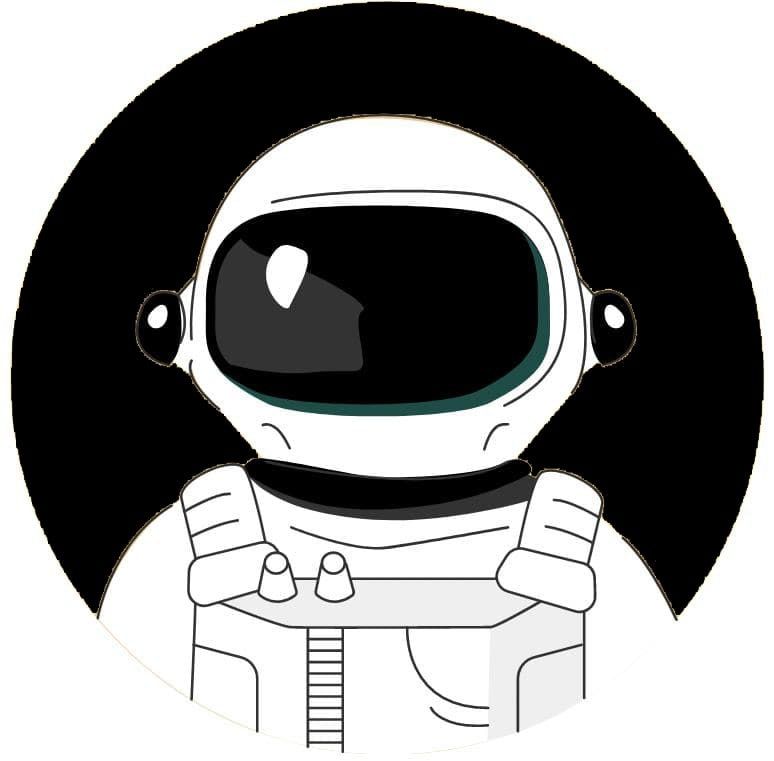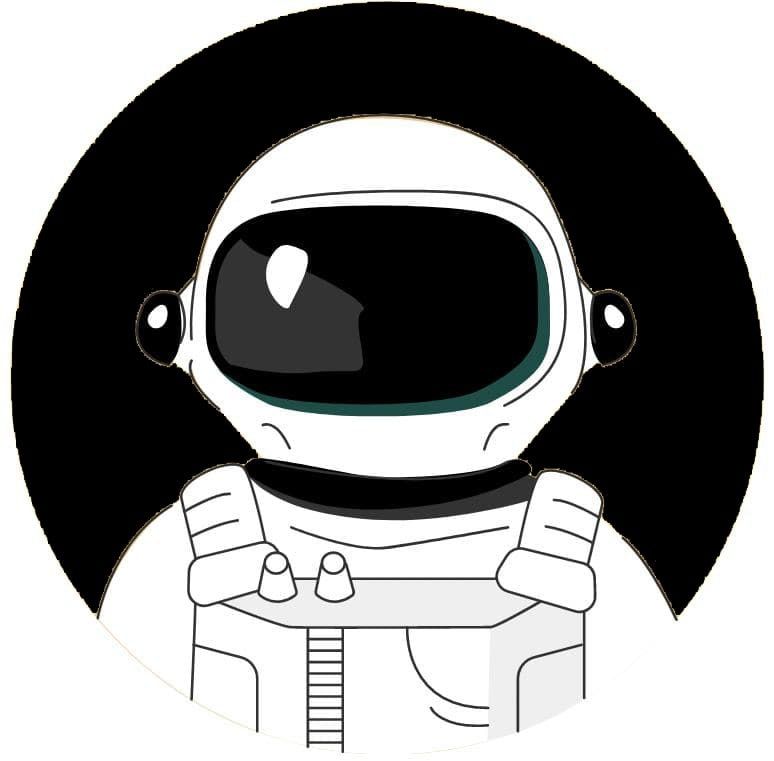我們並不在同一個泉州
當我還是初中生時,一次翻開歷史教科書,看著泉州的地圖發呆。書上說,元代時期有「刺桐港」:江面遍地商船,很多外國人在此居住。這個畫面充滿著想象力,就想起當時常玩的《大航海時代》單機遊戲。
但難免不去想,這種世界主義的泉州是過去的,只存在一段歷史中。當我到訪泉州後,這種印象多少被證明了。這是一個本土的古城,豐富、活躍的閩南文化,城內的小巷、寺廟、植物也讓人感到親切。在一部蔡國強的紀錄片中,他就站在樓房的陽臺上,不遠處的泉州古城一覽無余。西街與東街,串起了整個鯉城區,古候被城墻環繞。海在不遠處。
對於阿燦來說,泉州又是另一個樣子。在他看來,泉州非常本土,但同時又很異域。阿燦從福州來的泉州,從高鐵下車後,他就走進巷弄,拿起照相機拍了起來。面對鏡頭,當地人並不警惕,反而成了一塊聊天的由頭。
「在廣州,你走上街、或進入某個地方拍照,會有種對抗的感覺。這邊的話,卻很放松。」阿燦又講到了「異域風情」,這種感覺沒有在泉州城發現,而是在靠海的小鎮上。第二天,他搭車去了永寧鎮,離古城三十多公裏。小鎮更有一種鄉野的感覺,阿燦發現村子裏有些人,面貌接近東南亞、印度人。
永寧是僑鄉,住戶多有海外的關系。在街上,阿燦看到一個模樣像意大利的人,直接把他攔下。「我們不需要交流,他知道我只是要拍個照。在別的地方,人們會問你是不是要放網上,你有什麽目的?」
在鎮上、村子裏,多是當地風格多元的自建房,有傳統的福建民居、現代農村式別墅、仿日式、歐式洋房.......混雜,但街道卻看起來和諧、整潔。一棟來自菲律賓的建築,引入註目,它修於1930年,所有的建材都從菲律賓運來。這樣的樓叫做「迎薰樓」,也叫「番仔樓」,建築風格是一種拼貼:門洞是巴洛克的,構造是歐式的,外立面和雕飾物則有著泉州本土元素。
空間總有一種鮮活感。在海邊,雕飾過的樹幹、呈放著釋迦摩尼像,構成了微型的廟宇。你常能見到一堵墻,由不規則的磚塊和石頭砌成,傳說來自當地人在廢墟中的就地取材。鎮上戲臺邊緣的中段,蓋起了籃球框,看臺也可以做球場.......當你步入其中,會看到更多。
第二天,阿燦在蟳埔村遇到了一場婚禮。女人們戴著花環,四處派發著新婚禮物,敲門、說道恭喜,無人應時,就把禮物留在門上。她們見到阿燦,不覺得好奇,追來遞了包糖和餅。原來,村子人不是有喜事才戴花,只是日常所戴頭飾。
阿燦覺得,泉州充滿著反差感,新城區隨處可見高樓,有著廣州類似的現代化生活,也能找到10元一條褲子的批發街。蟳埔村就離新區很近,但還是一副漁村的景象,女人們戴著傳統的頭飾,附近有著古樸的農貿市場。盡管生活在小地方,人們卻沒有「閉塞感」,反而快樂和自信。
泉州城是另一派景觀。古城的格局,在元代時基本確立,從開元寺、承天寺、天後宮等大型寺廟,到巷弄中供奉不同地方神的小廟。從府邸舊址、文廟,到鄭成功、李贄等名人故事,儼然一副舊日府城景象。人類學者王銘銘告訴我,明朝以後,海洋貿易在泉州城外還在進行,而城內進一步「文明教化」。
如果說靠海的小鎮有一種異域感,泉州城更接近一種本土,居民像是世世代代生活在城內的感覺,過著一種「住了舊厝起新厝」的生活。在通政巷24號,每周六會有提現木偶戲的表演。木偶藝術歷史悠久,產生時間能追溯到春秋時代,至今在廣東、福建、山東、四川等地活躍。我看的那場表演結束後,工作人員前來講解,他提到了人物造型。「你們有註意到一個木偶的膚色差別嗎?原型是波斯人。這也說明了,古代泉州住過很多外國人」。
泉州的世界主義,在歷史中,也可能融入到了日常生活。當你走進泉州,會發現當地人性格溫潤,又對陌生人好奇、友好。這是一個容易偶遇的城市。在泉州的最後一天,阿燦看到酒店外停了輛「摩的,想著去天後宮。他就這樣認識了阿英。
阿英大概四十多歲,是家中的老五,有四個哥哥,父母幹脆給阿英起了女孩名。一路上,阿英熱情介紹泉州歷史,關鍵地方停下車來,又執意帶阿燦去趟聚寶街 、港仔乾等老街。原本五分鐘的路程,兩個中年男人在老城區,兜兜轉轉了兩個多小時。
結束後,阿燦料想要付阿英一個「天文數字」。兩人加了微信,阿英說道:「你隨便給就行,那就二十吧。」 沒等到轉賬,阿英就騎著摩托車一溜煙走了。回廣州的路上,阿燦收到了阿英的微信,「你給我那麽多錢?我微信退三十給你,你要收下,謝謝。」
這是阿燦第一次來泉州,他覺得這裏值得來玩很多次。於是,阿燦收下了紅包,回復道,「阿英,我還會回來的。」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