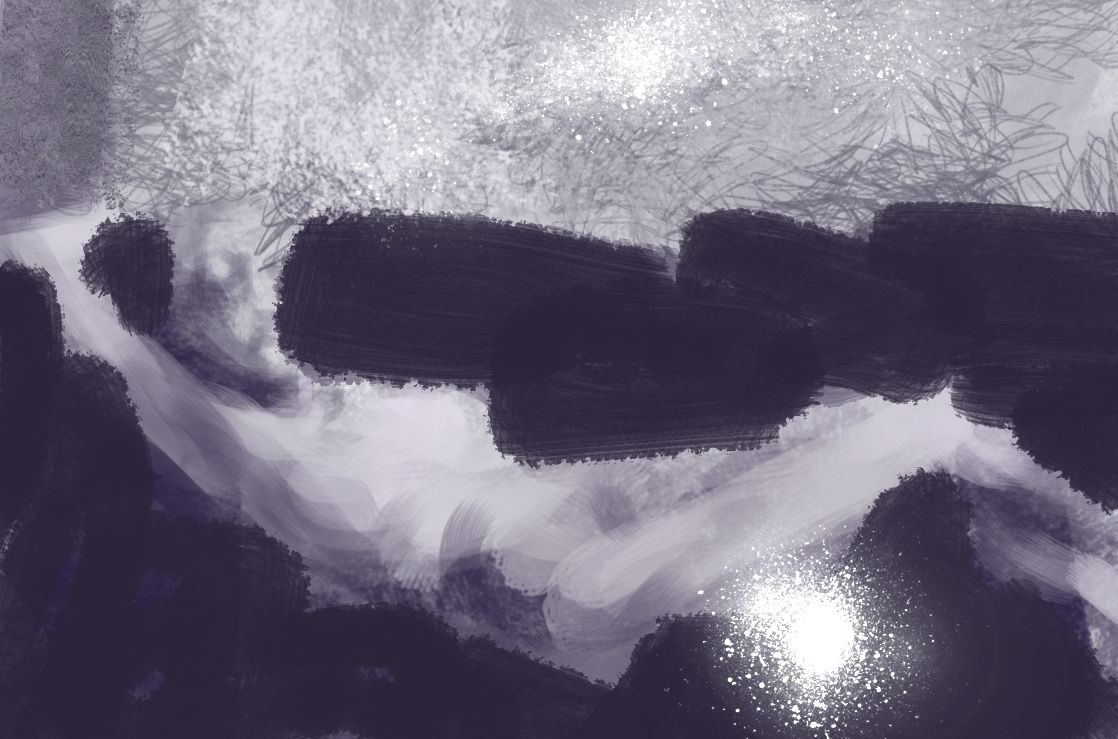
女性,藝術,精神病……觸摸命運。
记录|♥伤心女人心♥?
*人的思绪竟然可以如此复杂,记录了在这数个小时里,脑锅里发生的事情。
文/圖:iago
我压不过我心里的迷茫感了,新的一年,这和那的选择横在我面前,我感到彷徨。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连续很多天很多天没日没夜地通过看网络小说进入别的世界,以至于我产生了一种空茫感:我真的属于这个世界吗?我是不是剥离了这个世界的?我无法做任何事情,无论朝向哪个方向,凡是往前走的都叫我抵触。
这样的感受已经很久没有了。
我决定去找我好久不见的一个朋友,她性格内向,并不是我们常见的那种“学富五车”的人,却非常知道现实在何方。
我晃荡着坐着地铁,甚至看着旁边的男孩子想象他是偷偷摸摸的色情狂,然后我如何打倒他,压制他,在众人面前羞辱他,在羞辱之下,最后放过他,直接改变了他性享乐的方式,让他从摸摸索索去蹭别人裤脚的卑微痴汉,变成只求暴露在大众之下,被仁义礼智信按在地上摩擦的暴露男M。
这样的想象让我热血,我低着头继续看手机上的小说。自回了一趟家,我就开始看小说,无言的窒息下我选择躲避。直到回了大城市,才开始重新呼吸。
我已经几近两三年没有看过任何网络小说了,这回常看的是修真耽美小说。后来我才知道,也许是巧合,在老师讲了科塔尔综合症,俗称活死人症,僵尸症,也就是当事者相信自己身体已死的一种精神病之后,老师在课后总结的那句,恐怕将我钉在了某处。他说:在象征界被否定的死亡,最后在实在(real)中返回。
这病里的实在,就是身体。在上完那个课后的两个月,或者一个月吧,也是最近几天,我回想起了,我回想起了我17岁时候对我初恋说“我闻到了我嘴里发出腐烂的味道,是从我身体里传出来的。”
这句话,我说到二十岁出头。
我不知道何时开始,我就活在巨大的否定中了,或者,我是在巨大的否定中,被生出了肉身?
我看的那些修仙的东西,基于道家保身那套创造的东西,不过是另一种生死翻转的科塔尔综合症。

在晃晃的地铁尽头,我终于见到了我朋友,她还一如7年前那样的神态,只是头发短了点。在上一段关系中,我的状态非常糟糕,被雪藏的暧昧,扼紧了我的喉咙,把我压得变形。那时候我与她也有一年两年未见,她一见我就识破了所有人都看不穿的伪装出来的笑容,告诉我我状态很糟糕。我们讲了很多话,她说了一句话令我记忆犹新,她说:我们是一样的人。
我与她认识以来,一直以为我与她是十分不同的人。我性格外向活泼善于交际神经大条,她内向害羞社恐细腻敏锐;我擅长阅读,难以看视频,听音频,她不擅阅读,但对影像过目不忘,常听播客。
她当时接着说:只是你屏蔽了自己的敏感,所以常常不知道自己在难受。我们其实都很敏感,甚至你的处境比我更糟。
我甚至不知道我的处境是什么。
这也是我今天会去找她的原因吧,我想知道,我究竟在何方?
我们好多年没见了呀,我给她看我自己给自己剃的头发,有个地方剃凹了一块,告诉她我或左或右的茫然选择。她问的问题总是那么直达要点,跟7年前一起玩乐时一样,善于分析。这些困扰的问题不过是表象,真正飘摇的是我的心志,我说,我还没有真正完全准备好做一个分析家。
她说,你转行的能力是比我强很多的,因为这里要投入的成本太高了吧,不然你早就把路并着走下去了。
我细细一想,确实是,这里面的成本令我惶恐。而我已经过了忍耐自己去画画赚钱的阶段。我曾经可以这样做,客户要什么样的画,我都可以画,但现在已经非常困难了。我笑着跟她说,我和三和大神一样,只要口袋里还有一块钱就坚决不赚钱。
画商业的插图,以及背后赚钱的意义,在我这儿,完全就是一个空。
这样的空,让我提不起半点儿劲儿去敷衍它,实在是无趣得紧。这无趣简直光是想一下就掏空了心窝窝。
我更愿意与朋友们胡侃瞎侃,笑骂讽刺,把自以为是的家伙们阉割了鞭尸,或者在一个人的现场中,在女人的现场中,在精神病的暴风中,在重重业障烈火中。
满宇说,最后还是要靠慈悲,神经症穿越幻想后只是成为“正常人”,但只有慈悲,才能在理解自己之后理解他人,不执著于观点立场。满宇在兜兜转转好几圈之后,终于在精神分析中明白了佛要说什么。还叫我别走太快。
回到我的姐妹这里来,她说:我的忍耐力比你强,所以画这些模式化的东西,没有你那么痛苦。
她还说,太阳终其一生都要和它内在的引力对抗,我也是这样,我想“共情”这比我庞大的它,像古代人信仰比自己强大许多的神那样,去应对现实……

我到今天才明白,为什么我和她是一样的人。我们都是赤裸生命,在我们这里,这个世界失去了包裹,像剑气一样直逼我们。因为与她的谈话,我从我躲避的小说世界里重新掉落回来,我想起了有一年,可能是春夏之交,我发现我要坐一个小时的地铁却没有耳机让我听歌,我的肌肉如同被锐声的喇叭驱赶,呼号着去找寻地铁内的间间店铺,终于买上了耳机。今天,在回程的路上,我戴上了耳机,惊讶于我还没删掉一年半没打开过的音乐app,我好久没有独自面对这些了,好像多年以前的那天,急切地需要有调子笼罩头颅。
在一个人的回程路上,我听着歌,感觉到巨大的否定改造着我生活环境的轰鸣声。我才知道,生活之地将被拆迁改造,而这个乡下小镇的站台周遭的变化,从绿草树荫变成高楼,尘土飞扬,道路变迁,这些环境的变化对我的伤害。我听着情歌,里面唱的是爱情。我更加感觉到那种爱情,友人之间的那种爱情,在那么关键的时刻,令我见到我自己,听见自己所活的环境。令我知道我负荷过载,我承担了什么。
过量的情感劳动总是无声无息,无色无味,它混杂着期盼、欲望乃至正义;它勾连着失望,挫败,心酸和愤怒;它还可能被一边屏蔽一边运作,它是种种忧心、担心、小心……这段时间都发生了什么啊……我知道我朋友每说一个对不起,每自责一番,我就如同遭遇了攻击;我知道在对看着自欺欺人的女性朋友感到绝望;我伤心地看着女孩们被背叛,她们的爱与同情被可估量,被可算计;看那占尽规则便宜的男人,饕厌地揩油……可我不知道它们堆起来那么伤啊。
父权亲自培养了无法承担父姓法则的男性,娇惯出的懦弱根深蒂固,滑动的词语像密不透风的墙,这些人总能在话语中立于不败之地,我看到了我的女朋友们被扼住了喉咙。
一个女孩说:我以前都不会看他一眼的,为何如今这段关系这么的伤?
一个女孩说:我做了噩梦,有一个人欺负别人,游戏规则却不许我们揍他。
但她们总会心软,总会爱着男人的。
这件事令我好伤心。我学着精神分析,以此为武器去刨析。我讲过幽灵女人,女人幽灵的豪言,骂过公主话语和言情小说如毒糖果,怎样规划了女人的理想自我、情感和欲望投射,让女人忽视自己的勇气,迷失方向,看不见自己。
无论我怎样说这话语权力将女孩儿们的爱标签引流了,女孩儿们仍因为渴望被爱,去勇敢地率先爱人的。
我好想撕碎给爱的男人的幻象,说爱情从来不在这些个男人那儿,男人与女人永远是失臂之交。你就说性爱吧,女人的性爱如同濒死一般,与死亡冲动紧密联系,颠倒无常。可这些个男人各个这么能算的,性之于他是胯下二两肉保守安全的幻想,他总是被词语温暖保护的宝宝,是他妈眼里的乖乖,当一个真正的女人,感于欲望的女人,敢将性露出来的女人,他们会一边说刺激,一边逃跑,安全地呆在屏幕后看黄片就好。越是性感的女人越把来自死亡的阉割焦虑永远暴露于其顶伤。女人在深处被话语折叠成既生又死,无论生还是死,之于这样的男人,这总是阉割他的那把刀,这就是他无法理解的定时炸弹。他只会恨死阁楼上的疯女人,最后互相撕碎。
“可我还会想着他。”
“男人就像个谜一样。”
与其问“女人究竟在欲望着什么”,不如问,为什么女人的投射的欲望无法返回到她自身,而只能通过爱情投射到一个异性身上。女人到底被削减了什么?

我翻阅着穿越耽美文中对性爱的描写,那男人的性如同快死了一般,上次读到类似的描写还是弗洛伊德五大案例中,在成为首席大法官后发病,相信自己成了上帝的淫荡的妻子的“施瑞伯大法官”的笔记中。小说中的男人逐渐放弃后天建设起来的防御,把在无辜的他放入肮脏的性,拉坠到深渊之底与死神共舞。
每一场狂欢都是死亡呼啸的喇叭,月经的血激荡流淌,我在地铁上来了一段将男人按在道德法则上摩擦,手握权力的幻想。
还有一些故事会主角或配角对母亲的执着。明明是虚构的故事,却能将爱的吸引不过是因这起源之地、原初之爱的求而不得这一真相隐隐说清了。我保持着男性般的造型,也不过是因为我与母亲潜意识里的共谋:我得像我爸,否则母亲看不见我,我就难以存在。
我今天见的朋友说,她深深地怀疑自己的存在。
即便我能说出“幽灵女人”来揭示女人的处境,我面对的她的困境,就是她的困境本身。否定发着巨大的轰鸣,滚滚。整洁被规划好的商业街,将自然原生的一切都铲除了,我们的皮肤一点泥土都不需要沾到,树草也都按我们想的那样长着,格子屋与快递寄存箱一样,分不清里头的是人还是被踢来拿去的快递。
拉康在讲《被窃的信》的时候说,人们总被放到能指的链条(话语的运作)上,总被那能指的运作所支配,看似人们可以拥有它,但它总还能赤裸裸地隐形于人们的眼中,它甚至被人们遗忘……可它还在运作。
对生命赤裸的人来说,这个链条荒谬地运作着,人们如傀儡般。现实如此赤裸刺人,暴力如大音声稀,大象无形,人们熟视无睹,乐观向上。而看见的人就像开了天眼看尽魑魅魍魉的、独行的幼儿一样。

我跟她说,我现在又重新相信绘画了,无论是否学了套路,有没有天赋,只要我们为自己画,绘画就是诚实的,它就是你说的那个“不变的东西”。
我们谈到关系,爱对精神病的帮助,我说我还相信艺术,不是那种被展览的艺术,是为了自己的那种。好像一些歪扭快活的缝纫啊,自然欢欣的身体舞动啊,瞎突突的绘画啊,被拨动的琴弦,心里自己流出来的歌啊……
反正我相信那快活地发泄而出的艺术,身体甩动留下的痕迹,梆梆作响的肉体,被紧紧捆绑而出的皮肉边,哗啦啦的文句,晃晃的昏黄的灯,能被回应被接住的女孩儿,抛起抱下的枕头……
女孩儿,女孩儿,女朋友们,
“我们的敏锐使我们以肉搏的姿态站在这冰天雪地之中。所以,让我给你穿上衣服吧,让我带你制作自己的衣裳吧。你已经学会了最初的缝补,很快将会拥有自己创造的衣物,塞以棉絮,缝以金线,披上布,绑上皮,戴上手套,做上一顶好帽子。你像鸟儿一样有彩色的羽毛,像骑士一样豪气壮胆,有着女巫的鞋子和法术,这些曾经伤害过幼小的你的残酷爆裂的链条,将不能再耐你何。你在成长的,我们有一天能直视那人性的恶与善混合的一面,去面对那些极不协调的暴力与良善的现场。那时我们会感到悲悯,而非恐惧。”(给小龙的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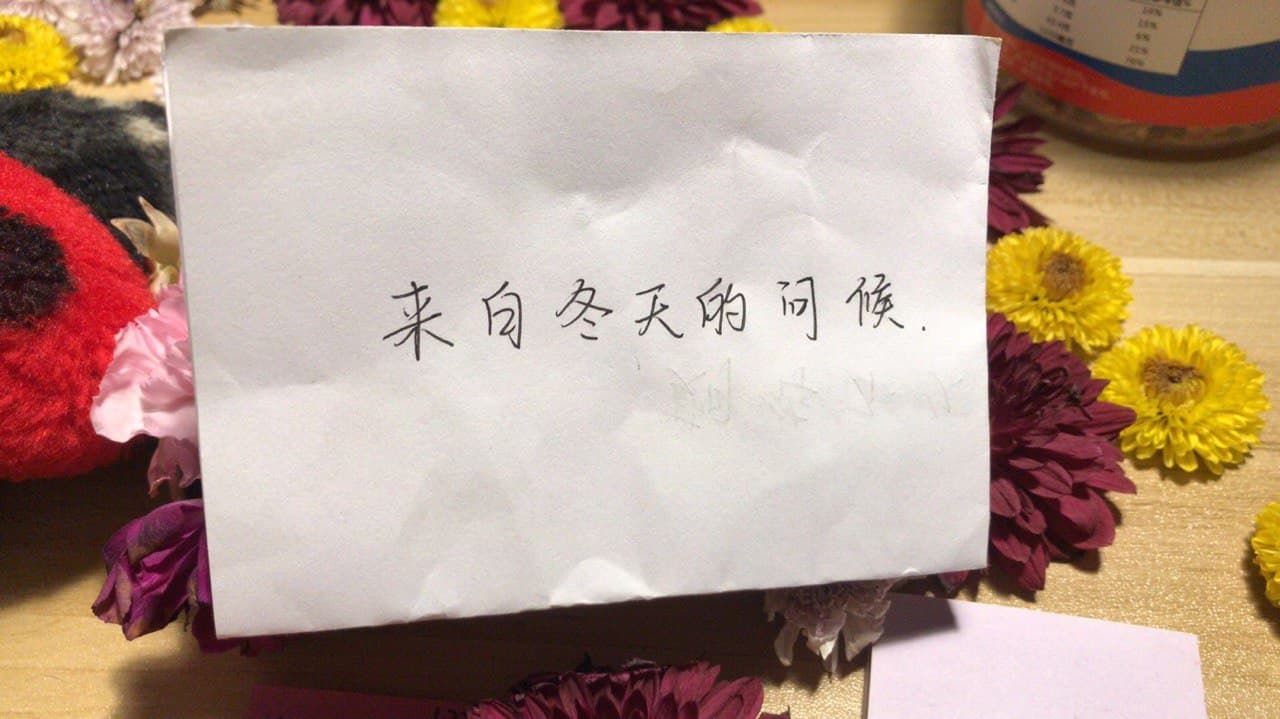
如果我来写修仙小说,就写一个凡人,ta记忆中存在的地方总因为修士们的争斗导致的山崩地裂而改变了样貌,ta迁徙、漂流,记忆中的家园总是难以再寻,神仙的力量仅仅是力量的存在,关于神仙的话语并不包裹这赤裸严厉的天地。哎,就像一个沮丧的游魂一样,你说,在这样的小说中,能不写那什么唯一不二的爱情吗?生活在这般天地的女孩儿们,能放下爱情吗?哪怕一点可能,也要被爱啊。最好是那不顾一切的爱来掩埋住这荒谬沉寂的现场,靠付出一切来遮掩看得见魑魅魍魉的眼睛,麻痹并不存在的痛苦。
出口究竟在哪呢?女孩儿,我的好女朋友们,请求你们看看自己为自己所作的努力,自己的勇气:探寻秘密的家书,仅是为了项目吗?看了一本本各个学说的书,是为了知识吗?忧心于社区孩子们的关系,仅是为了孩子们吗?在情爱关系中做的每一个决定,仅是为了得到那个男人的爱吗?
在这每一件你做过的事中,都浸润着焕焕明朗的勇气,在这儿,你难道不是存在着的吗?你就是存在的呀,你是做了这些事情的人呀!这些事,都是我们因为我们的身体呼唤着我们去往我们遭遇的现场,它不断呼喊,要我们回应自己,这些既生又死的点让我们卡壳,慢慢来,放松来,看看自己,看看自己发生了什么……我因为爱你们而走向精神分析,也是因为我的过去还没有过去,而是仍在发生。

命运女神的双脚压在肩头,压得心肝肺胃疼,我抓着她的裙摆,令她变作热气球,一起飞过河山,化作冰川,等着春融崩腾而下,去往大海。你们的笑呀,就是那浪花的咆哮。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