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福克纳《我弥留之际》:弥留,是为了刻画曾经存在
致谢微批Paratext刊登本文
连结: http://paratext.hk/?p=26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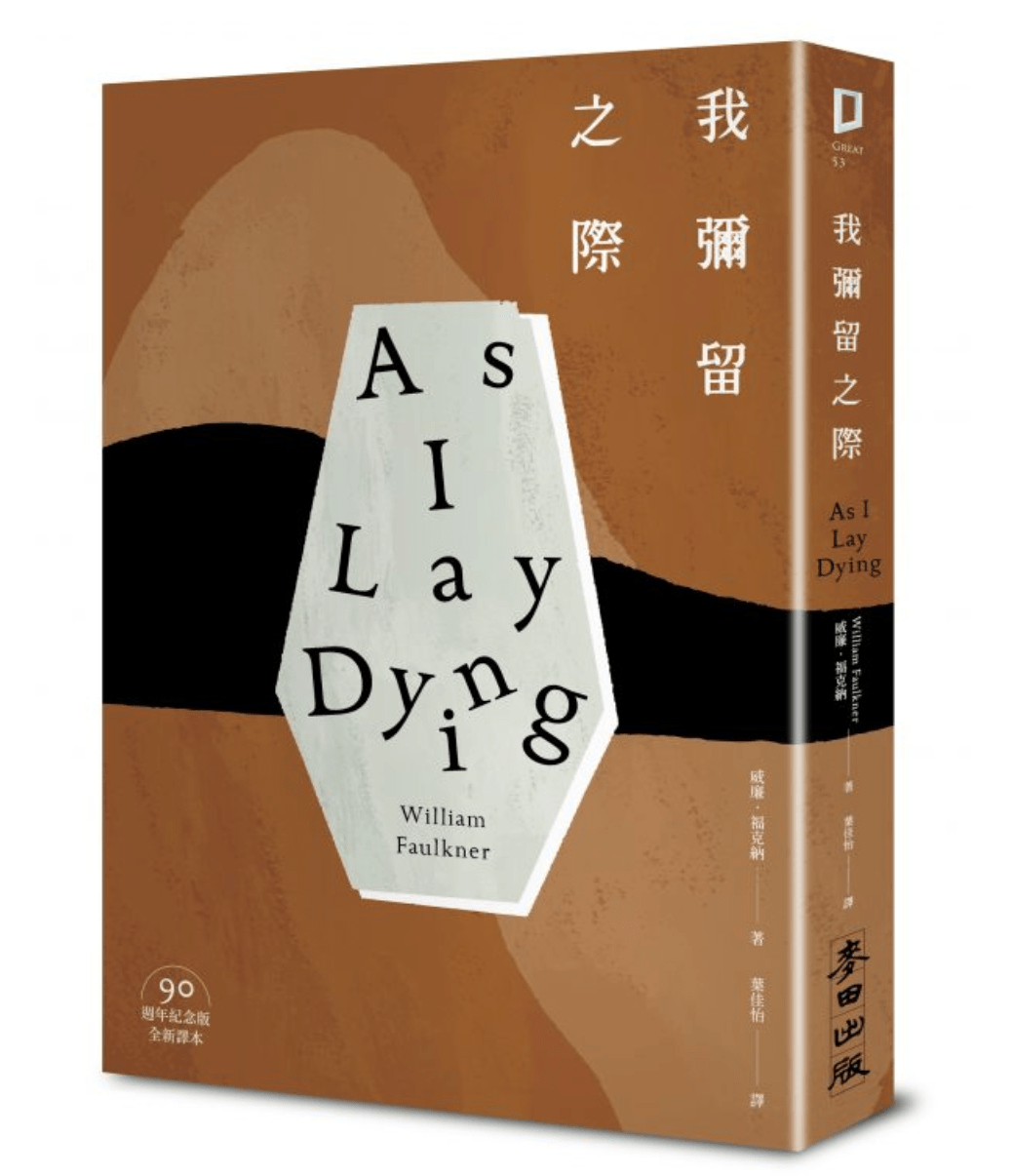
《我弥留之际》是一本风格独特的小说。在这本书里,福克纳选择不以单一的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去描写一个乡下家庭为了送葬亡母,踏上一个充满挫折、艰困的旅程。而是让15个人物的独白交错成全书59篇的章节。营造了一种散乱、去中心化的叙事。这些人物主要是家中的亲人,但也不乏其他途中遇到的角色。仿佛在这些交错的独白里,读者不但感受了亲人死亡的阴影如何弥留、徘徊在各个角色的心中,也在这样的叙事里,产生弥留、徘徊在各个角色间的抽离体验。
去中心化的叙事方式,让这篇小说变得不好读。我们很容易因为多重视角的陈述而迷失故事的情节。变得要翻来翻去,看看人物关系表,反覆阅读不同的陈述来组织、整理事情的全貌。在这角度上,《我弥留之际》就像一个大型复杂的《竹林中》,每个人描述着各自看见的事情,说着自己对他人的揣想。有时相互重叠、呼应,有时则好像是情节的岔开,让读者窥见隐藏的细节。有趣的是,虽然每个篇章都是一个人物的独白,但这种独白,虽是独白,却常常仿佛说的不是自己。事实上角色述说自己心理的描述不多,而总是在不停详细、深刻地描述那些他看到的风景与其他人的对话、举止。在一些不可思议的时刻,人物揣想着别人的情绪、精神,甚至说着别人眼中看到的风景与魔幻的意象。
「凯许喜欢将漫长、悲伤的发黄日子锯成一块块的的木片,再钉成某些玩意……(另一方面)我不认为达尔会发现,坐在晚餐桌前的他,眼神越过食物及桌灯,看的全是从他的脑壳里挖出来的土地光景,以及那片土地之外远方的满地洞穴。」
我们不经想问,一个角色到底是如何知道他人心中涌现的光景?并能够这样栩栩如生地描写出来?在另外一个章节里,去城市送货的达尔,甚至叙述着乡下家中当下夜晚发生的情境。仿佛在这本书中,每个人物都像是一个作者,在一些时刻里拥有超越文本的全知观点,然后如幢幢的影子相互重叠又伸展出新的阴影。
另一个去中心化的叙事所带来的效果,是小说时间感的停滞。因为对读者来说,每次的事件透过这样一层层不同人物对彼此的叙事、描述,变得好像很漫长、没有尽头一样。徘徊再徘徊,弥留再弥留……
「我们继续前进,以一种无比昏沉、梦境般的动态,仿佛无法推断出正在前进的结论,仿佛在我们与目的地之间缩短的不是空间,而是时间。」
送葬是一种移动,然而这股移动却好像在透过移动的过程在抵抗自己。人们虽然在移动,精神却因为习惯移动而陷入恍惚,像乘着缓缓的火车,弥留在某个不清楚自己在哪的地方。这个精神弥留的「地方」福克纳认为不是一种空间,而是一种让人迷失、「出神」的时间。
「他的头低垂,透过不停滴落的水往外看,仿佛透过盔甲的眼部遮罩往外看,那眼神漫长地穿越整座村庄,抵达依偎在断崖边的谷仓,仿佛透过眼神,将一匹隐形的马敲打出来。」
透过每个人物的眼睛,福克纳在这本书里捕捉角色们各种「弥留」、像引文里那种「出神」入化的瞬间。在这些时刻里,弥留成了某种洞察,也成了某种恍惚。有目标却好像失去方向。
眷恋,就像一种弥留,有目标却失去方向感。并使人们让自己被一种无能为力给包覆。试着在这种包覆里滞留在一个过往或想像的时空中。而那种「无能为力」,首先针对的是亲人死亡的事实。有趣的是,福克纳说了这句话:
「到头来你会明白— — 死亡,只是一种心灵作用。」
家人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故事中每个角色的内心。但福克纳提醒我们死亡和死掉并不一样,死掉是失去生命的状态。但很多事情尽管不会让我们死掉,却会令我们感受到死亡。小说里,儿女们的母亲— — 爱笛的确死了。但对她的情感、记忆就像死亡的感觉一样仍然弥留在角色们的内心。除此之外,让读者突然感到惊恐的,是在59篇的章节里,有一篇是死去的爱笛所说出的话语。仿佛她虽然死去,但阴魂仍然不散。其中我们可以发现,爱笛的婚姻生活并不美满,她认为自己走入了被名为「家」的骗局。而人们所说的爱,不过是一个空壳子的词汇,为的是让她能填补他人心中的匮乏。
丈夫安斯与儿女们在送葬过程中所承受的阴影,除了是死亡带来的,另一个面向便是他们对爱笛的亏欠,以及,爱笛对「家」的义务所感到的愤怒、不满反过来产生的影响(无法给予爱)。让大家都希望借着这次的送葬,爱笛能够「安息」。
就像寺山修司曾在《我这个谜》写到的话:「死亡不过是人为了活着所创造出来的虚构罢了。」「安息」也只是一种宗教性的虚构。爱笛的确死了,但尽管大家都知道这个事实,但整个葬礼大费周章的准备却暗示死亡对人而言从来就不只是死掉那么简单。因为或许需要「安息」的根本不是死者,而是那些仍然还活着的人。这场漫长的送葬,真正要送葬的也不是躺在棺材中的爱笛,而是仍然活在家人心中的爱笛。
送葬,成为一个让人能够弥留、能够眷恋、体会逝去与悲恸的旅程,让他们以各自的方式缅怀心目中的母亲。对家中最小、尚不理解死亡是什么的儿子— — 瓦达曼来说,他不相信躺在棺材中的是母亲,认为母亲肯定是变成一条鱼了,离开这个对她不好的家。只要他仍然持续每天捕鱼,某一天他一定可以在河里找到愿意回来的母亲。而爱笛生前偏爱的三子珠尔,则将失去母亲的悲恸转换到自己最钟爱的马匹身上,仿佛母亲对他而言变成了一匹马,想在与马的抚摸、陪伴中找到过往的依恋、爱慕。身为木匠的长子— — 凯许对死亡没有那么多想像,但非常卖力地打造一座棺材,来纪念自己的母亲。次子达尔和长女杜葳则对母亲的死保有某种冷漠和抽离,一方面爱笛在生下达尔时已经对生活感到绝望,不曾认真爱过达尔,让达尔甚至说:「我没有母亲。」另一方面,杜葳因为珠胎暗结,却不敢和母亲诉说,遂独自承受着压力躲避母亲的关爱。而丈夫安斯,正如爱笛的自白,虽然活着但其实早已死去。失魂落魄地只想把亡妻送到她的故乡:杰佛森城市,哪怕因为暴风雨途中的桥梁已断,需要多天困厄的路途。
如果能这么地沉浸在各自的弥留、眷恋里,这趟旅程或许对彼此来说也是正向的。但上天偏偏不让这种事发生。故事里的角色最后都落得凄惨的下场。在强行过河的时候,邦德伦一家出了事故,拉车的骡子全数溺毙,凯许断了腿。为了继续路途,珠尔最钟爱的马匹被安斯擅自卖掉。而达尔后来发疯,烧掉一座谷仓后被逮捕。杜葳私底下想要买药堕胎,却惨遭诱拐。瓦达曼也没能得到他向往的小火车。而安斯虽然最后现出他自私的目的(再娶),但在福克纳的文笔下只让我们觉得他仍旧是一个悲哀的人。
As I Lay Dying,这本小说的书名出自希腊史诗《奥德塞》中,阿迦曼侬回忆自己被妻子刺杀时,垂死之际想要反抗的心理。从这方面来看,正如译者在译序中提到的,以「弥留」一词理解书名,虽颇有意境,却可能忽略这种垂死之际的挣扎感。因为仔细想来,福克纳想描述的那种弥留,除了是种无能为力的眷恋,同时也在借着送葬艰困的过程表现书中人物面临的现实困境。这股现实困境,除了是书中人们在家境、路途上遇到的灾难。若回到历史脉络来谈,与1920、30年代城市繁荣、乡村衰落的背景有关。而《我弥留之际》在深入书中人物失去亲人的悲恸精神外,也借着送葬的路途描写城市人对乡村人处境的无法同理(甚至歧视)。而爱笛的烦恼某个程度上就像是一个城市人嫁到乡村后所遇上的困境。反过来谈,当安斯一家拖着早已腐臭的棺材进入城市街道遭人诟病时,那棺材似乎象征的并非一个人的死亡,而是整个乡村的萧条、破败和狼狈对城市的叩问。
所有的弥留,还有那垂死之际的挣扎,随着葬礼的尾声、每个人向往的失落,都变得越来越强烈,甚至让人感到一股残酷跟冷漠。并在最后一刻以那潦草、仓促、几近全无描写的埋葬,直接回归成终究徒劳、悲恸、无法挽回的现实。福克纳笔下试图捕捉弥留的书写,在此时,也就像是对某个事物曾经存在的刻画,如同沉默、无人过问的丧礼,埋葬在生与死、存在与不存在之间。
(文章同步发布于方格子部落格: 文学实验室)
Medium: https://pse.is/R7YT3
方格子: https://vocus.cc/1111/home
FB粉专: https://pse.is/PEVPU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