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福克納《我彌留之際》:彌留,是為了刻畫曾經存在
致謝 微批 Paratext 刊登本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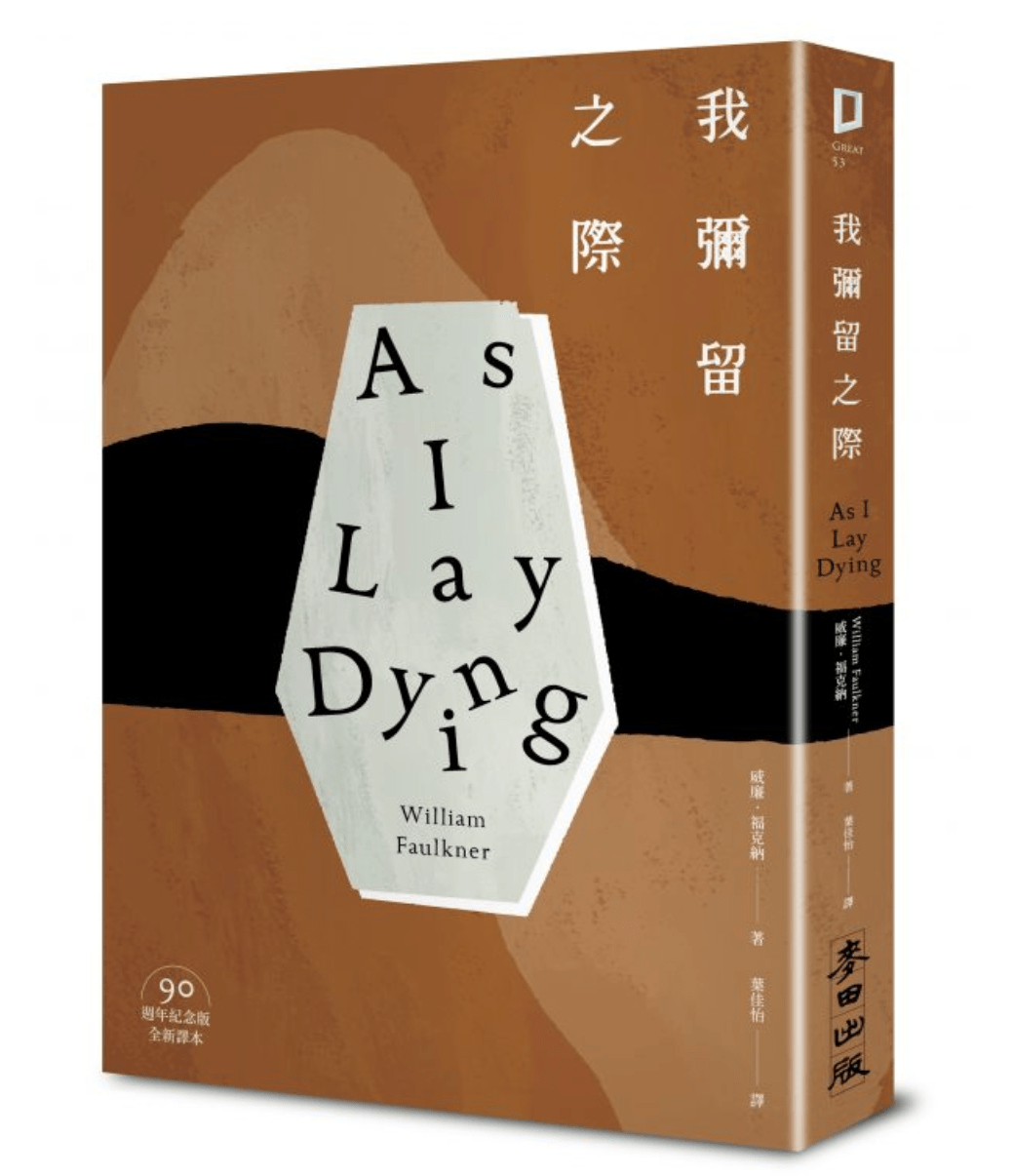
《我彌留之際》是一本風格獨特的小說。在這本書裡,福克納選擇不以單一的第一人稱或第三人稱去描寫一個鄉下家庭為了送葬亡母,踏上一個充滿挫折、艱困的旅程。而是讓15個人物的獨白交錯成全書59篇的章節。營造了一種散亂、去中心化的敘事。這些人物主要是家中的親人,但也不乏其他途中遇到的角色。彷彿在這些交錯的獨白裡,讀者不但感受了親人死亡的陰影如何彌留、徘徊在各個角色的心中,也在這樣的敘事裡,產生彌留、徘徊在各個角色間的抽離體驗。
去中心化的敘事方式,讓這篇小說變得不好讀。我們很容易因為多重視角的陳述而迷失故事的情節。變得要翻來翻去,看看人物關係表,反覆閱讀不同的陳述來組織、整理事情的全貌。在這角度上,《我彌留之際》就像一個大型複雜的《竹林中》,每個人描述著各自看見的事情,說著自己對他人的揣想。有時相互重疊、呼應,有時則好像是情節的岔開,讓讀者窺見隱藏的細節。有趣的是,雖然每個篇章都是一個人物的獨白,但這種獨白,雖是獨白,卻常常彷彿說的不是自己。事實上角色述說自己心理的描述不多,而總是在不停詳細、深刻地描述那些他看到的風景與其他人的對話、舉止。在一些不可思議的時刻,人物揣想著別人的情緒、精神,甚至說著別人眼中看到的風景與魔幻的意象。
「凱許喜歡將漫長、悲傷的發黃日子鋸成一塊塊的的木片,再釘成某些玩意……(另一方面)我不認為達爾會發現,坐在晚餐桌前的他,眼神越過食物及桌燈,看的全是從他的腦殼裡挖出來的土地光景,以及那片土地之外遠方的滿地洞穴。」
我們不經想問,一個角色到底是如何知道他人心中湧現的光景?並能夠這樣栩栩如生地描寫出來?在另外一個章節裡,去城市送貨的達爾,甚至敘述著鄉下家中當下夜晚發生的情境。彷彿在這本書中,每個人物都像是一個作者,在一些時刻裡擁有超越文本的全知觀點,然後如幢幢的影子相互重疊又伸展出新的陰影。
另一個去中心化的敘事所帶來的效果,是小說時間感的停滯。因為對讀者來說,每次的事件透過這樣一層層不同人物對彼此的敘事、描述,變得好像很漫長、沒有盡頭一樣。徘徊再徘徊,彌留再彌留……
「我們繼續前進,以一種無比昏沈、夢境般的動態,彷彿無法推斷出正在前進的結論,彷彿在我們與目的地之間縮短的不是空間,而是時間。」
送葬是一種移動,然而這股移動卻好像在透過移動的過程在抵抗自己。人們雖然在移動,精神卻因為習慣移動而陷入恍惚,像乘著緩緩的火車,彌留在某個不清楚自己在哪的地方。這個精神彌留的「地方」福克納認為不是一種空間,而是一種讓人迷失、「出神」的時間。
「他的頭低垂,透過不停滴落的水往外看,彷彿透過盔甲的眼部遮罩往外看,那眼神漫長地穿越整座村莊,抵達依偎在斷崖邊的穀倉,彷彿透過眼神,將一匹隱形的馬敲打出來。」
透過每個人物的眼睛,福克納在這本書裡捕捉角色們各種「彌留」、像引文裡那種「出神」入化的瞬間。在這些時刻裡,彌留成了某種洞察,也成了某種恍惚。有目標卻好像失去方向。
眷戀,就像一種彌留,有目標卻失去方向感。並使人們讓自己被一種無能為力給包覆。試著在這種包覆裡滯留在一個過往或想像的時空中。而那種「無能為力」,首先針對的是親人死亡的事實。有趣的是,福克納說了這句話:
「到頭來你會明白 — — 死亡,只是一種心靈作用。」
家人死亡的陰影籠罩著故事中每個角色的內心。但福克納提醒我們死亡和死掉並不一樣,死掉是失去生命的狀態。但很多事情儘管不會讓我們死掉,卻會令我們感受到死亡。小說裡,兒女們的母親 — — 愛笛的確死了。但對她的情感、記憶就像死亡的感覺一樣仍然彌留在角色們的內心。除此之外,讓讀者突然感到驚恐的,是在59篇的章節裡,有一篇是死去的愛笛所說出的話語。彷彿她雖然死去,但陰魂仍然不散。其中我們可以發現,愛笛的婚姻生活並不美滿,她認為自己走入了被名為「家」的騙局。而人們所說的愛,不過是一個空殼子的詞彙,為的是讓她能填補他人心中的匱乏。
丈夫安斯與兒女們在送葬過程中所承受的陰影,除了是死亡帶來的,另一個面向便是他們對愛笛的虧欠,以及,愛笛對「家」的義務所感到的憤怒、不滿反過來產生的影響(無法給予愛)。讓大家都希望藉著這次的送葬,愛笛能夠「安息」。
就像寺山修司曾在《我這個謎》寫到的話:「死亡不過是人為了活著所創造出來的虛構罷了。」「安息」也只是一種宗教性的虛構。愛笛的確死了,但儘管大家都知道這個事實,但整個葬禮大費周章的準備卻暗示死亡對人而言從來就不只是死掉那麼簡單。因為或許需要「安息」的根本不是死者,而是那些仍然還活著的人。這場漫長的送葬,真正要送葬的也不是躺在棺材中的愛笛,而是仍然活在家人心中的愛笛。
送葬,成為一個讓人能夠彌留、能夠眷戀、體會逝去與悲慟的旅程,讓他們以各自的方式緬懷心目中的母親。對家中最小、尚不理解死亡是什麼的兒子 — — 瓦達曼來說,他不相信躺在棺材中的是母親,認為母親肯定是變成一條魚了,離開這個對她不好的家。只要他仍然持續每天捕魚,某一天他一定可以在河裡找到願意回來的母親。而愛笛生前偏愛的三子珠爾,則將失去母親的悲慟轉換到自己最鍾愛的馬匹身上,彷彿母親對他而言變成了一匹馬,想在與馬的撫摸、陪伴中找到過往的依戀、愛慕。身為木匠的長子 — — 凱許對死亡沒有那麼多想像,但非常賣力地打造一座棺材,來紀念自己的母親。次子達爾和長女杜葳則對母親的死保有某種冷漠和抽離,一方面愛笛在生下達爾時已經對生活感到絕望,不曾認真愛過達爾,讓達爾甚至說:「我沒有母親。」另一方面,杜葳因為珠胎暗結,卻不敢和母親訴說,遂獨自承受著壓力躲避母親的關愛。而丈夫安斯,正如愛笛的自白,雖然活著但其實早已死去。失魂落魄地只想把亡妻送到她的故鄉:傑佛森城市,哪怕因為暴風雨途中的橋樑已斷,需要多天困厄的路途。
如果能這麼地沈浸在各自的彌留、眷戀裡,這趟旅程或許對彼此來說也是正向的。但上天偏偏不讓這種事發生。故事裡的角色最後都落得淒慘的下場。在強行過河的時候,邦德倫一家出了事故,拉車的騾子全數溺斃,凱許斷了腿。為了繼續路途,珠爾最鍾愛的馬匹被安斯擅自賣掉。而達爾後來發瘋,燒掉一座穀倉後被逮捕。杜葳私底下想要買藥墮胎,卻慘遭誘拐。瓦達曼也沒能得到他嚮往的小火車。而安斯雖然最後現出他自私的目的(再娶),但在福克納的文筆下只讓我們覺得他仍舊是一個悲哀的人。
As I Lay Dying,這本小說的書名出自希臘史詩《奧德塞》中,阿迦曼儂回憶自己被妻子刺殺時,垂死之際想要反抗的心理。從這方面來看,正如譯者在譯序中提到的,以「彌留」一詞理解書名,雖頗有意境,卻可能忽略這種垂死之際的掙扎感。因為仔細想來,福克納想描述的那種彌留,除了是種無能為力的眷戀,同時也在藉著送葬艱困的過程表現書中人物面臨的現實困境。這股現實困境,除了是書中人們在家境、路途上遇到的災難。若回到歷史脈絡來談,與1920、30年代城市繁榮、鄉村衰落的背景有關。而《我彌留之際》在深入書中人物失去親人的悲慟精神外,也藉著送葬的路途描寫城市人對鄉村人處境的無法同理(甚至歧視)。而愛笛的煩惱某個程度上就像是一個城市人嫁到鄉村後所遇上的困境。反過來談,當安斯一家拖著早已腐臭的棺材進入城市街道遭人詬病時,那棺材似乎象徵的並非一個人的死亡,而是整個鄉村的蕭條、破敗和狼狽對城市的叩問。
所有的彌留,還有那垂死之際的掙扎,隨著葬禮的尾聲、每個人嚮往的失落,都變得越來越強烈,甚至讓人感到一股殘酷跟冷漠。並在最後一刻以那潦草、倉促、幾近全無描寫的埋葬,直接回歸成終究徒勞、悲慟、無法挽回的現實。福克納筆下試圖捕捉彌留的書寫,在此時,也就像是對某個事物曾經存在的刻畫,如同沈默、無人過問的喪禮,埋葬在生與死、存在與不存在之間。
(文章同步發佈於方格子部落格:文學實驗室)
Medium:https://pse.is/R7YT3
方格子:https://vocus.cc/1111/home
FB粉專:https://pse.is/PEVP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