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学为认同发声III》创造更理想的社会共同体ft.杨佳娴、李琴峰、Apyang Imiq(程廷)

主持人:杨佳娴;与谈人:李琴峰、Apyang Imiq(程廷)
文字整理:李怡坤、陈柏均
➤学习部落文化时,要找到舒服的状态很重要
杨佳娴: Apyang的书有提到Gaya ,意义很复杂,简单来说可以指「禁忌」。你觉得部落里面的Gaya ,是可以挪动的吗?
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说要复兴部落文化、学习部落文化,其实也包含遵守这些Gaya 。可是如果你喜欢的自己的样子,或者你感兴趣的事情触犯了Gaya的话,到底该怎么做?比如说,社会还是会不断变化,新观念也会传到部落里面, Gaya是不是因此有可能被松动呢?
我记得你在书里有写,作为生理男性,你非常热心学习务农还有猎人的文化,可是你同时对织布也很感兴趣。你描写到,你想要碰织布机的时候,有些人会严厉地说绝对不可以,因为你是男性,你不可以碰。
你既学习猎人也学习织布,是有意为之吗?你希望去挑战Gaya吗?

Apyang:我们讲Gaya ,其实不是专指禁忌啦,可以比较概括诠释的讲是「文化」。我其实不是有意为之,只是纯粹觉得很好玩,这跟我的成长背景有关。虽然我是在部落长大,一直到大学才离开。前阵子接受专访时被问到,我在台北市大概待了10年,会不会觉得我在台北的阶段就是被汉化的过程。后来想一想,其实不用离开部落,原住民在家里就会被汉化、现代化,或者是各种比较复杂的情境。
Gaya对我来讲,本身不是一个固着、不变的点。 「传统」本身就会变,比方像结婚、离婚、上山、买车、当兵,都会杀猪,这个我们也叫Gaya 。有些杀猪的原因其实跟以前不一样,怎么去杀猪、怎么去分猪,也跟过去不一样。
以前自己还不太懂部落文化的时候,总会觉得,很难得可以听到一些Gaya 。比方猎人上山的时候,在山林里面不可以放屁,会影响到你的收获。但是实际跟着长辈上山的时候,发现他怎么在放屁?其实很多我们把它视为不能变动的东西,实际上现实情境就有很多松动的可能。我也听过有的部落的女生是学习打猎的,因为她家真的就没有男生,她们家就要有人去打猎,她还是得去做。
所以对我来讲, Gaya是一种感觉,当我们对自己的认同,或对自己的文化有很强大认同的时候,应该是舒服的状态,我们要让自己找到那样的状态。不是说我在学习文化的路上应该怎么样,而是要让自己找到一个舒适的状态,这才是比较重要的。
➤用文学探知自己的处境
杨佳娴:提到返乡、学习部落文化,想到的形象都是很任重道远,好像承担起某种时代责任的感觉。但我觉得Apyang说的很有趣,也很人性化,「舒适」这件事情是满重要的。而且,传统确实不是僵化的、等大家挖出来的古物,应该是有弹性,而且也是逐渐生成、不断变化的东西。我们认识这个文化的方式可能也在变化中。
接着我想回到琴峰这边。在台湾,因为同志书写已发展满长的时间,甚至可以说台湾同志文学已有自己的小传统。读琴峰的作品时,常常会指涉别的文学作品,从古典到现代,或者不同国家的文学等等。很多台湾性别书写的作家,比如邱妙津、赖香吟、陈雪等等,在你的作品当中很明确地现身。你的其他作品中,也有写旧体诗送给心仪对象的情节。似乎对你的小说人物来说,文学是非常重要的认识自我的方式,同时也是传达感情的管道。
因此,想请你谈一谈,对你的性别书写而言,文学作为资源或中介物,会起什么作用?你是有意把这些东西放到作品里,希望让读者体认到这样的书写传统吗?
李琴峰:首先,以《独舞》来讲,与其说有意,倒不如说是自然的。首先设定主角是台湾人,台湾的同志,同时又喜欢文学,在这个世代,喜欢文学又是女同志,有很大机率会碰到邱妙津,所以我觉得把邱妙津放进来是满自然的。再加上主角是1989年生,她接受的国、高中国文教育,也都是以古典中文、古典文学为主,所以在这个作品中去引述邱妙津、赖香吟或一些古典诗词,是满自然的事情。
以我自己来讲,文学的确在我对世界的认知过程,或对自我的认知过程起到满大的作用,当然并不是绝对、不是全部,但它起到满大的作用。它让我们能够用俯瞰的视角,或比较全知、宏观的视野,去看到自己的处境,看到自己的生命,然后渐渐建立自我认同。当然不是全部的人都是这个样子,但是对我,或者对赵纪惠来讲,它就是满重要的。
杨佳娴:我自己就是从邱妙津的书才知道太宰治。我觉得,文学本身会形成某种传递,我可以在这个人的书里面,发现其他阅读的可能性,像一条长河一样,不断传递下去,也因此形成自己的阅读版图,然后又会反过来哺育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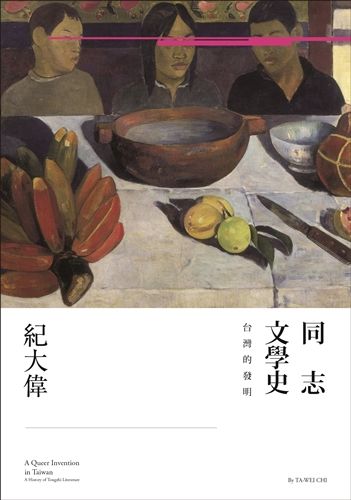
我当然也是一个文学青年,在读《独舞》以及琴峰其他作品的时候,都会感受到文学的力量。这也可以回应到纪大伟,他在《同志文学史》里特别提到,过去报章媒体关于同性恋的知识或描写,常常是负面或耸动的新闻,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同志,要怎么认识自己、怎么想像未来等等,可能要透过文学(也许有些人会透过影视作品)。显然在某些时代,文学是一个满重要的管道。
➤〈告白河坝〉朗读
杨佳娴:镜好听推出了《独舞》、《我长在打开的树洞》的有声书,是透过专业声音主播朗读。但这次收到许多读者回馈,大家非常期待能听到两位作者亲「声」上阵。接下来我们要邀请两位作者来读读其中的片段,先邀请Apyang。
Apyang:我要读的是〈告白河坝〉。写完这篇的时候,我的室友,也就是我的配偶,其实正在睡觉。当我写完的时候,我就在他的耳边念给他听。这其实是我写给他的一封情书,也是我写给自己部落的一封情书。
你给我勇气,让我变强壮。你无惧出柜,一派轻松地跟身边人说你的性向,那种弹性像水,我也想像水,自在地分享生活。回乡定居本是舒适而非禁锢,相爱是人的本性,这个部落有太多风花雪月:房间里的床垫、山上的工寮、水沟旁的草丛、卡拉OK的厕所,学校教室的后面……每一则都让我称羡不已。
爱情充斥支亚干,河水懂得吞噬,河水不会排除,我对你的喜爱和性冲动也是如此,悉数包含在流动的支亚干溪里。
河坝上,我说好多支亚干的故事给你听,其中有打开的树洞,这条溪从白石山往东流,水冲到河坝这边,开口突然扩张,像一张大嘴,像一个洞穴,把我们一起含住,吞咽在树洞里,我们的Bhring形成龙卷风,原地旋转直到消逝在水波里。
那一晚,我们接吻拥抱,交换彼此的风。白天的时候,你回传讯息:「我们在一起吧!」
杨佳娴: 〈告白河坝〉这篇是整本书里最甜美的一篇。用非常纯真而大胆的方式,把性作为爱情的重要组成写出来。在台湾过去的同志书写里,很少有这么自然的表达。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大家不写性,满多写性的东西,但是这篇是在散文这个文体里非常直接的告白,毫不扭捏。
接下来请请琴峰朗读所选的段落。
➤《独舞》朗读
李琴峰:接下来我会朗读《独舞》第十六章后半,主角到达雪梨走过同志游行后,抵达林肯岩的内心独白。
她回想起这一路上看过的风景,以及旅途中邂逅的人们。被氤氲水气覆盖而显得朦胧的金门大桥,以及全身被雨淋湿、静静望着桥的Caroline。如白银巨龙般蟠踞群山的长城,以及仰望长城的乌仁图娅。六色彩虹四处腾跃的游行队伍,以及一边观赏游行队伍一边嘻笑打闹的柏彦与八四。夜不眠的纽约曼哈顿,石墙酒吧茜红色的鲜艳霓虹,冬日暖阳舒适地糁在中央公园里。秦始皇陵与华清宫南倚骊山北临渭水,大雁塔南侧玄奘三藏的塑像庄严伫立,一旁广场上各个世代的男男女女欢欣跳着广场舞。绯红的紫禁城覆着纯白的雪,狭窄微脏的胡同受雾雨濡湿。然后是雪梨,碧蓝得使人不禁吞声的天空与海洋,群山神圣几乎要让人忘却世间所有苦痛的存在──
她闭上双眼,霎那间苍穹、白云、群山、绿树都为无边的黑暗所覆盖。二十八年的人生里所见过的人事物,那些景色与人物表情历历在脑海里打转翻腾。而后渐渐地,那些景象也沉淀了下来,不久,知觉的表层回归到不兴一丝波纹的平静水面。
一滴泪沿着脸颊滑落,感受到那滴泪滑下的同时,她才注意到,自己有多么醉心于这尘世的美,多么由衷地爱着这个尘世。这世界啊,人要求生则嫌太过狭窄拘束,要求死却又有太多羁恋牵绊。直到经过与世界作别的旅途,真正站在生与死的边界上,她才重新体认到自己对这世界的眷恋之情。
➤住在太鲁阁族部落的男同志情侣幸福之道
杨佳娴: 《我长在打开的树洞》这本书出版之后,在关注性别、原民书写的朋友当中引起满多讨论的。 Apyang说,大家一直关注返乡青年这种严肃问题,他希望大家可以聊聊生活化的事情,所以我想问一些真的超生活化的事:请问在部落里,同志们如何交男朋友?
搞不好大家还是透过交友软体——这个问题好像有点预设了什么。但是当我们对部落生活非常陌生,是个原民文化麻瓜,可能会想到这样的事情。你跟你的伴侣是住在部落里吗? (Apyang:对。)你们一起住在部落里,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他会跟着你一起去打猎吗?他可以跟你一起去打猎吗?你觉得最大的困难跟考验是什么?
Apyang:一开始还不太敢跟别人公开关系的时候,家里的人都知道,但我部落里的家族总是来来去去,有很多亲戚朋友、好朋友会进来我家,然后看到他,就会问他是谁?我爸妈不知道怎么回答,就会说他是煮饭的。一开始他觉得很困扰,觉得奇怪,为什么他只能被介绍成这种角色。
我觉得快乐的事情,是他跟我一起,在我喜欢的地方一起生活。我们不是一直都住在我的地方,我们其实是隔壁部落、隔壁村,所以我们会两边轮流住,有时候住我们部落,有时住他那边。我觉得可以住在自己喜欢的地方,跟喜欢的人住在一起,就是最快乐的事情,然后可以跟自己的家人或是对方的家人处得很好,就很幸福。

➤不同于既有的社会、国家、家国的想像共同体
杨佳娴: 《我长在打开的树洞》整本书,如果大家是从第一页开始慢慢读到最后,会觉得最后一篇文章太过分了吧,放闪放成这个样子!全书最后一句话是:「我们在一起吧」。
接下来想要问琴峰。 《独舞》里面出现了来自不同国家的同志,因为各种偶然与必然而相遇,这样的情节在琴峰其他作品里也会出现。对你来说,同志是否会有一种隐隐然联合起来、成为彼此力量的可能性?换言之,在这个不见得美好的现实世界,隐然存在着像同志共和国一般的可能性。你的小说,最后会希望提出这样的可能性吗?
李琴峰:我觉得,并不是我愿不愿意提出这样的可能性,而是这样的可能性的确存在。不过,我觉得它比较像是想像的共同体,是一种不同于既有的社会、国家,或者是既有组织的想像共同体。这样的连带,可能建立在虚构的基础之上,但是我们会去想像,我们共享一些历史、一些经验、一些痛苦。
比方说,我们讲到同志权利的历史,就会回溯到石墙运动,回溯到爱滋的历史等等,会立刻想起这些东西。基于想像共同体的虚构连带,我们也可能会去同理——当然不可能完全感同身受,但是我们也可能试图同理——车臣在排斥同志的时候,同志族群是经历非常大的痛苦。
又比方说,俄罗斯推出反同志宣传法,我们会觉得非常气愤。又或者说,阿富汗又遭到塔利班的支配,很多女性以及同志族群就会遭到打压、遭到压迫,甚至会有生命危险,我们就感到痛心疾首。

其实讲残酷一点,这些好像并不是跟我们那么相关,但基于你是女性,或者同志族群,基于这样的共同想像,我们能够想像这些人的痛苦,想像这些痛苦是不是有可能、或者过去真的发生在自己身边。
我有一次到中国旅行,因缘际会认识了几个中国的女同志,她们就带我去玩。我跟她们真的只有一面之缘,但她们跟我说,天下拉拉本一家。我感觉非常奇妙,我跟她们只见过一次,或者说根本不认识,只是我认识A,然后A介绍我认识B。 A在北京,她的朋友B在西安,然后我到西安,B还会带我去逛。
我觉得这是一种满奇妙的连带,你也可以说,它是一种反讽的连带:假如没有社会压迫、不是弱势的话,可能就不会存在这样的连带。但这样的连带,的确是一个可能性,让我们试图去抵抗男性霸权、异性恋霸权、顺性别霸权等等社会的压迫与歧视,而成为这样的力量。
杨佳娴:我还满喜欢想像这种同志共和国的。在琴峰的作品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文学共和国的存在,大家以文学作为桥梁或平台,让心灵找到可以对话或安住下来的可能性。
➤把痛苦变成一种力量
杨佳娴:今天很高兴可以跟两位对谈。
我在读Apyang《我长在打开的树洞》时,觉得整本书带我们去感受一个返乡部落青年怎样重新成为自己,做一个太鲁阁族人,也做一个坚强而快乐的同志。当然,我所谓的坚强与快乐,并不是说只有正面而没有其他面向,但我觉得Apyang是很有力量的一个人。
树洞是这本书的重要意象,我们既可以说它是宝物的储藏地点,也是吐出河流的洞穴,当然也像是身体里面的激情通道。全书最后一篇文章,我最喜欢的几句:河水懂得吞噬,河水不会排除,一种包容的、流动的意象,我觉得非常美丽,而且可以代表Apyang这本书的核心精神。
琴峰的《独舞》,从台湾到日本,在痛苦的成长中摸索「女人爱女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是一场跨越幅度满大的追寻。当赵纪惠和小雪在雪梨重逢,把一切事情说开,小雪说纪惠其实是坚强到了逞强的地步,然后纪惠脑中就浮现黑衣女子独自旋转跳舞的画面。
我们可以说,这其实是死亡与童女之舞,死亡与诞生之舞。接着,纪惠想着她要活下来,她要继续写。作品的最后,她跨越死亡的闸门,但是我们不希望继续停留在死亡的这一刻。虽然这篇小说的开头是死,结尾似乎也朝向这边走,但是最后跨越了、克服了。
因此,我觉得这两部作品,其实都带给我们新时代性别书写往前看的气象。往前看,并不是说没有痛苦,而是我们怎么样把痛苦变成一种力量。
今天是镜好听夏日耳朵阅读节的第一场,如果你已经读过《我长在打开的树洞》和《独舞》,绝对值得再读一次。如果你还没有读过,这会是你夏日阅读时光的最好选择。今天的活动就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两位,也非常谢谢在线上一直陪伴我们的听众朋友,谢谢大家。 ●(原文于2022-07-10在OPENBOOK官网首度刊载)
➤以文学为认同发声,完整侧记
从语言、性别到族群|在多重弱势中,摸索出赖以为生的奇迹|创造更理想的社会共同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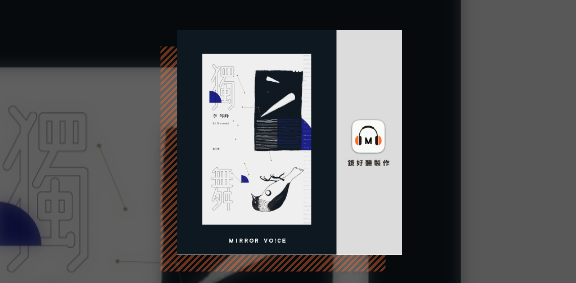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