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答案,是为让更多答案出现」——访《河边的错误》导演魏书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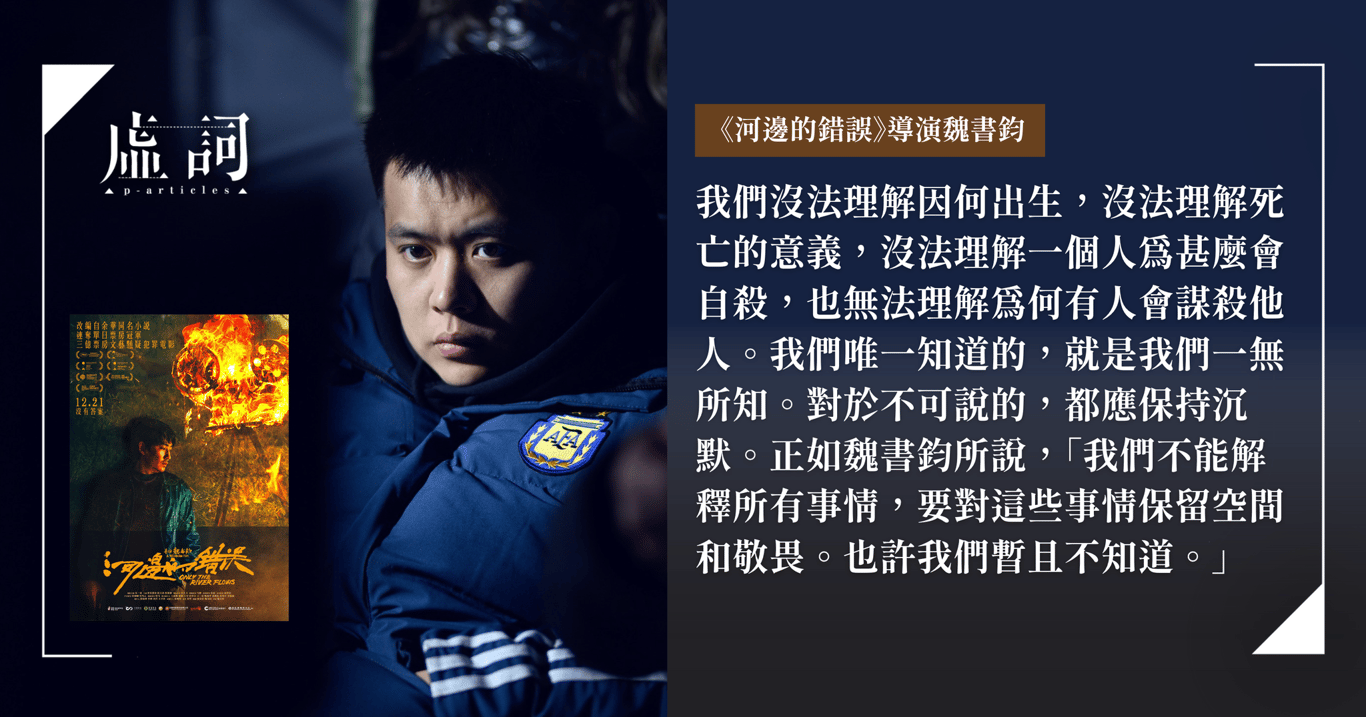
( 原文刊载于虚词・无形)
文|王瀚梁
身为90后的中国导演魏书钧,此前已凭短片《延边少年》、首部长片《野马分鬃》、2021年的作品《永安镇故事集》,三度入围康城影展。而他近日在香港上映,改编自余华同名小说的新作《河边的错误》,同样成功入围去年康城影展「一种关注」单元。作为近年在康城最受瞩目的中国新生代导演,魏书钧的电影总是带着独有的反叛与荒诞感。正如《河边的错误》看似是一部悬疑、推理电影,电影海报上却已说明「没有答案」。观众看毕面面相觑,没有得到答案,反而带着更多问号,而这正是魏书钧所追求的。 「没有答案,是为让更多答案出现。无数的观众,无数种看法,共同构筑了这部电影。让它超越了电影本身,我觉得这个过程很奇妙。」
二十七岁的隔代相遇
《河边的错误》改编自余华在1988年发表的同名小说,故事发生在一个小镇之中,一位老婆婆在河边被谋杀,警察马哲(朱一龙饰)受命调查此案,然而发现案件扑朔迷离,他极力接近真相,渐渐触碰到各种社会禁忌,浮现出各人的埋藏心里的秘密。然后不断再有新的死者出现,令他自己也坠入层层迷雾之中,直到再无法分清梦境与现实,在现实、记忆与幻象交叠之中迷失。 《河边的错误》是余华的代表作之一,魏书钧看到这本小说时,已是小说发表的三十年后,但小说的先锋性仍使他惊叹。 「在一个侦探故事里面,他没有把如何找到凶手,或是凶手的杀人动机作为核心的叙述,虽然写于三十年前,仍然令我觉得十分吸引。」

余华在1987年创作了《河边的错误》时,是二十七岁,而魏书钧在2018年初次看这本小说时,刚好同样是二十七岁,那一年,他刚凭短片《延边少年》初次入围康城影展。魏书钧笑言,他也是后来才知道这个年岁的巧合,觉得这种关系很奇妙,仿似是两个希望在不同艺术类型中探索的年轻人在书中相遇。 「余华老师创作小说时的想法,像冷冻了一样,在小说里面藏了很久,等到三十年后,又被另外一个二十七岁的人,重新发现拿了出来。虽然余华老师是名成利就的大作家,但看小说的时候,我依然能感受到那种年轻的锋利,他对传统叙事的挑战。」
看起来像电影的,都不是电影
远在魏书钧看到《河边的错误》小说之前,中国著名导演张艺谋在90年代初便曾希望将小说改编成电影,并撰写了一个剧本,可是余华看过后,向他推介另一部当时未出版的小说——《活着》,张艺谋凭这部电影享誉国际,而《河边的错误》的改编则因此作罢。 《红衣少女》导演陆小雅以及其他制片公司,也曾购买小说版权,但他们的尝试都不成功。几经波折,小说改编的责任来到魏书钧手上。魏书钧指《河边的错误》难以改编的原因是,这本小说有陷阱。 「小说中有很多细节的描述,很有电影感的画面,很多有过去的人物。可是这些看来很电影的部份,是一个陷阱。当我真正去梳理小说脉络的时候,便发现无法将它改编成一套探案电影。因为探案电影之中最核心的推进要素,是案件如何发生、死者的死因,或是凶手的动机,在小说里全都看不到,我不能按照原来的方法去做。」

在《河边的错误》之前,魏书钧的电影《野马分鬃》、《永安镇故事集》都是他有份编剧的原创剧本。他的上一部电影《永安镇故事集》,更在开镜前把原有剧本推倒重来,与另一位编剧康春雷以七天时间完成新的剧本。而这次他将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剧本,魏书钧表示比起自己创作剧本困难得多,因为文学与电影两者之间有着「艺术语言的不同」。 「我用非常久的时间才发现,最重要是保留小说的案件,保留我第一次观看它的感受,将感受放进电影当中,再传递出来。」他记得读完小说后,脑内响起华格纳的歌剧《崔斯坦与伊索德》(Tristan und Isolde)。这部歌剧被誉为由浪漫乐派带入现代音乐的开山之作,当中的崔斯坦和弦(Tristan chord),为现代音乐开展无限想像。 「它的和弦每一次都不解决到主音上。好像小说中的案情,每一次都在迷雾中前进。这种强烈的感受,我特别想拍出来。」
魏书钧回答问题时,喜欢把自己想像成厨师,把电影比喻成各种食物、食材。他说余华写的小说是一个成熟的苹果,已是完整的,可以品味的。 「把它改编成电影的过程,就像苹果又掉到地上,变成了种子,长出新的树,结出新的果子。它还是这个品种,还有本来的味道,但它的样貌、形态已经不一样了。」
文本只是电影的一小部份
余华在《河边的错误》小说的后记中写道,「事物总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的说法,不同的说法都标榜自己掌握了世界真实。 但真实永远都是处女,所有的理论到头来都只是自鸣得意的手淫。」余华并没有就自己的小说,如何改编成电影提供一个说法。在电影拍摄、剪接、制作过程中,余华都没有参与在内。而魏书钧在《河边的错误》电影中,同样没有为观众提出一个答案,直到电影结束灯光亮起,观众甚至没法分清电影中的真实与幻象,如同角色一样陷入五里迷雾中。正因为没有答案,电影反成为网上热话,观众看毕纷纷在网上讨论,仔细拆解案情,疏理各种脉络与细节。魏书钧再用上他的「大厨」比喻,「我觉得观看电影,不是一个填鸭的过程,不是观众张着嘴巴,我们往里面放点薯条放点芝士,放点番茄酱。观众要主动在电影里面拿到薯条,找到番茄酱,没找到番茄酱的话找到盐也可以。」
但对他而言最深刻的一次观众分享,并非以理性拆解电影案情,而是有一个女生跟他说,这部电影打开了她的嗅觉,在电影当中,她闻到铁锈味,闻到河边的泥草味,闻到主角身上的烟味。 「这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她是用感受去描述电影。很多时候我们喜欢提炼讯息,总结性评论电影,因为这句对白,因为这个故事,因为主角的变化,都是关于文本的。电影的文本非常重要,但对于一个艺术作品来说,文本只是一小部份。文本之外的感受,要跟我们自己经验的结合,这是观看和体会艺术作品,收获更多的方式。」
不要尝试去理解,去感受
魏书钧曾在映后谈上引用《永安镇故事集》中他所写的对白,「这部电影你不要理解,要感受。」有观众说电影打开了她的嗅觉,魏书钧常用味觉作比喻。而作为电影不能忽视的,当然还有视觉和听觉。在《河边的错误》之中,魏书钧选择使用16mm的菲林进行拍摄,便是希望直观上让观众感受到90年代的质感。现今使用菲林拍摄的电影已经不多,以16mm菲林拍摄更是绝无仅有。因为罕有,拍摄与冲洗的成本亦大为增加,但他认为这种菲林的颗粒、蒙胧,甚至镜头边缘的色散,都不是后期数码调色可以营造出来的。因此他选择以菲林去拍摄,建构电影中的时代感。

而电影中的配乐,他采用了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除了因为电影中提及月球的阴暗面,就如电影中的角色各有不为人知的秘密,他更感受到音乐中有一种精密而优雅的气质。精密与优雅,正是他阅读《河边的错误》时的感受。 「有时候我拍完一个镜头,想确定它是不是够精密、够优雅,会坐在监视器旁,放这个音乐配上画面,便知道感觉对不对。音乐像是储存了我对这本小说的感受,在我拍电影的时候释放出来,像一把尺子帮我去校正。」
观看魏书钧的电影,不难发现他对音乐、文学、电影以至哲学的喜爱,例如《河边的错误》主角马哲在关闭的电影院中办案,梦中出现燃烧的放映机。而在电影开首,他引用了存在主义哲学家卡缪在剧作《卡利古拉》中的一句名言:「人理解不了命运,因此我装扮成了命运,我换上了诸神那幅糊涂又高深莫测的面孔。」在《卡利古拉》中,卡缪讲述身为国王的卡利古拉认识到世界的荒谬后,作出疯狂的杀戮与荒唐的行径,游走在疯狂与理性、反抗与毁灭之间。
假使世界原来不像你预期
在卡缪的哲学思想之中,「荒谬」是其中一个最核心的概念。卡缪所说的荒谬,是永恒存在于人与世界之间的冲突,人尝试去理解世界,去改变世界,对世界有所期盼,但世界原来不像你预期,于是人便要面对「荒谬」。魏书钧自言在五六年前,特别着迷看卡缪的书。 「我当时觉得特别意外,一个人能在现实生活中,发现了荒谬,而我们其实也在经历荒谬。」他尤其记得卡缪在小说《异乡人》之中,描述主角莫梭在一个沙滩上开枪杀人,原因只是天气太炎热、太阳太灼眼了。 「如此荒谬的理由,无法满足法官审判的要求,大家很着急替他找各种辩护,解释他的杀人动机。但他写得很清楚,就是因为太阳太耀眼。」这种真实的荒谬,往往难以令人接受,人们总要为无法理解的一切,寻求一个合理的解释,让他们能在「正常」的世界中如常地生活。

在《河边的错误》之中,主角马哲是一个警察,他的职责正是要找出凶手的杀人动机。他尝试以他的理性与经验,追寻各种线索去调查案件,可是每当他接近真相本身,真相却总是超出他能够理解的范围之外,结果他亦深陷其中,成为「荒谬」的一部份,作出疯狂的反抗。电影中的马哲,在残旧的电影院舞台上办案,魏书钧形容,「马哲开始时拼命地按照原本的理解,以理性去发现、调查各种线索,但后来这些线索跟案件好像没有关系,在他没有方向时又有新的线索出现,然后这个没关系的人又死了。案件很现实地,在他面前呈现超出经验范围的事情。他就像是一个舞台剧演员,剧本已经写好了,他只是像扯线木偶般演完这套戏。」当理性无法解释世界,他便陷入了疯狂,再也无法分清现实与幻象。
电影与现实,有谁能分清何者更为荒谬、虚幻?不要尝试理解,或者因为在这世界发生的事情,本身便没有什么我们能够理解,我们没法理解因何出生,没法理解死亡的意义,没法理解一个人为什么会自杀,也无法理解为何有人会谋杀他人。我们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们一无所知。对于不可说的,都应保持沉默。正如魏书钧所说,「我们不能解释所有事情,要对这些事情保留空间和敬畏。也许我们暂且不知道。」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