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学为认同发声I》从语言、性别到族群ft. 杨佳娴、李琴峰、Apyang Imiq(程廷)

主持人:杨佳娴;与谈人:李琴峰、Apyang Imiq(程廷)
文字整理:李怡坤、陈柏均
杨佳娴: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杨佳娴。欢迎参加「夏日耳朵阅读节」的第一场活动。今天的主题是性别,活动非常特别,因为我们是三地连线,除了我个人在台北之外,还有在花莲的程廷Apyang,以及在东京的李琴峰。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三位。我自己过去比较让大家熟悉的身分是创作者,我同时也在大学教书。我会出现在跟性别有关的场合,一方面是因为我最近编了一本跨世代的台湾同志散文选,《刺与浪》;另一方面,我也参与好几年的性别运动,虽然不是街头的冲组,但是我担任台湾的性别运动组织「伴侣盟」的常务理事,非常关心这方面的议题。我是研究文学的,对于同志文学、同志书写也特别感兴趣,今天非常荣幸可以跟两位写作者进行跟性别有关的对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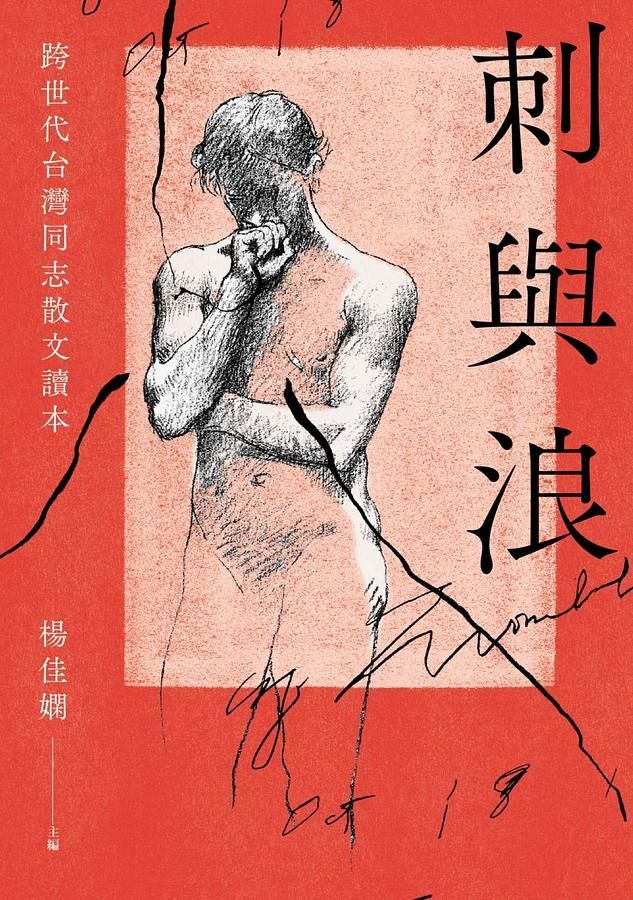
今天来宾之一的李琴峰,是来自台湾的中日双语的写作者、翻译者。她从2013年开始住在日本,在日本已经获得好几个文学奖,相信关心文学的朋友都非常清楚。其中几本作品目前在台湾都已经出版,比如各位可以在镜好听听到朗读版本的《独舞》,以及《倒数五秒月牙》、《北极星洒落之夜》、《彼岸花盛开之岛》。因为琴峰精通中日两种语言,她也翻译了东山彰良的作品,还有可能现场很多人都读过的,李屏瑶的《向光植物》。
另外一位来宾程廷Apyang,他是太鲁阁族人,现在住在花莲支亚干部落,毕业于台大城乡所。大家如果查博客来的作者简介,其实非常有趣,因为他参与非常多社区发展和部落事务。我看到Apyang的个人简介,非常想问「部落简易自来水委员会总干事」这个职位通常是做什么事情?他目前出版了一本散文集,叫做《我长在打开的树洞》,写到部落跟性别方面的经验,写得非常有趣,又打开我们对于这些议题的想像视野。
李琴峰:大家好,我是李琴峰,我现在住在东京。因为疫情的关系以及种种因素,没有办法到台湾跟大家见面。我的视讯背景是虚拟背景,这是2016年我到雪梨参加同志骄傲活动拍的照片,刚好因为6月是全球同志骄傲月,所以就放这个背景,请大家多多指教。
杨佳娴:谢谢琴峰。相信如果线上朋友有读过《独舞》的话,应该也会记得里面有雪梨的相关段落。
➤部落简易自来水委员会总干事,到底要做些什么?
Apyang:大家好,我的名字叫Apyang,我现在住在花莲万荣乡的支亚干部落,很高兴可以参与这个活动,希望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尽量提出来。
杨佳娴:可以问一下「部落简易自来水委员会总干事」这个工作的内容吗?我觉得超酷的。
Apyang:因为我们部落里面,很多地方是在山区嘛,一般的自来水公司不会牵水上去,不会帮我们处理水的问题。所以我们部落有管理水的委员会,每3年都要选一次主任委员等等。刚回来部落的时候,大家想说你会打电脑,就去当总干事了,就是处理行政、公文、做纪录、做报表等等。
杨佳娴:我觉得这个经验还满有意思的,很少看到文学创作者的简历上面,会出现这样的工作。
今天的对谈,首先希望把重点放在两位创作的语言、文字的面向。因为琴峰的母语其实是中文,但是她在日本主要是用日语来创作。如果看过Apyang的书,会知道他是汉语跟族语交互使用。

琴峰,我们知道你第一部出版的《独舞》原来是用日文写作。你曾经创作过中文的作品吗?在什么契机下,你决定要用另外一种语言来写作?我觉得满有趣的是,为什么一开始就想用外语写作、进入外语的文坛,而不是母语的文坛?在文学创作的使用上,中文与日文两者的语感有没有关键性的差异?
➤用日文书写,起因竟是投稿回台湾邮资太贵? !
李琴峰:我大概从国二的时候开始尝试写作,写一些可能不怎么像样的小说、散文。那时候当然还不会日文,英文也写不出来,所以也只能用自己的母语,也就是中文写。所以在我创作的习作过程,基本上都是用中文,主要都是写短篇小说、短篇散文。
在台湾也没写出什么太了不起的成绩。后来因为念研究所到日本来,当时我的日文已经有一定的程度,研究所念的是日语教育,已经不是学日文,而是学如何教日文。再加上生活周遭都是日文,去上课、写报告、写论文,全部都是用日文。我在日本看到很多来自台湾的留学生,大家都喜欢聚在一起,我比较不会这样,我会尽量融入日本的社会,可能参加当地的活动,然后认识日本朋友。国籍对我来讲不是太大的隔阂,自然融入当地生活,生活里面很自然地都是日文。
阅读的部分,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2011年日币真的涨得非常贵,在台湾要买日文书非常不容易,非常贵。我是穷学生,买不起。到日本之后,就比较能够拿到日文书来阅读,比如日文小说等等。渐渐累积阅读的经历之后,对日文小说的写法或者说腔调,渐渐有一些掌握。即使如此,我还是不觉得自己有办法用日文写作。在念研究所阶段,虽然我会用日文写论文、写报告,但是要写小说还是太困难了。
到底为什么会开始用日文写?其实真的是偶然。比较现实的问题是,假如我在日本,然后还用中文去写、投稿台湾的文学奖,这样邮资太贵了。
开始用日文写真的是偶然。 2016年我开始在日本的公司上班,当一个上班族。那时候是4月,日本开学的时候,也是樱花盛开的季节。某天早上,我在前往公司的电车里面,那是所谓的满员电车,人很挤的那一种,我看到外面樱花开得非常漂亮,然后自己搭乘满员电车,就想说,我以后都要这样过生活吗?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一个单词浮现出来,就是「死ぬ」,这是日文的死亡。
记得我大概从青春期吧,10几岁的时候,一直有种淡淡的,日文叫「希死念虑」(きしねんりょ),中文叫「自杀愿望」之类的,觉得好像活着也没什么意义。我心中一直都有一种关于死亡的念头,刚好就在2016年4月那个时间点,用日文的形式,从心里浮现出来。
学过日文的朋友可能会知道,「死ぬ」是一个动词,是满特殊的动词,在现代日文的所有动词里,只有这个词是以ぬ结尾,其实这是满意外的一个巧合。那天就不断地胡思乱想,想说这个好像可以变成一篇小说的开头,因为一开始这个词汇是用日文的形式浮现,我就想说不如用日文写,写出来了就是《独舞》。因为第一篇就是用日文写的,拿去投日本的文学奖,很幸运得了一个小奖,然后就出道,之后满自然就一直用日文写。
➤Kari,太鲁阁族语「聊天」,有时候已可以翻「咖喱」(才不是
杨佳娴:谢谢琴峰的分享。确实大家如果手边有《独舞》的话,可以翻开第一页,第一个字就是「死」。
用外语写作的作家,比如哈金,他讲过,因为他在美国用英语写作,这不是他最熟悉的语言,因此他会倾向用更简明、简洁的句式来写,反而会造成一种比较特殊的、不一样的文体。这部分也许等一下还有时间的话,琴峰也可以再稍微回应一下。
我们先请Apyang来谈一谈,学习族语对于你在文学创作的帮助是什么?加入族语,跟全部都用汉语或中文来写,有什么不同的效果跟意义?
Apyang:我会在创作里面加入族语,其实有几个想法。以前我在念原住民前辈的文学作品的时候,当时罗马拼音还没有那么盛行,他们一定得把族语翻成汉字,让一般人去阅读。可是有些族语翻成汉字真的很奇怪,变成我在创作上的一个困扰。比方说我的名字Apyang,翻成中文就满奇怪的。
再来,其实族语翻译在文学上有很多弹性,因为我不是在编太鲁阁族语字典,在两个语言上的转换,有很多我觉得很好玩的文字游戏。比方我的作品里面有讲,田里的工寮叫做Biyi ,我就直接翻译成「彼忆」。或者我们讲劳动或田里的工作叫Qmpah ,我觉得它有满可以对应的字,我用汉字的「耕」,刚好有一起去工作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们有个话叫Kari ,是语言、聊天的意思。我有篇散文是在讲养鸡的时候,我跟鸡寮里火鸡的故事。因为很多聊天的情境是在吃东西的时候,我直接把它翻译成中文的「咖喱」,会变得非常有趣。
有些字如果硬翻,或是把它音译成汉字,是满诡异的事情。再加上刚刚讲的,因为我自己是创作者,具有把两种语言进行转换的空间,我自己在玩文字的时候也觉得很有意思,可以传达我的一些想法,有些纯粹是我觉得文字上很好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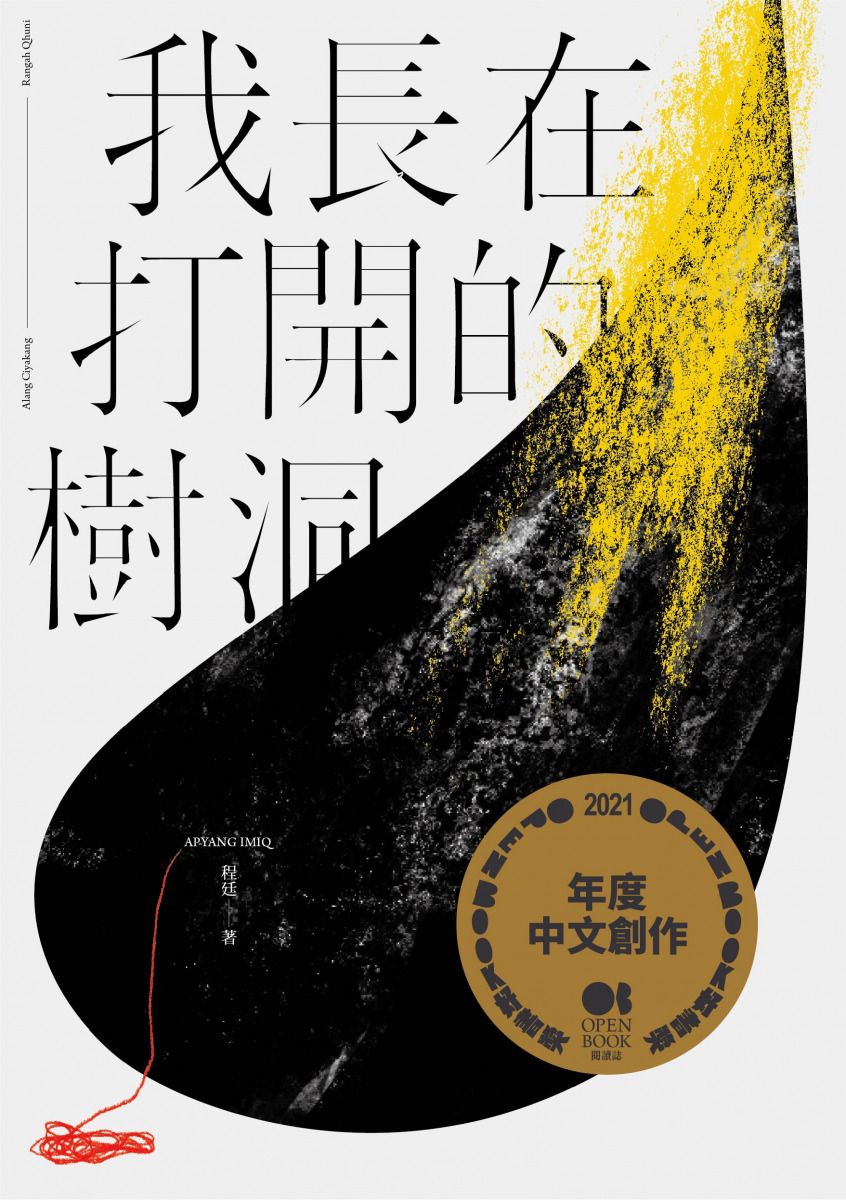
《我长在打开的树洞》是我的第一篇创作集。其实现在部落里,不见得大家会全族语或者全汉语沟通。很多老人家可能族语讲得不错,但华语讲得不像年轻人这么好,所以跟我们讲话的时候都会穿插族语。语言穿插的情况是我们很日常的状态,我在散文里满想要呈现支亚干部落的日常对话情境,所以会有很多族语穿插在汉字里面。虽然整体来讲,这本书还是以华语为主的创作,但我很希望可以呈现太鲁阁语在里面。
➤发明新族语描绘现代事物?
杨佳娴:谢谢Apyang的分享。确实,我们读这个作品,可以发现创作者虽然有意把一些族语单词跟华语混杂,但同时又做了一些带有诗意的翻译。它其实是太鲁阁族人的日常,平常讲话就这样。
这让我进一步好奇,在太鲁阁族语里面,对于现代的事物并不会发明新的词去描述,而是直接用华语来讲吗?
Apyang:对,有满多情况会是这样,或者是用日语。
杨佳娴、李琴峰:有什么例子吗?
Apyang:比如电影。有时候也会借用闽南语。
杨佳娴:所以现在在你们族里,年纪很大的老人家可能还是会讲点日文?
Apyang:会喔,他们日语很好。
杨佳娴:我觉得很有趣。我想到1961年张爱玲来过一次台湾,她觉得台北很无聊,一直要去花莲。她留下来的游记里面说,她遇到的原住民(当然她不是用原住民这个词,她当时会用「山地」这个词),全部都是讲日文,日文好得惊人,显然对她而言是很惊讶的事情。
我们再回到琴峰,因为你自己是外国人写日文,你也会采取某一些语言策略,甚至产生跟其他日语作家不太一样的文体吗?
➤表音文字的强大与表意文字的黏稠
李琴峰:老实说,关于文体,每个作家都各有不同,所以我也不大能够说,我跟所谓以日文为母语的作家不同。我觉得每个人都不同,所以也没必要特别去区分你的母语是不是日文。
不过想提的是,中文跟日文是完全不一样的语言,在语言学上的分类也不一样。虽然可能有千年以上的交流,但真的完全不一样。当我学会日文并开始以日文创作之后,我感受很深的是,表音文字真是太强大了。汉字虽然有些是形声字,有表达声音的一些要素,但基本上还是表意文字。表意文字在书写上有它的效果,但同时也有局限,比方说有些你想传达的声音,就是没有字可以表现,这些中文就写不出来。
日文也用汉字,但是日文同时又有假名(平假名、片假名),是表音文字,当你想写出某些效果、表达某些声音,就可以用表音文字表达。又或者,在写对白的时候,每个人讲话的方式基本上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腔调也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可能发音比较好,有些可能声音拉得比较长,有些人可能讲话比较快之类的,这样的对话腔调的不同,有时候很难单用表意文字去表达。在这个面向上,其实日文的表达功能是满强大的。
像刚刚Apyang说,有些族语不知道怎么用中文的汉字去表达,我觉得是有共通的,你怎么写都觉得很卡。因为中文的汉字是每个字都有份量,不像日文的假名,一个字就是一个音,也没有特定的意思,感觉就比较轻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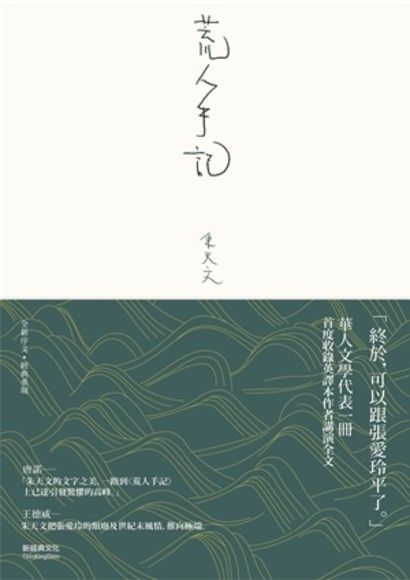
当然中文的汉字也有它的好处。因为每个汉字都有意思,都有重量,所以可以创造出其他语言表现不出来的效果,比方说一种黏稠性,或者是一种文字的密度。我觉得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荒人手记》,文体真的非常稠密。 《荒人手记》有日文版,对照之后会发现文字多了一倍。中文的密度非常高,把它翻译成日文,密度必然会被稀释。因为日文必须要有假名,不能全部都用汉字,日文就比较难写出这样高密度的文体。
杨佳娴:谢谢。这个牵涉满广的,比如说有一些情绪或声音,怎样简单而传神的表达?或者有些新的词汇,怎样在自己的语言把它写定?这其实好像都得经过一定程度的时间与过程。
我刚刚立刻想到的是,大约100年前,当时有个诗人,就是大家熟悉的胡适,他想写我们今天叫做「野餐」、Picnic的词,但这个词的翻译当时还没有固定,诗人不知道该怎么写,最后只好音译,而且把它放在七言的长诗,放在古诗体里面,写成「辟克匿克来江边」。一开始看,根本不知「辟克匿克」是什么,你要念出声音,才可能联想到是英文的那个词。我们在100年后来读,会有一种特殊的趣味。 ●(原文于2022-07-10于OPENBOOK官网首度刊载)
➤以文学为认同发声,完整侧记
从语言、性别到族群|在多重弱势中,摸索出赖以为生的奇迹|创造更理想的社会共同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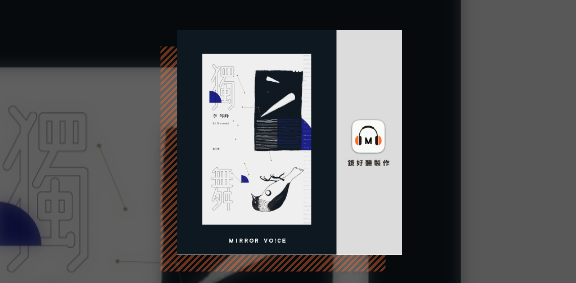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