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3 | 思緒在哪裡落腳?人類學對於哲學課題的審閱(上)
人類學與哲學之間有著可以無限追溯的淵源,回顧20 世紀以來的學科歷史,人類學家的思考倚重於哲學的概念與知識傳統,而哲學則試圖在異域的民族誌中尋求西方認識論的啟發與替代。然而,壁壘森嚴的學科分工想像讓學者們固守領地,人類學家滿足於負責“特殊”的民族志寫作,哲學家引述經驗只是為了充實“普遍”的分析,二者一面曖昧相望,一面彼此拒絕。
回顧哲學和人類學交織的歷史是有必要的。人類學一詞早在古希臘哲學已經出現,在哲學受到其他思維範式衝擊時,人類學的立場和哲學人類學為人立法的傾向每每是康德、舍勒、海德格爾等哲學大家背水或仰攻的陣地。不同於思辨追尋“人是什麼”的哲學和神學人類學思辨,近代以來的人類學實踐強調通過田野,接觸異質的文化,在實踐中進行理解、思考和深描。這套語法雖然在20世紀才系統化為人類學的學科,卻早已在歷史的流轉中與哲學家相遇,是盧梭遇上的加勒比人,康德在哥尼斯堡讀盡的旅行日記,黑格爾在海地革命裡發現的時代精神。而在現代人類學理論奠基的年代,經典的人類學現象、概念與理論也總刺激那個時代最卓越的哲學心靈不斷回應和思考。哲學家列維-布留爾(Lévy-Bruhl)基於世界範圍內民族志材料提出了互滲思維的理論;太平洋的馬納(Mana)概念對20世紀初歐洲現代社會反思啟蒙的持續共振;維特根斯坦多次閱讀《金枝》,從中獲取的靈感啟發了他“語言遊戲”等一系列後期思想;莫斯的禮物理論不但是最俱生命力的人類學辯題,也激發著德里達、馬里翁(Jean-Luc Marion)等哲學家的不斷回應。
對讀哲學與人類學不是去攀附兩本學科的親緣性,更需要的是超越西方中心和學院中心,與在地的行動者一起構築經驗和理論的連續,揭示和理解被壓抑和忽視的聲音和思考,學習田野裡湧現出的倫理和反思:正如作為記者的福柯在伊朗革命時所體察的“靈性革命”,烏鴉族印第安勇士教給喬納森·里爾(Jonathan Lear)的“基進希望”,正如亞馬遜部落啟發威維洛思·德·卡斯特羅(Viveiros de Castro)對本體論的再聚焦,埃及穆斯林女性的讀經運動中馬木德(Saba Mahmood)開始了對現代社會自由和倫理觀念的反思。無論是豐富對人的境況的學習還是重構對世界的理解,人類學與哲學都需要從典籍轉向實踐,並在對實踐的共同聚焦中重啟交流、對話。
哲學人類學是結繩志與哲學社共同策劃的系列專題。我們試圖通過共同譯、校的方式來開啟一種共學共讀的模式。這是一場去中心化的合作,目的並不是要辯論人類學與哲學的高下之分,而是試圖與文章的作者們共同探討,人類學與哲學在當代如何以新的方式彼此聯結、彼此貢獻。
本篇為哈佛大學神學院教授,存在主義人類學家,邁克爾·傑克遜(Michael D. Jackson)的文章,原文副標題為An Anthropological Critique of the Project of Philosophy。本文將critique譯為審閱,與其說是以人類學的視角批判哲學,倒不如說是將人類學的視角帶入康德批判哲學意義上為思考立法的努力中,看看人類學和民族志可以為哲學做些什麼。
思緒在哪落腳、交匯?思想在哪凝聚、誕生?這些過程只發生在學者的書齋之中和課堂上嗎?它們的脈絡必須只能通過梳理歷史和譜系才能敘述嗎?它們可不可以就發生在我們的周遭世界之中—現在、這裡?傑克遜以反思哲學課題為出發點,引用了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的積極生活(vita activa)以及現象學內生活世界(lifeworld)和人生哲學(lebensphilosophie)等概念,來提議民族志研究方式能夠實現思緒本身的政治性和事件性,也就是說它是人類主體間,公共和私人領域間權力關係的表現。文章大體分為四個部分。首先,傑克遜認為思緒落腳點是一個社會空間,在其中我們在人際關係中摸索前行,所以思緒的萌芽到思想的形成是一個主體間交流與分享的過程。有了這個背景鋪墊之後,傑克遜主張民族志研究方式的有效性,因為它的假定就是通過沉浸於他人的生活世界中,我們懸置了自身先驗的理解,從而使得我們能夠站在一個第三視角來判斷他人同時自身。第三部分,傑克遜把民族志研究方式從一個方法論提升到了一個思維模式—“旅行想像”。不僅是肉體更多是思想上,傑克遜主張一種持續的“流亡”狀態,也就是不避世但是總是站在“別處”思考和判斷“這裡”的情況。最後,回歸到最初的問題—思緒在哪落腳? —傑克遜認為哲學應該捨棄這一假設,即思想以及從它引申出的一系列價值標準擁有啟迪和引領人類社會進程的特權。他主張一個實用主義的態度,即思緒本身和人類切身利益密不可分,所以應該以它們為這問題重重的世界所真正謀求的福祉為衡量它們的標準。
原文作者 / Michael Jackso
原文標題 / Where Thought Belongs: An Anthropological Critique of the Project of Philosophy
譯者 / Michael
校對/ 星原、子皓
摘要
阿多諾(Adorno)、阿倫特(Arendt)、巴迪歐(Badiou)、德里達(Derrida)、海德格爾(Heidegger)和羅蒂(Rorty)都曾主張重新設想哲學,但是他們中沒有一個人選擇從歷史和系譜構成的過去轉向人類學式的當下。考慮到思想不可能逃離思想者眼下的當務之急,這篇文章通過生活世界(lifeworld)和生命哲學(lebensphilosophie)等現象學概念來探究思想產生和發展的社會空間(social spaces)。漢娜·阿倫特認為思考紮根於積極生活(vita activa)而非是沉思生活(vita contemplativa)。由此為起點,本文提議民族志的研究方式能夠有力地實現她對於思想的理解——思想無法擺脫政治和事件,這即是人類主體之間、公共與私人領域之間權力關係的表現。
關鍵詞:
阿倫特,民族志研究方式,事件,判斷,人生哲學,極限狀況,積極生活
正文
“哲學已經無法再被人們應用到掌控生活的技能上了。與此同時,不管是常規的邏輯學和科學理論還是所謂的本質高於所有存在形式,因為與所有明確內容的割離,哲學已經在面臨實際的社會問題時宣布破產了。”
阿多諾(1998: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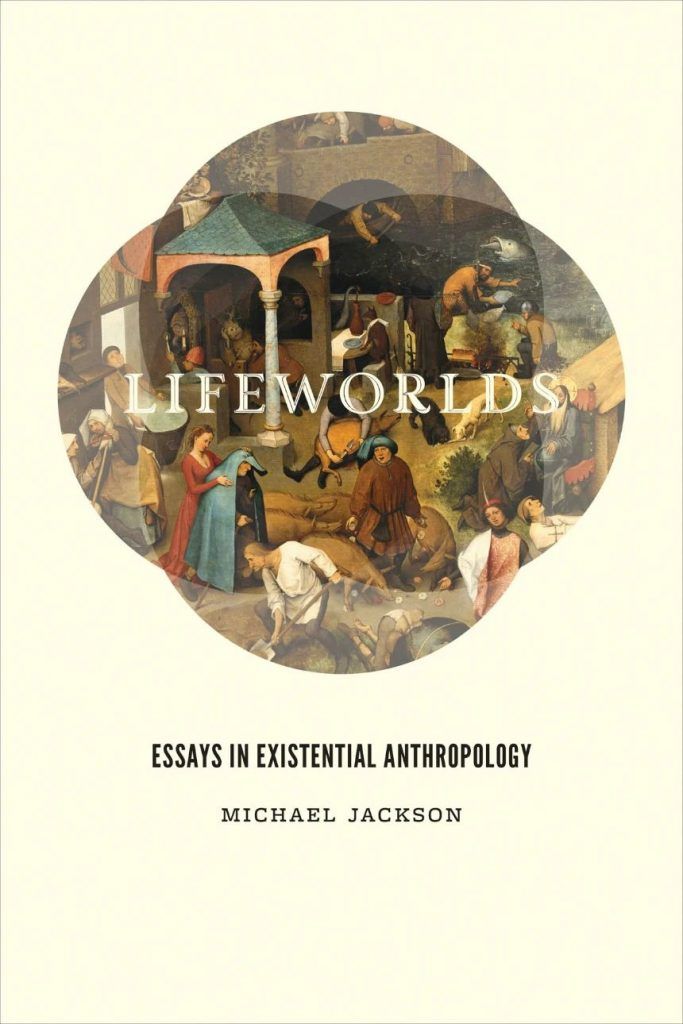
說到哲學的“終結”和“破產”【1】, 或許是(哲學家在)坦白自己對於習慣性借助古希臘先賢製造輿論的一絲惱怒和乏力。這些先賢無法回話,我們亦不可能進行面對面的對話和交流,而且他們的社會狀況和我們的大相徑庭。這其實也是承認在哲學自身傳統內部重塑哲學的難度。這也是為什麼阿蘭·巴迪歐會說:作為方法論的第一原則,我們必須忘記哲學的歷史,並且將思維從“譜系律”(genealogical imperative)中搶救回來。 (2008: 4-5)但是我們應該走向何處?巴迪歐引用了聖保羅皈依的經歷並將其作為一個超越猶太法律傳統和古希臘智慧傳統的關鍵節點,但諷刺的是,巴迪歐的起始點依然是歷史而非當下的事件,而且他依然執著於真理問題,即使具體事件的獨特真理顛覆了哲學概念“真理”的普世性。羅蒂則主張振興和重塑哲學的方式可以是重新思考啟迪性的學者,像是威廉·詹姆斯和約翰·杜威。對於他們來說,“真理”是我們後續添加給對於我們有正面效益的事件的標籤。但是我們還是有一系列未解答的問題,包括什麼類型的事件需要哲學,在我們周圍世界何處最需要我們的思考,和我們如何理解思想的本質。我覺得巴迪歐是對的,他鼓勵我們關注具體事件並且提醒我們這個事件可能“沒有傳遞任何律法,掌控形式,無論是來自於智者還是先知。”(2008: 42) 但是為什麼不把我們當下的事件當作起始點呢?與其關注歷史事件和人物,為什麼不從此地此刻開始我們的思考,將我們自身沉浸在他人的平凡瑣事中,從他人的煩惱中找到我們的思緒,並且用他們選擇的措辭來進行對話?簡言之,為什麼不從人類學中汲取歷史主義(historicism)一度提供的那種靈感,通過走向遠方而不是回看歷史,將人類對話以柏拉圖無法想像的方式拓寬擴大? (Rorty, 1979: 391)哲學家們通常會尋求一種能夠使思想擺脫日常生活中肉體、感官和現世糾葛的立場(阿多諾將這樣的設想貶為“妄想”(1998: 7)), 然而人類學家們堅持認為思緒總是和世俗利益、物質考量、文化成見和日常情況密不可分【2】。據此,把沉思生活和積極生活分離不單單是錯誤的,這也是烏托邦化的,也就是說這在哪裡都不可能實現。這樣的錯覺類似於異化,是在產品和生產過程、文字和語境、資本和勞動被分離後隨之產生的結果。
哲學充其量就如浮雕——用人造而且局部的圖像來捕捉充滿事件並且多維的生命過程;往壞了說,哲學是在模仿自我繁衍並且自我循環的奧羅波諾(Ouroboros )銜尾蛇的形象【3】。而現象學、存在主義、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和實用主義的核心則是在方法論上發問思緒如何落腳在人類的生活世界內而不是從中被提煉出來,和思緒如何啟始於主體間生活的過程而不是凝結於其最終產物——(產物包括)文化和符號形式、法律和道德教條、宗教經典、出土文物。這就好比人文學科避開了自然科學對於實驗對象、物種、標本、典例的執著,(因為)這些對象同樣也是脫離背景並且籠統。實際上,任何關於人的真理絕不可能被話語主體完全囊括,即使我們通常用這些陳述話語來識別和分析自我和他人,例如男性或是女性,年老或是年幼,工薪階級或是中產階級,受未受教育,現代或前現代。為了全面地認識到存在本質的事件性(eventfulness),就要意識到在任何人類互動的過程中,浮現的經驗總是會溢出並且超越最初對於互動及其之後思考的框定和預設。即使經驗(experience)和知識型(episteme)之間的不確定關係可能不是那麼顯而易見,但是這種不確定性在關鍵事件(critical events)和極限狀況(limit situations)中顯得異常明顯,因為個人經歷無法被既有的可參考的知識體系、思維模式和語言架構所解釋。就是基於這個原因,我在尋求一套語彙來捕捉存在本身的這種不確定性、不穩定性、事件性、不協調性、進退兩難、自相矛盾和詩性(poetics)。
人的境況(THE HUMAN CONDITION)
為了反駁思緒能夠超脫於一個思想者眼下的當務之急和存在的迫切性(existential imperatives)的這一觀點,我們訴諸於現象學中生活世界的觀點來定義“社會”空間,在這其中思緒發芽、浮現、然後發生。或許沒有人能把存在哲學(existenzphilosphie)或生命哲學(lebensphilosophie)解釋得像漢娜·阿倫特那樣好,所以在接下來的文章中我會結合相關背景總結她對於學術課題的理解,考慮其中的不足,然後強調民族志的研究方式能夠有力地實現她對於思緒本身政治性的理解——在一個共同的世界裡我們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中摸索前行而不是站在一個至高點發號施令。

1975年12月4號星期四,在完成她的著作《心智生活》 (The Life of the Mind)第二部分之後的第五天,漢娜·阿倫特為了一次晚餐在她位於紐約市河濱大道的公寓中接待了她兩位老朋友——薩羅·拜倫(Salo Baron)和珍妮特·拜倫(Jeanette Baron)。晚餐過後,三位好友回到了起居室。正當他們在邊喝咖啡邊閒聊的過程中,漢娜·阿倫特突然遭遇一次咳嗽引起的痙攣,然後跌坐在她的扶手椅上失去了意識。一場突如其來的心髒病瞬間奪去了她的生命。
在接下來的三年內,瑪麗·麥卡錫(Mary McCarthy)傾注了她的身心去編輯和發表她朋友未能完成的著作。瑪麗·麥卡錫經常工作到深夜甚至持續到睡夢中,她說這樣為愛付出勞動是為了延續“一場想像中的對話……甚至接近辯論,就如在真實生活中一般。” 瑪麗·麥卡錫在她編者後序中解釋說阿倫特的書被構想成三個部分——思考(thinking)、意願(willing)和判斷(judging)。而對於漢娜·阿倫特,判斷的能力是“心智中三個部分的樞紐”, 因為判斷讓我們明白了我們和這個被共同棲息的世界之間的聯繫;正是因為判斷,學術活動變得接地氣並且睿智。當她去世時,漢娜·阿倫特只完成了關於她著作的第三也是最後一部分的一些零星的筆記。這些筆記在她的書桌上被發現了。嵌入她打字機的白紙上標題醒目,“判斷”,還有兩句卷首引語,卻很遺憾地無法透露出更多她的構思。所以,“心智的人生” 就好比是一個沒有結局的故事。然而,相關結論在阿倫特1970秋季為紐約社會研究新學院(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準備的關於康德的政治哲學的講座上已經有所預演了。
對於漢娜·阿倫特來說,判斷的前提是我們歸屬於一個被人們共同分享的世界。不同於純粹理性,判斷不存在於我和我自身的柏拉圖式無聲對話,而是誕生於他人的存在並且參與其中。相比其他思考模式,判斷尤其是置身於社會並且斡旋於其中,和我們生活中的事件相關同時也在故事中顯現。然而,判斷的能力需要保持和“主體個人的處境” 一定的距離,即使這種距離不是通過那種脫離世俗和情感的科學理性來實現的——(科學理性)假定了“一些至高點……高於(世俗的)混戰。”一直忠誠於自身本質上的社會性,判斷通過想像式錯位(imaginative displacement)來尋求距離——從他人的角度來重新思考自身的世界【4】。阿倫特的興趣是思想如何超越思想者本身,算是致敬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的“極限狀況”(grenzsituationen)的概念,意思就是哲學不再追求一個有界限同時內部協調的對整體的概念,轉而開始解決一些困擾和動搖哲學本身的情況。然而,她盡力指出,當一個人採納他人的立場時所做出的實踐以及經驗方面的效仿,既不會侵蝕此人自身本質,也不代表掌握他人實際的所思所想。所以,自身和自身習慣性立場之間保持一定距離,並不等於用他人的成見來取代自己的成見,也不代表失去主動性。不同於傳統經驗主義那樣倡導讓觀察者變成一張白紙來記錄對觀察對象的印象,判斷需求主動地參與和對話——讓自己的思緒被他人的所影響。據此,判斷意味著一個無法被納入自我或是他人立場的第三種立場:一個介於主體之間被共同分享的觀點。
“唯獨想像能使我們從合適的角度看清事物,使我們足夠強壯以至於毫無偏見地在遠處審視和我們息息相關的事物,使我們足夠樂意填補眼前的鴻溝、把遙不可及的事物帶入我們的生命。這種遠離已有的事物和靠近他人的事物是交流式理解的一部分,因為對於理解本身來說,直觀經驗會蒙蔽雙眼,單純理論也只是人為的障礙。這種想像實即為理解,沒有了它,我們無法和世界建立關係。這是我們唯一的指南針。只有在我們理解的範圍內,我們才是同時代的人。”
但是,這樣對判斷的設想難道不非常的理想化嗎?不顧雙方之間觀點和品味的天差地別,單單只通過橫向的錯位來置身於他人的出發點,並且不依靠身份上的共鳴或是抽象的概念?阿倫特的觀點難道不是忽略了在公共場合那些積怨已久的分歧嗎?正是這些分歧在極力反對“交流透明化”並讓比爾·裡汀斯(Bill Readings)所稱的“去指涉化”(dereferentialization)幾乎無法發生。一個“去情感的社群”(dissensual community)——不帶身份地思考,不受條條框框的束縛——或許學者可能成功達成,但是當分歧情況不關學術爭論和啟迪而是生死攸關,這(去情感的社群)還可能存在嗎?比如說,維納·達斯感人地描述了一個女子名叫尚蒂,她的丈夫和三個兒子在1984年英德拉·甘地被刺之後的德里騷亂中遇難,她僥倖劫後餘生。我們需要直面的是尚蒂慘痛的經歷和她所處的男權主導的社群之間存在無法調和的意識形態衝突。當這個社群開始羞辱尚蒂並拿她作為失去子嗣和背叛“男權世界”的替罪羊時,她看到的是“只有女性關係的人生已經……不值得繼續” ,所以選擇了自殺。
所以,我的第二個論點就是:判斷,以阿倫特對於這個詞的理解,總是存在於實踐中的,意思就是這更加考驗一個人的情感和社交能力而不是他/她的智識敏銳性。無論我們的意圖有多真摯,現實卻是每當我們竭盡全力去接納任何激進的差異,定義我們自我認知的習慣和秉性都會面臨危機。正是如此,如不是情況所迫,人們不太可能去從他人的立場審視自身的世界觀。在現實中,理解通常不來自哲學式抉擇和散漫的好奇心,而來自於強制地錯位和危機,後者能把人硬生生地從自己習慣性思維和行為模式中拖拽出來。
理解他人需要的不僅僅是在自身和他人出發點之間做智識上的轉換;它還涉及周遭劇變、身心俱疲和道德迷失。這也是為何經受磨難是理解過程中無法避免的伴隨情況——喪失了對自身特定世界觀能解釋萬物的幻想,並且痛苦地在一個陌生人的言行舉止中看到了自身的謬誤。正是因為這樣的險境和象徵性死亡是逾越自身世界的邊界所需付出的代價,我們便自滿地認為所處世界是這個世界的全部,並且拒絕像了解自身世界那樣了解他人的世界。同理,因為在世界上的某些地方,開放(openness,這裡同時指主動和被動地接受新的事物)已經成為了無法避免的存在形式,在那我們能找到最有說服力的例子來證明人們在拓寬他們的理解的過程中如何忍受痛苦和奮力掙扎。我稱此處為移民式想像(migrant imagination)。正是在此處,而不是在歐洲的沙龍和講座中,我們或許可以認識並且接受這個些許痛苦的真相:人類世界構成了我們共同分享的土地和遺產,但是這個世界不是一個和諧的個體而是一個充斥著偶然、分歧和爭鬥的場所。
在促使自身接受這個處境的過程中,講故事(storytelling)是關鍵,因為講故事提供給我們的不只是一個改變原本無法改變的事物的方式,而且是一個重新想像(世界)的方式。請思考以下的民族志的例子。理查德·威爾克(Richard Wilk)在他關於伯里茲的本土和跨國身份認同之間相互作用的研究中說,在伯里茲內持續增長的國外產品、電視節目、遊客、貨幣、商人、音樂、語言、毒品、犯罪團伙、文化品味和想法所帶來的一個結果之一便是當地主動創造的本土文化,包括飲食文化。威爾克主張,這個過程演化成了一個戲劇性的敘事。在這個敘事中,本土和國外,自我和他人被二元對立,同時伯里茲人獲得了一種掌控“全球文明”而不是任其擺佈的感覺。威爾克指出,“這個故事的寓意是,資本主義的科技架構,包括電視和其他媒體,被用在了非常本土的而且反霸權的目的上。”
第二個例子,選自於安德魯·拉塔斯(Andrew Lattas)關於在巴布亞新幾內亞的船貨崇拜(cargo cults)的研究,也闡明了講故事能促使在想像空間內本土和國際場域的重組。船貨崇拜的敘事是基於一個傳統的信仰,遠行去不熟悉的地方——尤其是死者之地(the land of the dead)——是拓寬一個人理解範圍和增強能力的先行條件。當歐洲人登陸巴布亞新幾內亞的時候,他們改變了當地的文化,經濟和政治狀況,白人便被納入了這個帶來力量的他性/他人(otherness)的世界。船貨崇拜的故事接納了這個新的焦點,但同時繼續注重於“衝破壁壘”從而逾越邊界以至於窺探並進入“他人秘密區域”。的確,皮欽詞“stori”意思是“一個關於秘密和遺失能力的故事” 。但是這樣的想像式策略不應該被貶低為一種共情魔法。即使當地的比喻提及接納另一膚色或是進入另個人的肉體(就好比我們說的“設身處地”【5】),這種船貨崇拜很少會陷入移情和模仿的被動模式,而是主動地嘗試新的想像和人際策略以提供人們真實的能力來控制世界。

船貨崇拜的敘事是非常考慮實際的,而漢娜·阿倫特對於判斷的理念則是基於啟蒙運動的人文主義目的。理解是為了理解本身。判斷是“代表性的”(representative),這不是因為一個人採納、主張或者甚至和他人觀點產生共鳴,也不是因為一個人逐漸擁有了可以反應外界現實的抽象概念,而僅僅是因為有助於個人判斷的理解是多元化的而不是一元化的,是主體間的而不是主觀的。恰恰是她堅持說現實不存在於自身或是他人內,而是在這兩者間——在一個“關係網”中,自身和他人如愛恨糾葛般與生俱來地糾纏在一起【6】,阿倫特無意地呼應了非西方思想中社群主義的邏輯。
民族志判斷(ETHNOGRAPHIC JUDGMENT)
對於阿倫特來說,判斷顯然是在我們與他人的關係中萌芽而不是來自某些第一原則。因為判斷位於主體間的邂逅,所以它不能對於人生窘境聲稱任何最終決議。判斷不是站在一個排斥他人信仰和習俗並以自我或種族為中心的立場上,然後對於分歧做出一個不加反思的、先驗的、說教式的譴責。相反,判斷是一種認真處理多元和模凌兩可的人類真實生活的方式,不把他人看作非人,而是身處其他狀況中的我們自己——即使這些“他人”可能包括了這個世界中的阿道夫·艾希曼【7】們。我們審判艾希曼不是因為他的所作所為是非人的並且邪惡的,而是因為他代表了一種人類未加深思的庸常的存在形式——既膚淺又自私——在這形式下,一個人預設了對他人的了解,卻未曾通過站在他人的位置上對這些了解進行檢驗(他人所處位置可能是自願和也可能是被迫的【8】)。以此類推,沒有判斷應該試圖將對話蓋棺定論,因為每一個判斷本身,反過來說,也在被他人進行判斷著【9】。
“這些觀點並不是在鼓吹道德相對論;它們只是在呼籲一些能夠使判斷建立在理解上的策略——也就是說,對自身和他人之間關係做深思熟慮。在這個意義上,理解就如講故事一樣,起始於'具體情況和手頭上的事物',而不是一概而論的歸納。”
比如說,在西方有人公開反對“野蠻”地對女性生殖器進行手術,並且聲稱陰蒂切除術是父權社會的邪惡或是伊斯蘭中世紀主義。我們可以說,這些西方人最讓人頭疼的不是他們觀點本質上的“謬誤”,而是在他們拒絕從其他立場理解這一現象,同時口是心非地引用“人權”來合理化一個他們從來就沒有冒著換位思考的風險去嘗試的立場。也就是說,“普世”不應該是把自身本土的或個例的觀點投射到世界各地,也不是一個號稱脫離世俗羈絆的觀點;然而,“普世”這詞最恰當的意思是在實際和社會層面持續參與他人生活世界的過程中所獲得的更完善的理解。正是如此,漢娜·阿倫特的判斷理論是奠定在一個和民族志研究的假定相類似的基礎之上:通過沉浸於他人的生活世界中,我們故意把自身的預設置於危機之中。這不代表我們必然會停止譴責和寬恕;而是說價值判斷來自——而不是先於——我們的調查。調查恰恰就是基於對我們習慣性思維的懸置。單憑智力不行,必須從習以為常的慣俗中抽離出來。
在她關於卡爾·雅斯貝爾斯的文章中,漢娜·阿倫特觀察到:“我所想的任何事物都和已被思索過的所有事物保持著密切交流。”這裡所暗指的是,啟迪在理想狀態下是一個生命和死亡的對話形式——在我們自身和過去之間。至於哪一段過去或許對我們最有益,阿倫特和雅斯貝爾斯在這裡的看法是一致的:這(過去)不應該僅僅是注重於基督降臨、拯救和最終審判的基督教的過去,而應該被定義為公元前800到公元後200年之間那段世界各地哲學思想相繼誕生的關鍵時期——中國的孔子和老子,印度的奧義書(the Upanishads)和佛陀,波斯的查拉圖斯特拉(Zarathustra),巴勒斯坦的先知們,荷馬和古希臘的哲學家們以及悲劇作家們。
作為一個民族志研究者,我質疑這個遙遠的“世界歷史軸心”提供給我們的只有可接觸的世界觀,而沒有可停留的生活世界。如果一個人進行真正的換位思考,這不僅僅簡單是用他人的思維模式思考;一個人必須不惜任何代價在接近之後直接體驗他人的人生和處境。應阿倫特的話,拓寬個人的理解需要學會讓“個人的想像去遠行”。然而,人類學,而不是歷史,或許可以為“想像的旅行”提供最具挑戰性的地貌。雖然和先賢們進行“對話”無疑是有益的,但是學習在我們當今世界中離我們貌似最遙遠也最陌生的活著的人們的語言也是非常重要的,同時通過在他們之間逗留發現阿倫特和雅斯貝爾斯所珍視的真理的奧義——真理不是對他人抽象的理解而是和他人直接的交流【10】。
所以,對於這個阿倫特也沒能從中完全掙脫的理想主義,民族志研究提供了解藥,因為民族志研究方式所需的不僅僅是在想像層面參與他人的生活,而是切身實際地投入到型塑了他人世界觀的各種儀式和生產生活中。這不單單是對於民族志研究者語言和概念能力的挑戰,也是對於他/她身心資源儲備的挑戰。民族志研究迫使心智的人生從沉思轉變到實踐。轉述福柯的話,迫使自己和他人一起並按照他人的條件生存是一種“邊界體驗”(limit-experience),通過將個人的身份和理智置於風險之中來探索不同於已知世界的其他可能性。正因如此,人類學式理解從來不簡單地僅限於認知,而且或許沒有其他任何一個學科像田野調查這樣融合了冷靜觀察和設身處地的痛苦經驗。
因為民族志研究包含了一個人和他/她正在進行了解的事物之間直接、親密而且實際的溝通,民族志式的判斷擯棄了自然科學的主體-客體二分,並且用主體間的理解形式加以取代。這意味著一個否定的辯證(negative dialectic)。因為當民族志學者同時被自身先入為主的觀點和他人對自身的理解影響時,任何主體間對話的結果絕不是所有觀點簡單相加,而是某種偶然隨性的收場,但留給自身和他人一個初步且開放式的觀點,並尋求未來繼續的對話和溝通。
儘管人類學的基礎方法——參與觀察——看似允許內外部觀點同時存在,人類學卻總是游離地穿梭於所謂的客觀和主觀立場之間。在一個極端,有無數的方法論和修辭方面的革新試圖把人類學改造為一種自然科學,也就是觀察者通過獨立於被觀察物來識別奠定和解釋社會現實的規則和常態。在另一個極端,在“走向本地人”(going native)這一變質主題上有許多不同的浪漫化嘗試,也就是觀察者在(模仿)他人中喪失了自我。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ity)的模式克服了這兩個極端錯誤的對立,因為客體和主體不再是被理解成任何先驗的、實質的或是不變的現實,而是看作成現象學式的詞彙,而我們用這些詞彙來標註經驗的瞬間和型態並反映在人與人、人與物或人與信仰之間交流過程中各種已實現的或預設的可能性(Jackson, 1998)。如果民族志研究方式被首先理解為我們已經掌握的普通社交技能(比如說,友善和互惠的待人之道)而不是一些我們需要習得的艱澀技術,那麼我們會更加傾向於接受主體性和客體性不能被“客觀地”和脫離語境地定義,因為它們的價值總是由個人在特定社會場合中的相對位置和個人特殊的經歷所決定。
漢娜·阿倫特完全懂得這一客體和主體位置的相對性。她曾問,在沒有明確個人對於極權主義下不公和恐怖的憤慨之前,一個人能如何書寫極權主義?如果一個人要對這種現象保持”客觀,”這種現像下的生活體驗和後果是關鍵的,而不是扭曲現實的。以納粹主義為例,她記錄:“冷靜地描述集中營不是保持'客觀',而是在寬恕它。”然後她說:“我認為描述集中營為人間地獄是更加'客觀',因為這樣的描述比純粹的社會學或是心理學式陳述更加接近它們的本質” (Arendt, 1953: 79)【11】。在另一個例子中,她討論了在一個非常富裕國家中的極度貧困。
“人類對這種情況的自然反應是憤怒和憤慨,因為這樣的情況違反了人的尊嚴。如果我在描述這些情況時不允許我自己的憤慨干預其中,我把這特定情況從人類社會的背景中剝離出來並且把它的本質去除了……因為只要極度貧困是在人類之間發生的,它的一個特質就是喚起憤慨。”(1953: 78)
(待續)
註釋:
【1】原註:參考The End of Philosophy and The Task of Thinking (Heidegger, 1969).
【2】原註:參考杜威反對將知識和入世實踐行動相分離的觀點:“如果我們不覺得(產生)知識是一個旁觀者的行為,而是一個參與者置身於自然和社會的環境中(的行為),這樣的話知識真正的對象便落腳在有目的行動的結果中。” John Dewey, The Quest for Certainty: A Study of the Relation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New York: Perigee, 1980), 196.
【3】譯者註:奧羅波諾源自於古埃及圖像,描繪了一條咬著自己尾巴的蛇。它是一個古老的符號,象徵了自我繁衍,生死交替等等。
【4】原註:此處阿倫特的想法和阿多諾的有異曲同工之妙。對於阿多諾,思考需求廢除自我。他觀察到,“自由思想超越自我”, “已被深思熟慮過的事物需要在其他地點被其他人重新審視”。參考Theodor W. Adorno, “Resignation,” Telos 35 (1978): 168. 社會現象學家阿爾弗雷德·舒茨的類似觀點也值得提起(或許因為兩種思路都源於康德), 對於他來說,“觀點間的互惠性”和“立場間的交替性”定義了主體間的戰略要點和“常識性”思維。參考Alfred Schutz, On Phenomenology and Social Relations: Selected Writings ed. Helmut R. Wagner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70), 183-4.
【5】譯者註:中文裡類似的話可以是換位思考。
【6】原註:我和蒙田觀點類似——這是一種把比喻放在中心的理解形式,因為一個人穿梭於自我和他人的觀點之間,總是利用一些共享的概念和修辭來比較個人和他人的經歷。而結果則是一個利用比喻的不精準性(比較的事物不可能一模一樣)造成的大致(經歷)重合來開啟對話、打破僵局、拉近彼此的距離。
【7】譯者註:納粹德國奧地利黨衛軍少校,二戰時對猶太人大屠殺的主要負責和組織者之一。
【8】原註:寫於1945年一月份,漢娜·阿倫特已經預想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1963)中她會獲得的結論。 “希姆萊的組織大體上不依賴於狂熱分子、先天殺人犯或是虐待狂;它完全依賴於忠於工作家庭的男人們的循規蹈矩。”參考Hannah Arendt, The Jew as Pariah: Jewish Identity and Politics in the Modern Age, ed. and intro. by Ron H. Feldman (New York: Grove Press, 1978), 232. 詹姆斯·鮑德溫(James Baldwin)在寫關於猶太人大屠殺時也說了非常類似的話:“一個文明不是被邪惡的人摧毀的;文明的崩塌不需要人變得邪惡,只需要人變得沒有骨氣。” 參考James Baldwin, The Fire Next Time (New York: Dell, 1970), 77.
【9】譯者註:參考Readings, The University in Ruins, 134.
【10】原註:人類學本身的歷史也恰恰是一個從歷史式研究到非歷史式理解的過程。所以,19世紀晚期的人類學家,如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弗雷澤(James George Frazer)、摩根(Lewis Henry Morgan)和庫朗日(Numa Denis Fustel de Coulanges)著重於對跨文化古蹟和文化進化論的研究,而馬林諾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的民族志研究方式則建立起了現代田野研究的傳統,並把歷史放進了括號中,之後克勞德·列維-斯特勞斯(Claude Lévi-Strauss)的結構學也做了類似的貢獻。
【11】參考George Devereux, From Anxiety to Method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The Hague: Mouton, 1967). 德佛洛在人類科學中“主體性”作為“客體性”重要組成部分的討論,和阿多諾對於任何抽象“主體”都需要“相互”研究的討論——包括對於“主體性”的描述等等。 Adorno, Critical Models, 245-58.
作者
邁克爾·傑克遜(Annemarie Mol)是哈佛大學神學院的世界宗教傑出教授,在塞拉利昂和澳大利亞原住民社群做過大量民族志研究,關注人類在特定社會情境下的倫理處境。他也是一位詩人。
譯者
Michael,一個關注巴基斯坦邊境的學生
獨立網站:tyingknots.net
微信公眾號ID:tying_knots
【傾情推薦】訂閱Newsletter
成為小結的微信好友:tyingknots2020
我們來信、投稿與合作的聯繫地址是:tyingknots2020@gmail.com

最新文章(持續更新)
125. 斯皮瓦克:庶民以死發聲
126. 一周年特別活動| 結繩故事繪
127. 社科畫集
128. 哲學人類學| 馬克思的「歐洲中心主義」:後殖民研究與馬克思學(下)
129. 你的奧運隊可能是個幻象
130. 弗格森| 今日無產者政治:歷史類比中的危險與機遇(上)
131. 弗格森| 今日無產者政治:歷史類比中的危險與機遇(下)
132. 溯源| 前人類學時代的博厄斯與“地理學”
133. 思緒在哪裡落腳?人類學對於哲學課題的審閱(上)
喜歡我的作品嗎?別忘了給予支持與讚賞,讓我知道在創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續這份熱忱!

- 來自作者
- 相關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