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戴鎖銬的娜拉:徐州八孩女子與農村父權敘事
徐州豐縣女子在寒風中帶著鎖銬木然站立的場景令人痛心。距離魯迅發表那篇著名的《娜拉走後怎樣》已臨近百年,距離中國人民“站起來”的宣言已經70年有餘,佔人口一半的女性的社會處境近年愈發獲得公共關注,因而這一事件的後續發展尤其讓人憤怒。 (截止22日在Matters發稿,江蘇省政府成立的調查組並無回音,網傳地方政府反而進一步在“維穩”方面開展工作。)
本文意圖探討並批判一種並不主流但值得回應的話語,即一種站在農村男性的立場上為其作辯護的話語。這種話語宣稱,像董某那樣的農村底層男性是社會發展不均衡下的弱勢群體,因而買女為“妻”(以及後續的罪行)是不得已而為之的,甚至暗示這是一種對農村的補償。它不主流是因為拐賣事件基本能夠達成公眾的道德共識,但它又值得回應,是因為這種貶低女性的論調屢次在農村與女性議題相交的場域裡復現(如農村高彩禮問題)。
我們完全應該看到,城鄉二元結構很重要,城市化發展主義所導致的政治經濟不平等、特別是對農村的剝削也很重要,它們在過去幾十年中形塑了人口流動及其性別分佈的基本形態。然而,這一前提這恰恰是批判性地理解農村各種問題(包括性別問題)的起點,而非辯護詞。
在我們所看到的拐賣所牽連的社會關係中,為男權秩序服務的人販子和農村男性買家仍然能夠以極端的方式(包括連騙帶拐)壓迫和剝削女性,再藉助地方宗族勢力、婚姻制度的合法化功能、家庭作為“家務事”的私人領域話語、對基層政權的影響力等限製女性的自由和自主。在這裡,男權秩序不僅僅是傳統/文化的,也要把當下更複雜的經濟性安排(如財產分配)包括進來。另外,與階級、民族/族群相關的不平等及其交叉性(intersection,意指社會系統的多個等級化維度在個體處境的交匯)也從中浮現(參見: “小花梅”背後的怒江傈僳族女人:被討走?被拐賣?還是自主婚姻遷移?| 訪談)。
如果拐賣女性是對農村利益的“無奈”補償,那麼這個農村指的究竟是誰的農村?所謂“農村利益”的主體,不包括女性、只有男性嗎?亦或者,是假借農村男性名義、卻從這種野蠻關係(如果按照它的同情者所說,即對所謂農村底層男性群體的收買)獲得好處的既得利益群體?
這種將女性排除出去的農村(男性/父權)敘事,甚至也為一些怯談“性別”的農村研究專家所共享。但如此一來,這一男性化的“農村”視角最多只能作用於當下城鄉結構性關係的維繫,實際上無法改變農村男性在這一政治經濟系統下的困境,乃至助長城市話語對農村的道德化優勢(後者被簡單地建構為落後、愚昧、未開化的前現代空間,農村男性則被認為是與暴力、犯罪同義的非人危險形象) 。另一方面,它也將破壞或消解國家的現代性承諾,後者曾是中國近現代政治與社會解放運動的基本關切與核心理想。
“至於女子,除受上述三種權力的支配以外,還受男子的支配(夫權)。這四種權力——政權、族權、神權、夫權,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製度,是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的繩索。” ——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本文於2月13日首發於微信公眾號“蜉蝣型幽靈”。)
往期評論:
東方主義,多重“邊緣”與審美解放:回顧陳漫事件及其爭議(2021-12-22)
歡迎訂閱Matters賬號與微信公眾號「蜉蝣型幽靈」
ID:gh_ff416309254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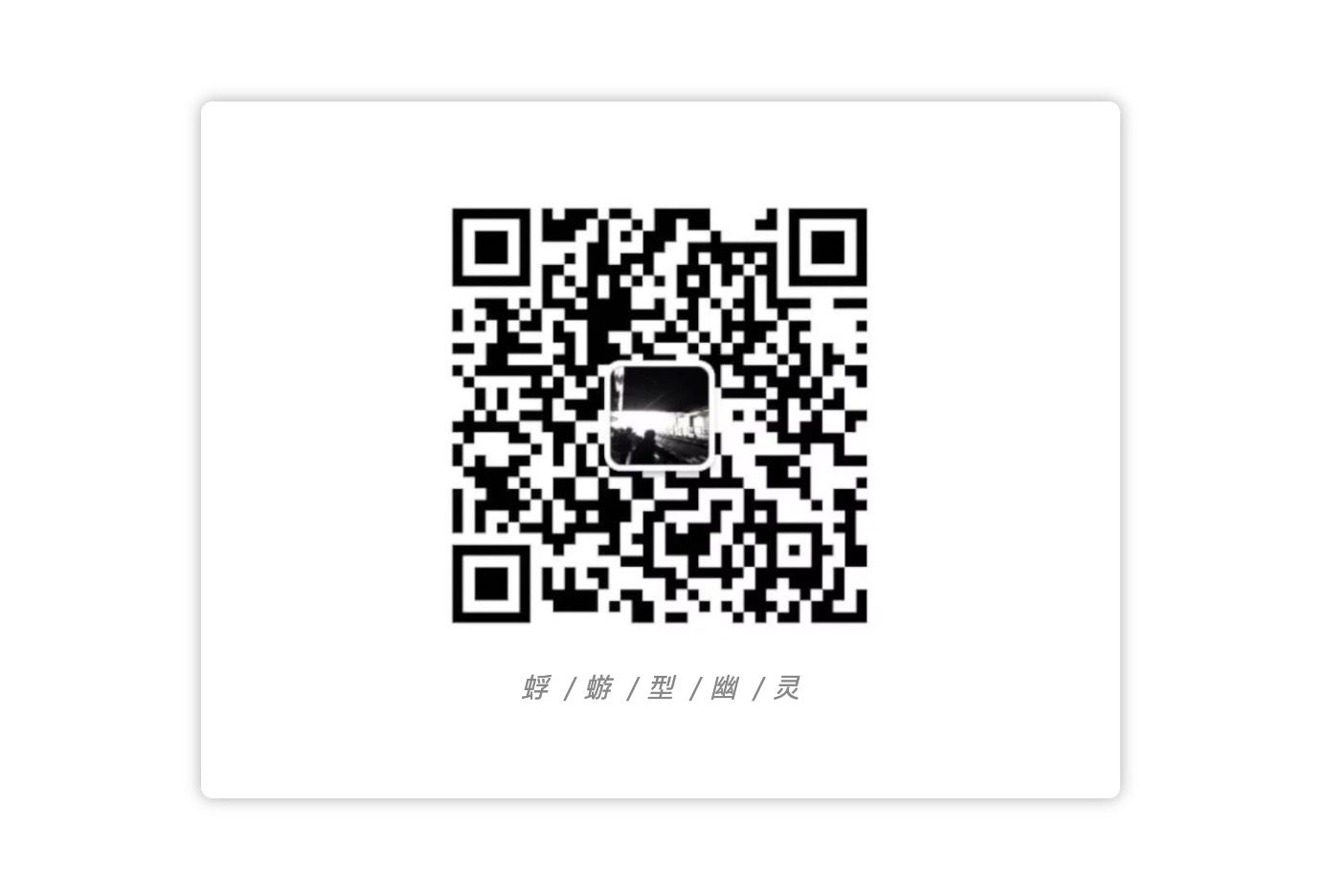
喜歡我的作品嗎?別忘了給予支持與讚賞,讓我知道在創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續這份熱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