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自在柏林帶兩娃,我和孩子收穫了一種被寬容的成長
一種被寬容的成長
在空曠的院子裡,一個小男孩背著藍色的書包,慢慢地走向紅磚牆的教學大樓。四周無人,教室樓安安靜靜,都已經在上課了。他用正常的腳步走,完全不著急,儘管上一秒鐘媽媽才在校門口對他說過,「跑步,快點上教室」。可是,他沒有,即使淅淅瀝瀝的雨淋下來了,他都不會快走兩步。

那個男孩就是我的兒子辰辰。
站在側門的背後,透過玻璃看著那個小小的背影,我輕輕嘆了口氣。學校大門在8:30準時關閉,遲到了就要走側門。大多數的日子,他會在最後幾分鐘跨進大門,最後一分鐘走進教室。
一年級的時光快結束了,我都沒等到班主任責備他遲到的郵件。第一學期時,我向班主任寫信,請他發出一些警告,讓孩子有點時間觀念,早上出門前少哭一點。過了幾天,我旁敲側問辰辰,老師是否批評過你,讓你不要遲到?
“沒有,他只是說以後早點來。”
“他生氣了嗎?罵你了嗎?”
“沒有,他笑著和我說話。”
我心裡嘆了口氣,“怎麼辦呢?”
我女兒四年級的時候,她的班主任很嚴格,寫過幾封電子郵件提醒我,督促孩子準時上學。這些郵件最終會轉化為對家長的壓力。那一年,我在柏林工業大學讀碩士,一個星期有兩三天都要搭火車去上學,每天8小時的課程。隔天早上還要把女兒準時送到學校,把兒子帶到幼稚園。
兩個孩子的年齡相距四歲,行動快慢不同,時間卻被綁在一起。於是,一家人難得有一個good morning。早上的交響曲永遠是媽媽的罵罵咧咧,弟弟的哭鬧和姊姊不耐煩的催促。騎車在路上,我像老唱片一樣播放,“騎快點,走直線,別繞路”,同時,內心裡還要和懊悔做鬥爭。為什麼昨晚不早點讓孩子上床睡覺?為什麼鬧鐘響了不及時叫醒?慈母總是想讓孩子多睡幾分鐘,可是往往讓每個人都狼狽不堪,為什麼不糾錯?如果早點叫醒,弟弟不至於出門的時候才拉屎。可是,拉屎是否可以進行時間管理?我匆匆忙忙,腦子裡一團漿糊,任由拉屎成為一個有哲學意義的問題。

直到有一天,送完孩子們上學,我暈倒在學校對面的馬路上,朋友叫了救護車,這個哲學問題終於有了初步答案。兩年前的某個週一,摯友張進在北京做手術,明明是個不需要擔心,擔心也沒用的手術,我卻哭了一個週末。週日夜裡,估算他進手術室的時間,沒睡好。等到清晨5點多,得到他平安出來的消息,才迷迷糊糊入睡。一個多小時候後,起床鬧鐘就響了。不吃不喝地就忙著做早餐,準備零食盒,把孩子們叫起床,急急忙忙騎車。
送完了,像打完一場仗。

我和另一個媽媽站在馬路邊閒聊,喘口氣。她個子很高,來自匈牙利。我仰著脖子,抬頭看著她說話。過了一會兒,嘴唇突然感覺不到血液,暈眩的感覺像雲朵,輕飄飄的。我慌了,朋友也慌了,問,「我該怎麼辦?」我擔心得了什麼怪病,想到保險公司會付賬,就對她說,「你幫忙叫救護車吧」。
我站不穩了。脫了牛仔衣鋪在人行道上,躺下來,看到了初夏淡藍色的天空,好高好遠。我始終沒暈倒,只是很虛弱。大概不到5分鐘,救護車來了,停在學校門口,兒子幼稚園的窗前。他一定不知道,在教室裡玩遊戲的時候,他的媽媽正被兩個穿著橘色制服的,高大健碩的人抬上了救護車。車廂裡設備齊全,兩個專業的人陪著我,心裡一下子踏實,情不自禁地脫口而出,“如果能嫁個醫生多好啊!”
他們聽懵了,笑著問,“為什麼?”
“作為他們的家人,會很安全”,他們笑了笑,好像不認同。在醫院待了6個小時,做了很多檢查,沒發現問題。下午,獨自離開了醫院。第一時間就去某個地方補了很飽的一餐。那次叫了救護車以後,我有了對飢餓的恐懼。
每個早晨我都先把自己餵飽才送孩子去上學,就算遲到,也絕不動搖。書包裡還隨時準備著麵包和巧克力,害怕再次暈倒,即使巧克力在書包裡融化得一塌糊塗。有了很長的一段時間,我害怕獨自出門,害怕獨自去超市,害怕獨自坐地鐵,害怕去人流擁擠的火車站,害怕來來往往的陌生人,害怕暈倒的時候沒有熟悉的人在身邊。總而言之,害怕一切。我困擾自己的恐懼,也深知那是對恐懼的恐懼。需要艱難地,努力擺脫那次經歷帶來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看見媽媽的需求”,是自救的第一步。做了媽媽10年,才開始學會不忽略自己,給孩子倒牛奶時,記得了給自己也倒一杯;當孩子們哭鬧的時候,學會把他們請出我的臥室,從衝突中抽離;無論多麼放心不下孩子,週五晚上都要去上跳舞課,保守自己的嗜好。

另外,也學習接受“做一個不完美的媽媽”,原諒自己,也分清孩子和媽媽的責任邊界。我會忘記閱讀學校的通知郵件;會忘記孩子們春遊的準備清單;還會對孩子吼丟東西;很多年來我都沒給兒子睡前讀書,讓女兒代勞等等。在母職裡,自責是我最大的敵人,我學習減少樹敵。
然後,是求救,看心理醫生,勇於向朋友求助。
人類學家項飆教授提出了「把自己當作方法」的方法論。去年9月,我去馬普所採訪他。我問他,能否把他的方法論理解為「把生活當成一場試驗」 ?他認同有這部分的涵義。把自己當作方法,把生活當成一場試驗──這個觀點讓我有思想解放的感覺,像昏暗混沌裡的燭光。在以往的人生經驗裡,是被動地去填充社會角色,不自覺地接受俗見的評判。後來,生活浪潮把我推到了陌生的國家。在陌生的佈景下,嘗試著新的活法,新的思考模式。既然是試驗,就代表結果是未知的。不必再用約定俗成的結果固定人生的角色。
日子瑣碎漫長,一個人在柏林照顧兩娃,生活總是顧此失彼。如果放眼看向鄰居的窗,就會自責,為什麼我的孩子不能在一年級就準時上學?我是不是一個失敗的母親?可是,每個孩子的成長都是一樣的曲線嗎?是否所有的家庭都要服從唯一的社會標準?一個月之前,我決定從自責和羞愧的情緒中解脫出來,主動給兒子的班主任拉頓先生寫了坦白的郵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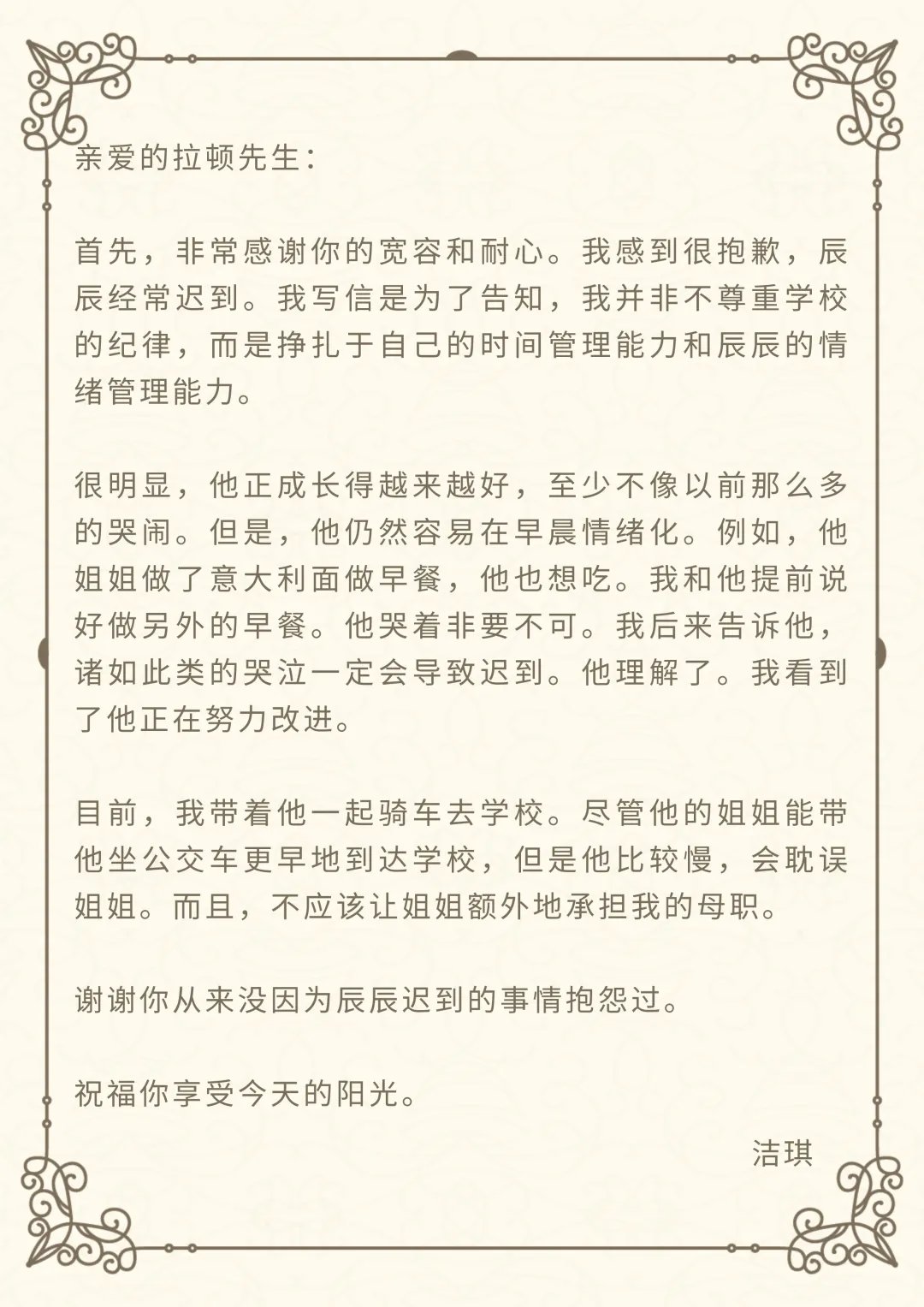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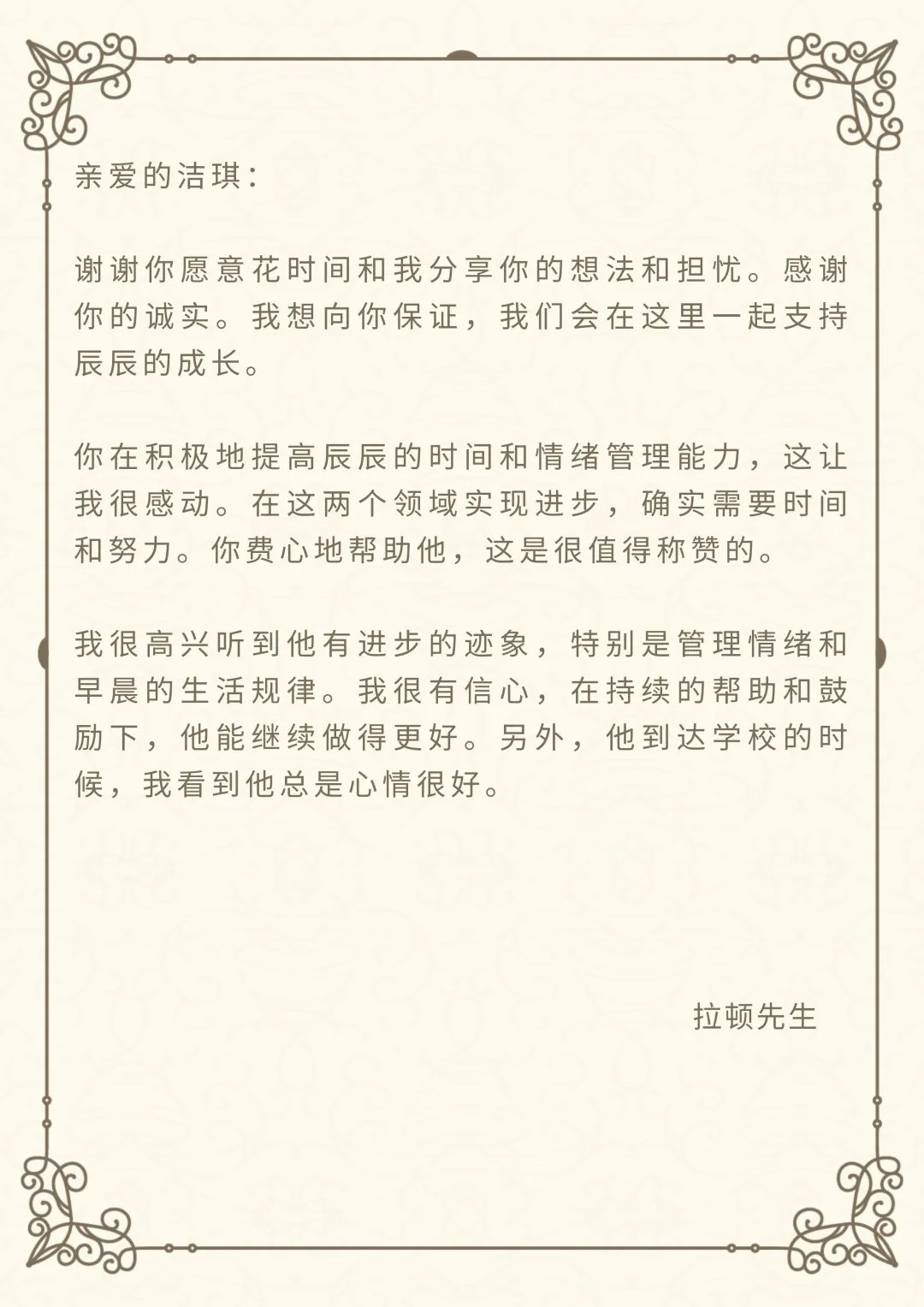
經過了郵件交流,心裡坦然了許多。學校設計了「黃金時間」 ,獎勵本週表現好的孩子。週五放學前,得到黃金時間的孩子可以在教室自由玩耍,不需要站在走廊排隊。黃金時間從10分鐘到30分鐘。辰辰往往得到了30分鐘。
我很驚訝,為什麼他常常遲到,還會有黃金時間,成為被稱讚的孩子?
辰辰說,“我沒遲到,是最後一分鐘到達。因為上課的時候,我是最安靜聽講的學生。另外,我寫數學題目最快。”
昨天,他遲到了15分鐘。我覺得時機到了,就對他說,暑假後就升上二年級了。如果繼續遲到,可能需要復讀一年來訓練時間管理的能力。你希望學校做出這樣的決定嗎?
他說,“不想,朋友們都上二年級,我不想一個人在一年級。”
「以後,你在前面騎車,我跟在後面。你來決定上學的速度,好嗎?”
他同意了。今天早晨,他仍然為早餐不可口哭了,不過很快擦乾眼淚去刷牙。路上再也不看河裡的鴨子,也不抬頭看繁忙的起重機了,飛快地騎車,遠遠地把我甩在後面。
可是,明天會怎麼樣呢?誰也不知道。

如果想讓孩子一一
懂閱讀,愛思考,善溝通
會選擇,負責任
歡迎評論和私訊預約我們的體驗課程吧。
喜歡我的作品嗎?別忘了給予支持與讚賞,讓我知道在創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續這份熱忱!



- 來自作者
- 相關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