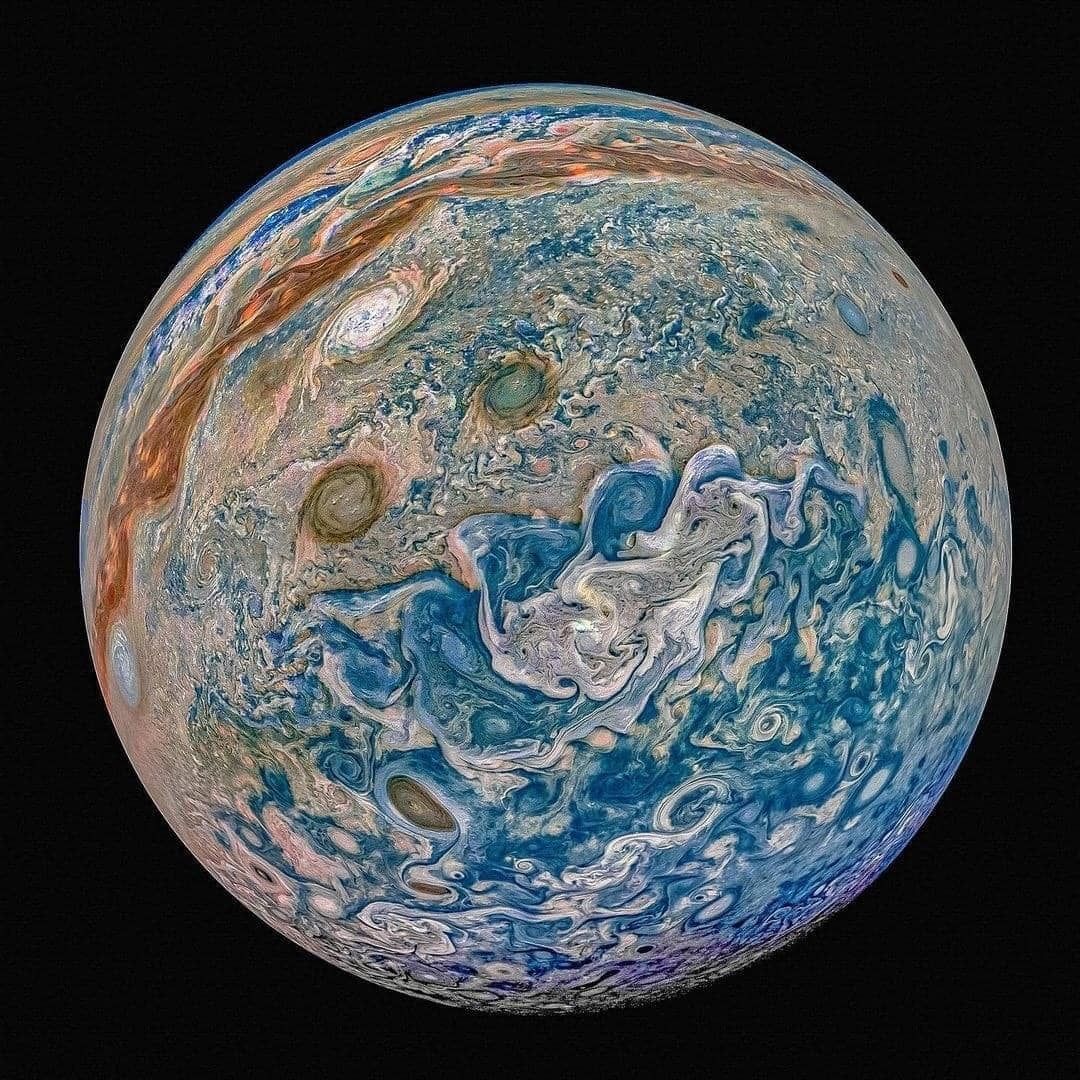个人小写|蚁路
此文写作完成后,投递该年度林荣三文学奖,得一评语曰结尾不符现实,综合其他因素最后未获奖。后转于2018年2月21日《自由时报》副刊登出。
蚂蚁什么都爬。
搬到这之后,家里的蚂蚁换了一种。旧家的蚂蚁起先还不太多,偶尔食物忘了收,或该绑的没绑好,或绑久了橡皮筋弹性疲乏导致门户大开,才会引来蚂蚁搬食。那时的蚂蚁是暗褐色的,姿态不慌不忙,但会咬人。其实不咬大家相安无事,也不会知道有什么食物遭了殃。一咬,等于占地插旗的宣示。一口也罢,两口三口,四五六口,咬到人心浮气躁了,便无法再容异种在地盘上如此嚣张。循路获巢,要嘛灌水,要嘛下药。既然你不把握我罕见的好生之德,我也没必要跟你客气什么。
只是事情从来也没顺利过。杀戒一开,往往不是你想停就停得下来。有时我很疑惑蚂蚁彼此的通报机制。照理说世间万物都该珍惜生命,知道这里有个疯婆子卯起来杀蚁杀到眼红,已经那么多前线将士壮烈牺牲了,不是应该发出警告电波通知楼上楼下行李款款另觅他处吗?显然蚂蚁不做如是想。我杀得愈疯,它们占得愈狂。本来只在开过的食物沿线流窜,后来,阳台上的盆栽废土有了(或许它们向往亲近自然风土),待洗衣物堆里有了(不知为何很常咬破内裤),封装完整的干货罐头也能见到它们的踪迹,在密不透风的包装上着了魔似地环绕,希望找到其门可入,非常坚持。
有一阵子时不时就有蚂蚁飞来落在我身上,我怎么也找不到来源,一度怀疑蚁路延伸到天花板,那些个攀抓力不足的蚂蚁便失手坠落。某天我又莫名被咬了几口,突然福至心灵地盯着一旁摇头卖力吹送的电风扇看了好一会,按掉开关拔了插头将风扇大卸八块,卸到底座,赫然发现蚂蚁们从四面八方搬来尘土毛发,在里头筑了个好生安适的巢,看得我头皮发麻。不知道那些蚂蚁在风扇内扎营是不是为了某种秘密任务进行高空训练,乘风而降时却老控制不住吃荤的口欲,一咬便泄了行迹。
还有一次我顺手拿了挂在床头的毛巾去洗澡,洗完擦身。不擦则矣,一擦全身不对劲,定睛细瞧,手上腿上好几只蚂蚁乱窜,边窜还不忘张口啃皮食肉。我惊慌地旋开大水重新给自己刷洗得更彻底,洗完抓起毛巾扯开一看,巾面上密密麻麻毫无逻辑的蚁群。我又怒又躁,顾不得杀生造业,把整条毛巾扔进热水。望着那一层浮上水面的蚁尸,心想你们何苦逼我至此。
如是我身上常有蚁咬的肿丘,一块一块暗自发红,好似吻痕般羞涩,却痒到足以令活人崩溃。那也像是人蚁之间的征战纪录,以肉体为计分板,一痕得一分,刻画着蚁类的开疆拓土,与人类的节节败退。
童年时我常随母亲返乡,外公外婆在屏东小村种植水果,凤梨芒果荔枝莲雾,一片热带风情。果园里什么没有,蛇虺蚊蚋无一不缺,最怕就一种红头红身的红蚂蚁。只只肥壮,蚁身坚实油亮,一看便知是不好招惹的货色。常常我在果树间穿梭玩耍,一不留神踏上蚁路,只要引来一、两只上身、只要咬上一口,我们的农村假期就随着我火速肿胀的手脚画下句点。那时母亲固定带我在高雄市区升平街内一处皮肤科就医,医师姓吴,候诊一小时,看诊三分钟。每每医师见我胀着一手掌或一脚背步入诊间,便笑笑地:「又被红蚂蚁咬啦?」有时挨上一针,通常开三天药,再加两扁盒白色药膏。肿消下后会浮一个水泡,是蚂蚁的咬口;水泡褪掉(或被我抓破)则会留一个疤。吴医师是我永恒的救星,他那药膏很是神奇,不凉,但擦上便止痒。我总希望他能多给我两盒存用,仿佛那时便预感自己与蚂蚁是一辈子的战争。
有时我不免庆幸自己年纪大了皮肉厚了,或免疫力增强了,或蚂蚁品种不一样了。现在被咬,肿还是肿,痒还是痒,咬口疤也还是照留,但已不至于像童年那样一口换一手(或一脚)。即便如此,去得郊外田间,我依旧不敢掉以轻心。毕竟吴医师与我一南一北,天高皇帝远,万一又被咬了肿成面包人,只怕我撑不到去见他,就先给自己截了肢。
搬到现在这个住处,室友们和我原本都还挺乐的。新环境新气象,虽是上看三十年的旧屋,然格局方正、明亮通风,前几届房客也将房子维持得挺好,不见老态。觑着农历年假期工作空档,我们便欢欢喜喜地住了进来。
欢喜不了几个月,春分刚过,蚁灾便至。先是墙角门边现了一列一列颇有秩序的蚁路,我们几个各自观察了一阵,一时找不到它们有什么特别肆虐的行为。尤其我看这批蚂蚁不是旧家那种暗褐蚁,顶着黑头,摇着掺点黄色的蚁腹,个头更小,不带一丝会咬人的凶残样,便也随它们去。
但事情总是这样的:你想和平共处,对方不见得领情。搬家百废待举,平日各自在工作上忙乱的我们,进驻之后草草安定,也不急着全部拆箱就定位。在这方面,蚂蚁扮演了皇帝不急急死太监的太监角色。时不时我们便会发现还封着的某一箱某一袋爬上了一列蚂蚁,拆开一看,里头肯定有个啥货遭了蚁殃。可能是泡面,可能是冰糖,无论是什么都给蚂蚁啃破一个小孔,辛辛勤勤地把我们的存粮运成它们的。
然而,那些蚂蚁是有点过分了。
原本想说,好吧,就当它们是来提醒我们快些把日常打点好,不要一直将就过着纸箱生活。蚂蚁看上哪箱,我们就整理哪箱,有时还刚好拆到一时遍寻不着的东西,未尝不是某种天启。直到某次,室友苦着一张脸告诉我,她已经好几天晚上,睡到一半被蚂蚁咬醒了。
「而且这种蚂蚁很烦,妳把它们蕊死会好臭!」室友说。
我们讨论了半天,一时还没想到怎么解决,只好暂且搁置。然室友的抱怨像是按到某种开关,那场对话之后,蚂蚁不只上了她的床,跟着爬来我的桌。常常我对着电脑工作,便见蚂蚁呼朋引伴地进入我的视线范围。我桌上零食收得紧,看到蚂蚁入侵我更决心尽量把零食往嘴里塞,一点存货不留。只要蚁群鬼鬼祟祟在我周边探头探脑,我要嘛整理桌子愚公移山,要嘛拍案惊奇制造地震,希望突来的变化能吓乱蚁路,让蚂蚁们知难而退;更希望它们去查询我的杀蚁前科,进而启动通报系统,不要再来烦我。
过不了几天,另一个室友的房间也沦陷了。除了房间,浴室也现了蚁踪,厨房更是重灾区,所有生的熟的咸的甜的干的汤的全的渣的,蚂蚁们无一放过。其见猎心喜的程度让我好奇它们到底是饿了多久,或者食指多么浩繁,得这样千千万万形形色色的吃食才能满足。
这批蚂蚁比旧家的蚂蚁更得寸进尺,丝毫不懂适可而止。你抹去这条蚁路,它们也不费心走远,就在旁边另开一条;咬破一包饼干,还没搬空,硬要再开一包。你以为它们什么都要,岂料它们专挑好货。加工太多的不吃,化合物更看不上眼。阿里山手工黑糖夹链袋没压好开了一小口,它们趁势搬得浩浩荡荡;一盒蛋卷吃掉三根还留两根,我只简单将折起来的袋口夹住,它们连靠近都没兴趣。那天我拿起蛋卷看了一下成分,一堆有的没的,想了想,便往垃圾桶扔。连蚂蚁都不吃,我为什么要。
有好一阵子我对这些蚂蚁探勘的毅力很是佩服。它们热爱寻访各种未知,即便危及生命也在所不惜。当我发现我的马克杯里无论装的是水是茶,有糖无糖,只要搁一阵子不动,再拿起来要喝时,里头都会浮着蚁尸,我的神经便愈来愈靠近临界点。你搬食物也就算了,偶尔爬来我身上咬个一口、我把你弹掉就是了;但我着实不喜欢我在工作空档只是想喝个水,还得因为你死在里面,不得不起身倒掉、清洗、重装一杯。举凡任何打乱工作节奏的事情都必须遭到天谴。
一再重复倒水洗杯,很烦。于是我找来一个深盘装了水,给杯子垫着一盘护城河。水可以隔离味道,隔断去路,却隔绝不了这些蚂蚁雄兵探勘未知的决心。我以为它们用触角点点水面便会知道此路不通,没想到它们竟前仆后继地投身入水,硬是想要知道那湖心之岛藏着什么宝物。到底是什么样的执念啊,这是蚁界的泳渡日月潭吗?就算给你侥幸游上杯岛、探到秘境,你形单影只的又搬得了什么回去?更何况你游过一滩水,探到的,只是另一滩水啊。
我看着深盘水面漂起一只又一只壮志未酬的蚁尸。它们努力划动六肢、却不幸于登陆前灭顶,在精疲力竭的最后一刻,它们会不会懊悔自己选错了路?我又看见几只游过同伴尸体、幸运攀杯的勇蚁,看着它们发现里面不过是一样的水,慌然无措地在杯缘来回踱步(怎么会这样?现在怎么办?要再游回去吗?),那是不是一种我常有的、人生徒劳的感觉?
某天我从朋友处得知有种蚂蚁药很是神效,转身就在网站下了单。突然一阵求知欲,便顺势查了关于蚂蚁的身家背景。或可能是某种不想让你在我的世界死得不明不白的动机吧,总之我得知旧家那种暗褐色蚂蚁是中华单家蚁,现在这种蕊死会留下臭味的叫黑头慌蚁;我还在果园穿梭玩耍的时光,台湾尚未出现令人闻之色变的入侵红火蚁。维基百科告诉我:入侵红火蚁源自南美洲,在1930年代传入美国、2001年左右透过货柜运输及草皮外销等方式蔓延至台湾。那时外公外婆早已将果园分给舅舅们,我也不再和母亲回乡,算是逃过一劫吧。
而在等待货到的日子里,我和室友分头确认蚁踪,好决定届时要把药往哪投。奇怪的是,原本多到让人心烦的蚁路,竟一条一条不见了。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