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翻譯社會學的角度看文科生與理科生的互相鄙夷
最近由於央行一篇論文中,夾雜了一句“東南亞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是文科生太多”掀起了軒然大波。又激起輿論關於“文科是否無用”的激烈討論。眾所周知,我國理科生與文科生素來不睦,前者蔑視後者沒邏輯,後者鄙夷前者沒文化。不過在網上的論戰中,理科生底氣更足一些,畢竟不少文科生選文科的原因只是理科不好,辯論起來未免少了些“理論自信”。

我可能比較另類,中學最擅長的課是語文、歷史和數學。雖然考進復旦數學系,但數學沒考好,反而是語文作文拿了最高分。數學系畢業後先讀統計,最後又轉回曆史系中。這兩天不少朋友問我怎麼看這次輿論之爭,“文科生是不是真的沒用?”。我倒不想辯論文科或理科的重要性,一無新意,二太空泛。但我認為大部分人在為文科或理科辯論時,似乎默認雙方對文理的內涵並無異議,而忽略了一個重要的前置問題:
“文科”與“理科”這兩個翻譯準確麼?如果不准確,錯在哪裡?其中的誤差又如何誤導了我們對於文科與理科的想像?
“文科”與“理科”之誤及其成因
當代文科與理科的劃分,雖然參照西方的教育系統,但在英文中卻並不存在一個標準的對譯。比如文科似乎囊括了英美學校的Art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理科則包含Natural Sciences,Applied Science,Mathematics。這些分類之間也有模糊地帶,比如數學算不算科學,人類學算Humanities還是Social Sciences都有爭議。不過我們就文科的全稱“人文社科”來看,似乎是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的對譯。那麼文科的“文”,應當源於Humanities(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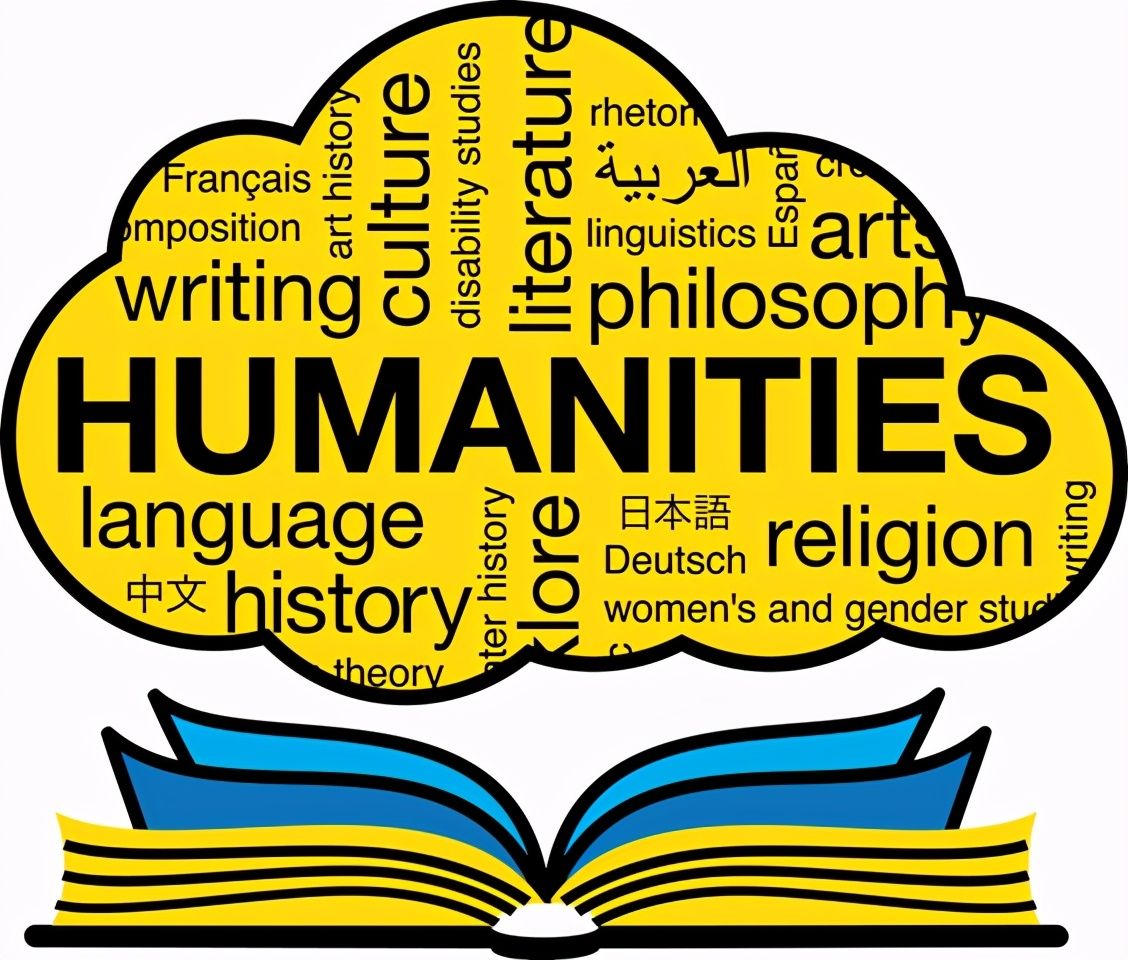
但“人文”一詞出自《易經》:“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這裡的人文和天文一樣,屬於偏義復詞,重點在於“人”和“天”,而非“文”。古文中也有水文和地文,均是研究水流與地質的學問,與“文化”無關。其實文通“紋”,因而關於星象、水流、地脈的活動,都綴以“文”這樣一個表示脈絡的語素。因此我們可以說,把“人文”簡化成“文”,已經錯了,畢竟我們並不把天文學、水文學、地文學也視為“文科”。如今所謂之“文科”,其內涵應當是“人科”,這倒與Humanities的精神相符,後者在文藝復興時,被用於指代世俗社會中的活動及文化,與神學研究相對。
理科的“理”也有類似的問題。俗語說“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這裡的文與理其實是近義詞。地理與地文在古文中內涵類似,只是現代文中地理用以翻譯geography,地文用於代指physiography,才形成了差異。文與理在古文中並不構成一組對立,與“文”對立的是“質”(文勝質則史,質勝文則野)或者“武”(文武雙全),與理對立的是“欲”(存天理、滅人欲)。 “理”也並不跟科學方法論所強調的實證主義有什麼關聯。

但語言是個積非成是的過程,歷史學者不能簡單地說某個現像或概念“錯了”,而應該進一步追尋其何以如此。具體到“文科”與“理科”的翻譯,其成因在於綿延千年的科舉制度。雖然今人把“文科”視為“人文社科”的縮寫,但“文科”同“人文”一樣,古已有之。科舉體系把考試分為文、武兩榜,大眾認知中皓首窮經的“科舉”統稱“文科”。有趣的是,在科舉初期,唐代一度將“算學”納入科舉,即“文科”。而清末迫於時局,清廷推動科舉改革,1887年重新加入算學,1898年開設包含政治、經濟、科技、理工、軍事、外交等內容的“經濟特科”,這些包含了不少“理科”內容的考試,當時同樣歸於“文科”一類。因為科舉“文科”的對立面,是“武科”而非自然科學。
“文科”一詞之所以稀里糊塗地從一種學問的統稱,退化為humanities的對譯,其實正源於這種科舉思維的慣性。 1902年,清廷廢除武科,三年後徹底廢除科舉,“文科”由此名存實亡。但由於思維慣性,科舉強調寫文章(並且也多少涉及如今人文社科中歷史、政治、哲學這些領域),但大部分時間內與數學、物理這些典型的“理科”全然無關。於是命名者基於慣性把他們眼中的西洋新鮮玩意視為與文科對立的理科,把跟科舉涵蓋麵類似的當成了“文科”。但此處的“文”,已經沾上了科舉考試中皓首窮經,重背誦而輕分析的八股味道了。
如果咬文嚼字地說,當今所謂“文科”與“理科”,其實可統稱為文科。畢竟科舉傳統的“文”是與騎馬打仗的“武”相對,知識分子無論文理,本質都不是武夫。一個諷刺的例子是,隨著科舉的廢除,中國的文章學傳統逐漸喪失(高考考生缺乏積澱,其作品及影響不足以跟科舉相比),“文章”一詞的內涵在學界逐漸窄化為期刊論文。在發表論文的意義上,科研工作者顯然也是“以文為生”。嚴格來說,大家都是“文科生”,只是作為對立面的“武科”被取消,所以譯者基於思維慣性,把sciences當成“文科”的對立面。
“文科”與“理科”這組翻譯的誤導性
可能有人會想,就算翻譯錯了,又有什麼關係。名稱只要起到區分作用就行。這句話半對半錯,語言學奠基人索緒爾認為,語言中的所指(語言符號signifier)與能指(語言符號所指代的概念signified)之間的指涉關係只是偶然確立,沒有必然關係。比如humanities這個詞的發音和拼寫跟其內涵無關。但這一論點如今也受到批評,比如索緒爾顯然沒有把中文這種表意文字考慮在內,更未涉及從拼音文字到表意文字的翻譯過程中,選用不准確的翻譯(signifier),會給其傳達的信息(signified)帶來怎樣的誤導。
以“文科”為例,把Humanities翻譯成文科,極易望文生義地把“文科”想像成文獻研究(textual analysis)。實際上不僅國內理科生這麼蔑視文科,很多文科老師與學生也這般理解文科的。一個直接的惡果是,國內文科生天然地排斥量化、編程之類被貼上“理”的標籤的東西。我也遇到幾位國內文科的訪問學者,常把“我們文科不那麼強調邏輯”掛在嘴邊。雖然他們只是自謙,但也能看出文科教育本身對於文科的偏見。
實際上,且不論文科生與理科生誰更有邏輯,至少文科研究比理科更需要縝密的“邏輯感”。原因很簡單,理科的邏輯是顯式的(explicit),一個方程算錯了,等式沒配平,算到最後一步自然出錯(或者無法證明命題)。換言之,理科的數學形式本身就能幫助學者發現思維過程中的紕漏。文科的邏輯是隱式的(implicit),一段洋洋灑灑的話是否成立,史料之間能否形成有效的邏輯鏈,全憑自覺。美國的人文學科比較強調理論性,經常有一些反直觀的論點。討論課上,不時出現研究生以“原作所批判的觀點”支持原作的滑稽場面,這顯然是沒有細讀或誤讀了原作,後者似乎更可悲一點。
舉兩個具體的例子吧。大一的馬哲課上,老師提到事物無限可分,有個學生表示反對“雖然我是文科生,但中學物理教材說原子是物質的最小單位……”這顯然是“記憶”而非“理解”教材內容。教材說的是“原子是保留物質化學性質的最小單位”,就好比人也可以一分為二,但後者不能作為社會人而存在,所以“人體是保留社會人性質的最小單位”,但並不意味著絕對意義的不可分割。當然,“原子(atomos)”這個詞的本意確實是“不可分割”,源於古希臘哲學家德謨克利特的原子論(世界由不可分割的最小單位組成)。但這並不是物理學意義下的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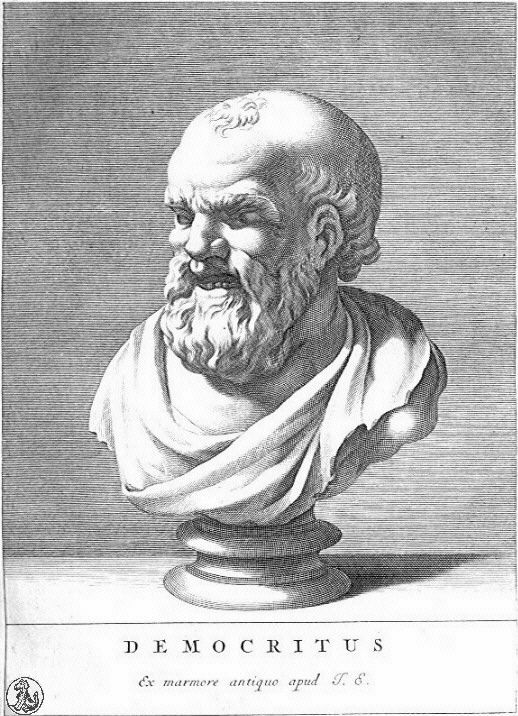
如果說上一個例子可能是把哲學原子論與物理中的原子混淆,還情有可原;下一個例子則更讓人無語,也更典型地體現出“文科輕邏輯”的偏見帶來了怎樣的惡果。在一節社會學課上,要讀布爾迪爾的場域(field)理論。我發現場域和電磁學的場用的都是field這個單詞,便有意地把電磁場的性質與布爾迪厄的分析相對照,發現頗為類似。在《為何閱卷組長成了小鎮做題家》一文中,我分享了這一對比:
“場域”常見於社會學理論,如文學場域、政治場域等。對這個概念最常見的質疑是,場域和通常說的領域有什麼區別?二者最大的區別在於視角的轉換。當我們說領域時,強調的是領域中的行動者,如“電影領域的陳導李導”,這句話的主體是導演,電影只是他們工作的場所。但若要研究電影場域,那就不是研究電影人,而是針對一個抽象的電影圈子,研究它如何對具體的電影人施加影響,以及這個圈子自身的權力結構、流動性等特徵。這是因為場域借鑒自物理學的電場(二者原文都是field)。布爾迪厄認為場域能對其中的行動者造成宏觀上的影響,但行動者本身仍然具有一定的能動性(agency);這對應了電場對微觀上不規則運動的電子產生作用力,使其宏觀上沿著電場方向產生電流。此外,電場作為客觀物質,其自身是物理學的研究對象。因此社會理論家提到場域,研究的也是場域的主體性,而非作為表演舞台的領域。
課上教授問起如何理解場域時,我也以此作答,隨即招致一位國內文學博士的反對。本以為她有什麼理論性的批評,沒想到其理由竟是“我剛才翻了Introduction,沒看到布爾迪厄說他參考了物理學。”看來我在分析場域與電場理論結構的相似性時,她一字沒聽,而是去前言裡看作者的原話,彷彿這才是正確且唯一的研究方法。那一瞬間,我感覺她似乎在從事聖經研究。這個例子無疑體現了國內文科教育訴諸權威、而輕視分析的傾向。後來我在布爾迪厄其他著作中,看到他確實承認受到了電磁場的啟發,不過對我來說,觀察和分析場域與電場理論的相似性,遠比考據布爾迪厄說沒說一句話重要地多,後者是傳記作家、文獻學或版本學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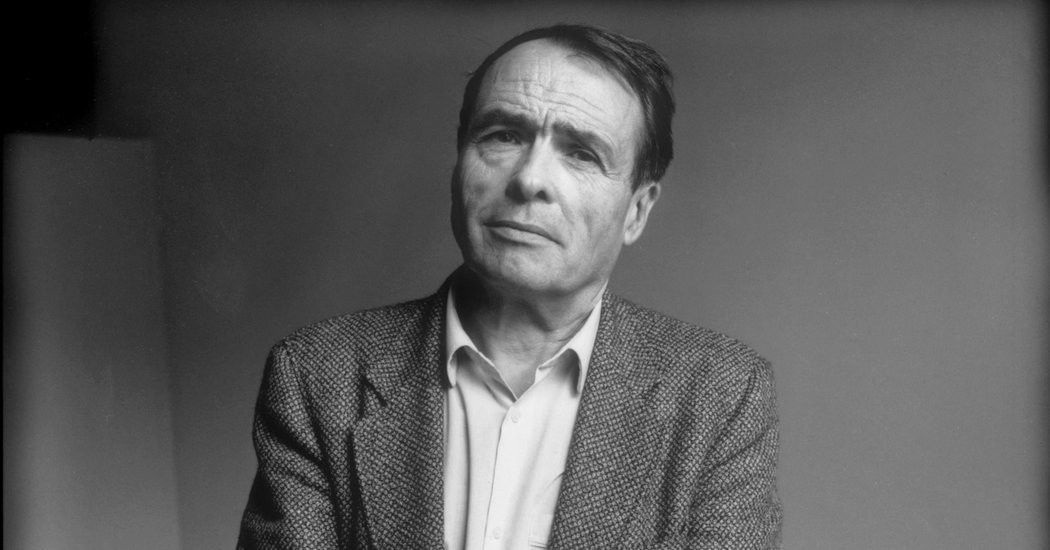
我現在算是“文科生”,所以對關於“文科”的偏見更有切膚之痛。但這種偏見是雙向的,不僅文科生有著輕邏輯、重堆砌的傾向,理科生也因為對文科的這種刻板印象而遠離了人文社科,並以“更講邏輯的高等人士”自居。許多為文科辯護的文章大談文科的深邃、批評性與人性關懷,卻沒有思考人們為何嘲弄而遠離文科。 “文科”與“理科”一詞的流毒正是原因之一。
人科與物科:異質化與同質化的研究取向
那麼Humanities與Sciences的對立,有沒有比文科與物科更恰當的翻譯?
我認為,譯為“人科”與“物科”好一些。當然有人會問,文學是書面文字,為什麼叫人科?醫學研究人體,為什麼要叫物科?這裡的“人”與“物”是隱喻性的(metaphorical)。文學是研究“作為人的物”,醫學是研究“作為物的人”。換言之,一門學問的重心是人、還是物,本質就是我們的側重點,究竟是異質的、與人的心智、精神世界、社會實踐相關的活動;還是同質的、自然世界中的物理規律,抑或人身上同質化的部分(比如作為生物體)。

關於異質與同質的區別,可以援引一位物理教授的觀點。我問他,為什麼物理學家不思考“電子是否有自由意志”之類的哲學命題,萬一它們也會思考甚至發脾氣呢?教授說,我不知道電子是否會思考,但至少在宏觀層面,電子是否思考並不影響我們的觀察,畢竟電子本身也做著無規則運動,只是因為各向同性而相互抵消。也就是說,不論電子是否“異質”,基於我們的研究興趣,可以默認他們是同質的(特別微觀的研究除外)。
自然科學大致也可以沿著這一思路加以分析。舉凡量化研究,必定要對研究對像做同質化假設。中美每天都有數以萬計的實驗室做著科研,大家並不覺得美國的小白鼠,與中國的有什麼本質差異(老鼠個體當然有差異,但在實驗的意義上這個差異被忽略了)。不過在文科或者說“人科”研究中,個體的差異性不僅難以抹去,反而突出其異質性才是研究的意義所在。以人類學為例,之前提到人類學屬於Social Sciences還是Humanities爭議很大,原因就在於學者看待研究對象的視角不同。偏於敘事學的人類學家,認為人類學屬於humanities,每一個故事都自有其深意;側重量化(比如把人群依照種族、位置、收入劃分)的則視之為Social Sciences。
在國內,我很少看到有人以“同質化”或“異質化”來區分文科與理科,更多地是以“需不需要數學”作為簡單粗暴的標準。這當然會帶來一些悲劇,比如國內文科生跨到了美國的“文科”專業,卻被其中的量化折磨地苦不堪言。我有一個中文系的同學就申到了國關的碩士,結果痛苦地上了一整年統計課。她認為國際關係既然是政治學的分支,當然也是文科,怎麼會有數學呢?我們姑且不論文科、理科的命名之爭,研究國際關係,自然要面對海量的資料與數據,為什麼不能運用統計知識及軟件呢?這就是被“文科”的“文”誤導了。如果我們把國際關係視為“人科”,那就不難理解了。相較於物理學中的電子,國際關係的研究對象顯然是異質的,不同的國家、組織、跨國公司都有著各自的利益考量,不服從某種宏觀的“物理定律”;但若和文學批評、藝術之類更突出個人特質的學科相比,國際關係的研究單位仍以機構組織為主,組織內部具有一定同質性,可以量化分析。無論如何,不能一刀切地認為“文科”就等價於跟數學或數字無關。
結語
其實人們之所以對“文科”與“理科”望文生義,還有一重原因,就是古文與現代文的隔閡。今人看到人文之文,已不會想到天文、水文、地文中的“文者紋也”,而自然地將之與文化、文明相聯繫。類似地,由於“理”被用來翻譯“rationality 理性”、“reasonable 合理”,也在語感上與“文”漸行漸遠,而側重邏輯思辨。我們似乎很容易就能接受“理科生”講邏輯這一觀點,卻並未質疑它的逆否命題“文科生不講邏輯”是否成立,而是下意識地默認。反之“理科生沒文化”也是一樣的望文生義。這或許是文理互相鄙視的根源,然而邏輯也好,文化也罷,本就無所謂文理。從這個意義上,晚清科舉改革把人文社科、理工知識一同納入“文科”,反而有著歪打正著的啟示作用。
我提出“人科”與“物科”的分類,倒不是為了取代“文科”與“理科”。在翻譯問題上,我始終持保守態度。唐玄奘曾提出“五種不翻”,其中就包含“順古故不翻(順應之前的譯法,不另加翻譯)。”文科與理科的提法,已有近百年曆史,一朝顛覆,既不可能,也無必要。但是倘若在思考“文科”與“理科”各自的側重與價值時,引入“人科”與“物科”,或者說“異質化”與“同質化”的概念,很多問題或許不言自明。
就我自己的經驗而言,國內與國外文科教育的差距,恐怕遠比理工科的差距大得多。這或許有點反直觀,因為我們坐擁各種“國學大師”,理工科諾獎卻寥寥可數。然而這種錯覺源於學科性質不同:理工類的差距是顯式的。有個段子說,“世上只有數學不會辜負你,因為數學不會就是不會。”理工類的定理證不出就是證不出,零件造不了就是造不了。因而面對美國的圍堵,我們時常感到自己科技實力的差距。但人文類的差距卻是隱式的,胡適所謂“敢開風氣不為先”,雖是自謙,也是事實。五四之際,只要能把西方人文學問嫁接到中國,不論是否準確,至少也有一代大師的名號。理工類就難多了,因為他們本來就要跟全世界在同一套標準下競爭。打個不恰當的比方,之前吐槽大會范志毅吐槽男籃,引發男籃反撲,骨子裡覺得“你國足也配罵我?”其實很多人忽略了,籃球在世界範圍內相當小眾(中美比較熱門所以讓國人產生了錯覺),國籃排名世界29,亞洲第4,最多就跟國足排名世界79,亞洲第9半斤八兩。只是在籃球本就無人問津的亞洲閉門造車,所以感覺良好。文科同樣如此,當人們把“中國哲學”與“外國哲學”、“中國文學”與“外國文學”並立時,文科已經立於不敗之地。然而即便不談文學、哲學這些與語言高度相關的學科,只看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這些社科領域,相對於華人在理工類的成就,依然乏善可陳。
其中的原因既有教育的原因,也有美國與英語在知識生產層面的霸權原因,已非本文所能承載,最後就以我在一個群中的留言做結吧。這段話是回應一位群友認為“文科生至少在馬哲等大學基礎課比理科生強”的觀點,也算點出了我認為“文科”教育落後的部分原因。
馬哲這些“基礎課”可以對標高數。有的文科不用學高數,或者只學高數c,但馬哲也沒有a、b、c,在高中準備比較多的文科生肯定有優勢。但就研究而言,悲劇在於,高數還是那個高數,馬哲卻不見得是那個馬哲。比如找一個理工科(數學、物理、統計)之類的碩博士,功底再差,高數基礎概念微積分之類的總是完全掌握了;但人文社科的研究生,雖然理論上國內從高中就學馬哲,還有大學四年,沒讀過原文或者誤讀的比比皆是。這當然也不怪學生,一方面是學科屬性決定的:國內數學教材雖不如美國蘇聯,但副作用最多就是學得慢一點,啟發性差一點;一個理工科學生不用讀牛頓的原著也能學會牛頓三定律和微積分;文科就不一樣了,很多人批判的馬哲可能只是列寧主義,或者列寧主義都不算,不閱讀整個系統的譜系,只能南轅北轍,但這恰好是高中教育沒法承載的。如果把文科窄化成古詩詞、訓詁學、文獻學這些與中文強相關的,那中國還是有優勢的;但那樣的文科就不足以與理科並列了,人文社科中歷史學、社會學、哲學、政治學這些都離不開理論。但知識生產的上游不在中國。
喜歡我的作品嗎?別忘了給予支持與讚賞,讓我知道在創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續這份熱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