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都死了這麼多年了,你們愛咋咋地吧
前幾天看到一則新聞:考古學家倡議停止進行人骨的性別劃分,因為生物性別並不代表了他們對於自身的性別認知。看到這則新聞的時候,我的第一反應是:Whaaaaaaaat? 瞬間有一種被後現代解構主義浪潮擊打在沙灘上一動不動的感覺,看著遠處離自己三米遠的鹹魚,感嘆這個世界的瘋狂。
接著我的感受是,考古學終於能夠參與到公眾議題的討論中去了……
再接著我的感受是,LGBTQ群體又要承受本不該承受的罵名了……
該倡議是由一個叫做黑鏟的組織(Black Trowel Collective)發出的,他們自稱是一個無政府組織,他們致力於消除當今世界既有的不公正的垂直等級秩序,通過提供小額捐助的方式“積極支持來自工人階級和歷史上被掠奪的社區的考古學生,改變學術界的種族、階級、性別等偏見。”
在archaeologists for trans liberation的聲明中,他們說到,組織支持跨性別群體,希望能夠打破對跨性別者的歧視,在具體行動方面,他們提出瞭如下的倡議[1]:
1、 Archaeologists must center the fluidity of gender in their archaeological practice.考古學家必須在考古實踐中關注性別的流動性。
2、Archaeologists must make fieldwork, research, education, and workplace contexts safe for trans people.考古學家必須確保跨性別者在田野、研究、教育和工作場所的安全.
3、Archaeologists must use their expertise about the past to fight against harm to current people.考古學家必須利用他們對過去的專業知識來抵抗對當下人群的傷害。

更為直接的說辭似乎只存在於單個學者的發言中,如Emma Palladino在推特里說:You might know the argument that the archaeologists who find your bones one day will assign you the same gender as you had at birth, so regardless of whether you transition, you can't escape your assigned sex。 (你必須要知道,有一天發現你骨骸的考古學家會給你分配與你出生時相同的性別,所以無論你是否轉換了自己的性別認知,你都無法逃脫這種性別的分配。 )
他們提出這一觀點的證據是,不同的性別鑑定方法具有不同的準確率:在已知樣本中,蛋白質組學(蛋白質分析)在染色體性別方面準確率是100% ,DNA 是91% ,而形態分析(骨骼研究)的準確率只有51%(Buonasera et al. 2020)。而且,染色體與生殖器外觀、性激素和其他元素一樣只是我們稱之為生物性別的元素之一(Davis and Preves 2017: 80)。科學家估計,1-2% 的人口在生物學上是雙性人(Blackless et al. 2000)。雙性體有多種形式:一些是染色體雙性體,但表型為男性或女性,另一些則具有生殖器或器官差異。 [2]
也即,雖然考古學家現在已經在努力區分生物性別和社會性別,大家對於社會性別的流動性已經有了一定的共識,但他們仍然堅持,即便是生物性別,也是非二元的,而當下基於人骨形態的測量方法是不可靠的。
倡議者提供的另一項證據是,不同文化對性別的認知是不一樣的,而當下社會中最為廣泛的二元性別劃分實際是歐洲殖民霸權在全世界傳播的結果。他們最常用的例子如印度的海吉拉,墨西哥的muxes,波利尼西亞的māhū,拉科塔地區的winkte,[3]這些或早或晚近的社會文化中一直有跨性別者存在,而這些存在往往被當下的歷史研究忽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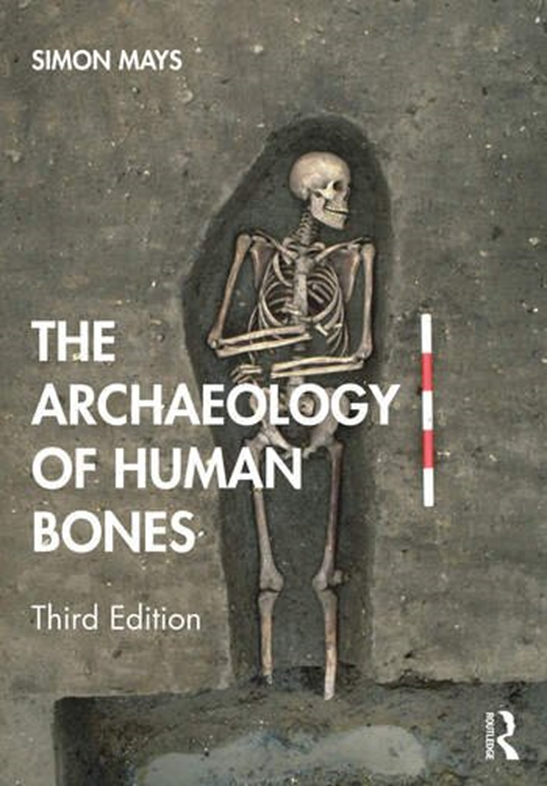
這場倡議本質上是少數群體的政治訴求,它引起爭議的原因是,他們的訴求錯了對象。仔細想想,考古學家在進行人骨性別劃分的時候,他的目的是什麼。考古學一直在強調,歷史不可能百分之百復原,只能無限可能地去逼近真相。那麼在絕大多數人群確實非男即女的情況下,面對一片墓地進行統計學意義上的性別劃分,是當下所能做的最為貼近事實的研究了。在做了性別判斷之後,考古學家的下一步工作可能是人口構成,社會分工,貧富差距,喪葬觀念等等,他們的研究成果能夠對當下的社會,特別是人的性別刻板印象產生多大影響呢?很顯然是微不足道的。而在主觀目的上,他們也從來沒有刻意去打壓和抑制性少數群體的訴求(其實我很懷疑他們是否關注到了這一點)。
當然現在整個網絡上的口風還是批評多於支持, Spectator上的一篇文章用辛辣的口吻指責了這種行為其實是用意識形態的包袱去破壞真實的歷史記錄: " This isn't science. It is politics with a trowel.”[4]TVPworld 上的一篇文章更是嚴厲地指出, They do not even appear to realize that for anthropologists who aim to determine the sex of an individual, that person's idea about their own gender, which is a matter of identity, goes neither here nor there. [5]
其它學者如埃克塞特大學歷史學名譽教授Jeremy Black說, “It is an absurd proposition, a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enders, just a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religious, social and national groups, are key motors in history……This very ideological approach to knowledge means that we're in danger of making knowledge itself simply a matter of political preference.'[6](這是一個荒謬的命題,因為性別之間的差異,就像宗教,社會和國家群體之間的差異一樣,是歷史上的關鍵動力……這種非常意識形態的知識方法意味著我們有可能陷入使知識本身成為一個政治偏好的問題的危險中。)
實際上,近些年來隨著女性視角和性少數視角的加入,考古研究中越來越多地關注transgender/bionary的存在了。人們不再以二元的性別觀念去簡單地將人劃分為男性或女性,而是尋求更加多元、更加具體的闡釋。
Megan Cifarelli分析在伊朗北部Hasanlu遺址中的五十一座墓葬中出土的遺物,其中針、別針和珠寶和被鑑定為和女性的人骨同出,金屬容器、武器和盔甲則與男性人骨有很強的關聯性,而其中有20%的墓葬則顯示出了這兩種搭配的混雜,Hansanlu遺址還發現有相擁在一起的兩具人骨(hansanlu lovers),而其性別均被鑑定為男性,考古學家認為這可能是一對同性戀人。 [7]在布拉格發現有一具男性頭骨和女性隨葬品合葬的例子,該人骨屬於青銅時代的corded ware文化,距今有5000多年的歷史,在這種文化中,男性人骨總是朝著西方並且和隨葬武器,而這具骨骼朝向東方並且和日用容器隨葬在一起。 [8]
如同羅新教授在訪談中多次提到的那樣,並不是學史使人明智,而往往是我們對當下的理解影響了我們對於歷史的認知。考古學也是如此,這一套男女二元的性別觀念是人類在漫長的歷史上發展而來的,可能要追溯到農業社會的誕生以及父權制的發展,而性別的流動性,則是相當晚近的發明與再發現。如同聖何塞州考古學教授Elizabeth Weiss所說, Recent spike in the number of people identifying as transgender suggests that the trend is “social and not biological” and that “retroactively de-sexing [of long-dead individuals] obscures this obvious fact.”(被認定為跨性別者的人數激增表明,這種趨勢是“社會性的,而不是生物性的”,並且“追溯性地對(長期死亡的人)進行去性行為掩蓋了這一明顯的事實。)

這些研究多少還是有點爭議,當研究者認為某些物品和某一性別的搭配“不合常理”的時候,這個“常理”在多大程度上是客觀存在的?我們在研究墓葬中的器物群的時候,很難看到嚴格的二元對立,因為從根本上我們就不能確定隨葬品和死者之間的關係,是死者的生前所屬物?是生者的紀念物?或是兩者兼而有之?
所以非常實際的情況上,在面對一門局限性和不確定性都如此大的學科的時候,如果還是要推翻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科學方法,那就有些太矯枉過正了。當一門學科只是服務於某個群體的訴求和表達的時候,也難怪會被人指責為政治化了。
我們無法在拋棄科學性的基礎上盲目拓展後現代的理論與方法。這其實是全體社會科學所要面對的問題,到目前為止,考古學的大部分理論是社會學和人類學理論的借用,但賓福德的遺產在熱鬧的後現代思潮中仍然佔據了一席之地,究其原因,是考古學的研究對象仍然具有客觀性的部分。
性少數群體反對父權制話語的訴求面向的更多是公眾和政策制定者,放棄人骨分析很顯然對於達成這一目標沒有助益。我們在完成了性別劃分並且逐漸意識到了性別的非二元性後,才會糾正以往考古研究和歷史研究中對於性別分工,家庭觀念,女性地位等問題的認知。
但如果我們仔細看黑鏟組織的聲明,會發現訴求本身是合理的,而且我一直認為在平等尚未實現的時候,激進的政策可以也應該被理解。提供新的性別視角,在具體工作中切實考慮每個個體的權益,以及利用學科本身去抵制某種霸權主義,這些也確實是歷史學科所應該做的。只是其中個別的支持者可能發言過於激進,才會在學界引發如此大的討論。
這又反映了當下性少數群體的另一個問題,當訴求過於激進的時候,社會公眾會在第一時間反駁其中的不合理處而忽視其中的合理處。當輿論演變為一場罵戰的時候,當特殊群體的權益呼籲成為外界眼中的“反智”和“反常識”的時候,他們就很難實現他們最初的目的了。
我一直覺得公眾考古想要發展,就必須去關心當下群眾最關切的話題,所以身份認同比一件“浸透了勞動人民血汗的青銅器”更值得人們關心。我也一直期待考古學能夠參與到這樣的公眾討論中來。而現在,我突然疑惑了,考古學能否承擔得起這樣的任務?考古與身份政治之間,到底有無合謀的必要?
在大多數人眼裡,考古的目的仍然是非常單純的,復原歷史,甚至是更為單純地輔佐歷史研究,只是我們在強調學科重要性或者在申請研究經費的時候會將其拔高到諸如追尋文明的起點追溯人類的本源之類高大上的意義上去。
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確實應該警惕考古的政治性,這是建立於對它的局限性的承認之上的,讓上帝的歸上帝,讓凱撒的歸凱撒,讓激進的無政府主義者和大政府主義者放過這門學科吧。
[1] https://blacktrowelcollective.wordpress.com/2021/07/06/archaeologists-for-trans-liberation/
[2] https://anthrodendum.org/2021/08/06/archaeologists-for-trans-liberation/
[3] https://www.sapiens.org/archaeology/transgender-people-exist-in-history/
[4] https://spectator.com.au/2022/07/how-dare-you-assume-the-gender-of-ancient-skeletons/
[8] https://www.pinknews.co.uk/2011/04/06/5000-year-old-transgender-skeleton-discovered/
題圖:奧古斯丁修道院Nick Saffell
喜歡我的作品嗎?別忘了給予支持與讚賞,讓我知道在創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續這份熱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