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有老朋友嗎?從王毅兩會呼喚新時代的斯諾說起
Hello大家好,我是瑪力。今天看到一個新聞,說的是在3月7日舉行的全國兩會記者會上,王國委在在就“中國外交政策和對外關係”相關問題回答中外記者提問中說到,希望外國記者客觀公正的報導中國,他說,中國希望並歡迎更多外國媒體記者成為“新時代的斯諾”。
那麼,什麼是新時代的斯諾,斯諾又是何許人也。可能除了中國大陸,很多其他華人社會的並不太清楚斯諾這個人,包括中國的年輕一代。
那麼今天,我們就來通過斯諾現象來八一八為什麼中國如此渴望“新時代的斯諾”這個話題。我們就首先來了解這位被稱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的斯諾同志。
埃德加.帕克.斯諾(Edgar Parks Snow),美國記者、作家,1905年生於美國堪薩斯城,1972年2月在病逝於瑞士日內瓦,享年66歲。
斯諾1928年來到中國,他先任職於上海的報社,後兼任歐美報社的駐華記者和通訊員,並在中國各地旅行採訪,曾任教於燕京大學新聞系。
斯諾因報導中共的革命而聲名鵲起。 1936年,他突破國民黨封鎖,訪問了陝甘寧邊區,成為第一個進入中共陝北革命根據地的西方記者,也是第一個採訪毛澤東的西方記者,成為當時的獨家新聞。以此寫成了他的代表作《紅星照耀中國》,後來又譯做《西行漫記》,引起了海內外極大的轟動。
《紅星照耀中國》講述了中共領導下的中國革命鬥爭,以及紅軍的2萬5000里長徵。西方世界透過斯諾的第一手資料,首度得知中共及其領導人早期的面貌。此書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在其取得政權前的情況,向西方世界做了最具影響力的報導,被認為是無可取代的歷史經典。
甚至影響了影響了部分中文詞彙的英文官方翻譯,比如英文中的Long March(長征)在《牛津英語詞典》中的註腳就是引用的《紅星照耀中國》。
斯諾在中國期間,積極參與中國的革命活動。在抗日戰爭期間,他和宋慶齡等人在香港成立**“中國工合國際委員會”,**並為中國的抗戰籌集資金和物資。
1941年1月,斯諾在香港得知皖南事變,遂在《紐約先驅論壇報》報導此事,指責國民黨軍隊對新四軍的突襲。同年2月初,國民黨政府取締斯諾的採訪權,斯諾被迫離華。
之後斯諾又作為戰地記者輾轉中印蘇多個國際戰場,整體來說,斯諾的報導和著作很多都是以共產主義為視角來進行敘事。對於中共,斯諾強調其角色主要是反法西斯陣營,並認為是推動中國民主的進步力量。所以他被一些學者認為有明顯的宣傳色彩,並不符合新聞中立原則。或者是認為他只是把共產主義浪漫化了,有他的歷史局限性存在。
戰後由於美國麥卡錫主義盛行,加之和共產黨的關係,斯諾在1959年被迫移居到瑞士直到去世。
好了,關於斯諾的生平我們就先說到這裡,從上面的描述中,我們不難發現,斯諾同志雖然不是共產黨員,但客觀上來講,他努力為中西搭橋,讓西方了解中國,認識崛起中的中共。還影響了英語,豐富了詞彙,促進了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從這一點來看,斯諾做出的貢獻確實是值得肯定的,他被稱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一點也不為過。
雖然通過現有的資料我們很難給斯諾同志的政治傾向下一個明確的定義。他傾向於某一種主義或者他更認可哪一種價值觀,作為一個出身在民主和自由社會的人,完全是他個人的權利。自然而然,並不能代表他所認同就是都是正確的,他反對的就是邪惡的。而他描述的是否公正客觀,自然而然也要經得起歷史的考證和質疑的聲音。
關於斯諾的還有幾個小故事值得我們仔細品味。
第一個故事就是,1970年代斯諾和他的第二任妻子曾經再次訪問中國。
在此期間呢,斯諾夫婦得到了不亞於國家首腦的待遇。周恩來和他們一起觀看乒乓球賽,和宋慶齡共進晚餐,在國慶遊行時,他們與毛澤東並肩站在了天安門城樓上,並將這種待遇表示為和美國重啟關係的重要信號。那時候離尼克松訪華還有整整兩年時間。毛澤東曾經對他直言不諱的對他說,當年如果不是日本人的入侵,共產黨也不會發展壯大並奪取政權。 (〈毛澤東會見斯諾的談話紀要〉,根據1971年5月31日印發之談話紀要個別文字刪節刊印本)
第二個小故事,斯諾訪華後回到瑞士之後,健康狀況開始惡化,毛澤東和周恩來曾專門派出一隻由三名醫生、四名護士和一名翻譯組成的醫療團隊前往瑞士幫斯諾進行治療。即使在1972年斯諾去世後,斯諾的夫人惠勒也與中國領導人保持著良好關係,頻頻訪問中國,直到1989年的六四事件。
斯諾的夫人惠勒在2000年接受《時代》亞洲版(Time Asia)採訪時說。 「我當時是個享有特權的人,出行坐的是有花邊窗簾的紅旗豪華轎車,」「我能見到這麼多人,就只是因為我是埃德加·斯諾夫人。」
第三個小故事,六四之後,惠勒斯諾開始重新審視那個她和他丈夫的曾經熱愛和崇敬的政權。她曾經發誓再也不會重回中國。多年來,她都會給鄧小平、朱鎔基等中國高層領導人寫信,希望藉助她丈夫在中國的聲望,呼籲人們去關注被天安門鎮壓影響的家庭的困境。惠勒覺得,秉承埃德加·斯諾之名,她有責任在中國利用這個名字做一些事情。
2000年,時年79歲的惠勒斯諾最後一次回到北京,希望能把一筆捐款轉交給「天安門母親運動」的發起人丁子霖,她的兒子在六四事件中喪生。但是那一次到訪,惠勒斯諾和兒子前往葬著丈夫一半骨灰的北京大學墓園,全過程處在監控之下。當他們試圖與丁子霖見面時,至少有二十多名便衣警察將他們包圍,秘密拍攝,並禁止他們進入。丁子霖對阻止她們見面的警察說:「你們怎麼能這麼殘忍?她是中國的老朋友。」所以,這次的到訪自然是嘎然而止了。
直到2018年,97歲高齡的惠勒斯諾在瑞士逝世,之前再也沒有重返過中國。
好,關於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斯諾先生和他的夫人的故事我們就先說到這裡吧。如果斯諾先生能活的更長的時間,他是否也會像他的夫人一樣重新審視那個他曾經追隨一生和為之奮鬥的國家,我們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作為一名知識分子和學者,斯諾先生一定會跟她的夫人共同探討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的王國委呼籲外國媒體能成為“新時代的斯諾”,不免有點貽笑大方了,到底是希望外國記者們成為那個會寫讚美文章的斯諾,還是那個熱衷文化傳播,關心人權的斯諾夫人呢。我相信斯諾夫人如果還在世,聽到中國的領導人再次用她丈夫的名義和威望呼籲的時候,心理也是五味雜陳吧。
那我們不妨以斯諾的故事為延展,繼續談一下「中國人民的老朋友」這個話題。
我記得從小時候開始,我們經常能聽到新聞報紙上對某些國際友人這樣稱呼,比較出名的有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金太祖日成同志、新加坡國父李光耀、前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等。據媒體統計,《人民日報》上先後有六百餘人被稱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這一稱呼出現的頻率,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改革開放初期、六四天安門事件結束後、鄧小平逝世後分別達到了高峰。不過,從胡溫時期起,這一稱號在《人民日報》上使用的頻次已從每年50次左右降低至20次左右,到現在幾乎已經沒有這樣的稱呼了。
我們不難發現早年反帝、反殖、反侵略是辨識“老朋友”的依據,而隨著中國外交不斷走向務實,'老朋友'稱呼的意義也逐漸淡化。
中國人民的第一批老朋友,大多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到過延安。因為抗日戰爭,一起扛過槍的戰友與“中國人民”結緣除了人盡皆知的加拿大大夫白求恩,印度、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阿根廷、美國、英國等國均有醫生來到中國的戰場救死扶傷,並結下友情。
還有一個老朋友群體就是以斯諾為代表外國記者,他們向外界報導神秘的中國,讓毛澤東領導的革命運動為世人知曉。外國記者中最有名的斯諾、斯特朗、史沫特萊被並稱為“3S”,1984年,中國專門成立了“中國三S研究會”,鄧穎超任名譽會長,原外交部長黃華任會長。後來,這一機構改名為“中國國際友人研究會”。
革命年代結束後,社會主義陣營和第三世界國家的老朋友多是這段時間結下。
不過,如果能為新中國的建設做出貢獻,或是能在國際社會正面宣傳中國的建設成果,那麼即使是擁有“不友好國家”國籍的人,也能被視為老友。 1957年出版了《中國經濟》一書的美國人愛得樂即是一例。
在1970年代的建交和恢復邦交浪潮中,幾乎所有為外交正常化做出過重要貢獻的政要和民間人士被悉數列入老友群體。像墨西哥前總統埃切維利亞這樣堅決支持恢復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領導人,則更被視為親密朋友。
從1987年開始,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又增添了一個新群體——國際組織的負責人。比如曾任聯合國人口活動基金主任的拉斐爾·薩拉斯。 《人民日報》報導說,薩拉斯“生前一貫堅定支持中國的人口政策(計劃生育政策)……當國外少數人惡毒攻擊中國'推行強制墮胎和強迫絕育'政策時,他挺身而出,發表聲明,予以駁斥”。前不久聲名遠揚的WTO總幹事譚書記也是近些年為數不多的國際組織老朋友之一。
隨著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發端,經貿領域的老朋友也開始出現,尤其是在本國反對聲強烈時與中國開展貿易關係的商人更受推崇。比如以日本友人為代表的政商屆大佬,從1972年開啟中日關係正常化的首相田中角榮開始,到岡崎嘉平太等企業家,前後有10多位日本友人都獲的老朋友殊榮。
說白了就是誰對我有利,誰就是老朋友。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張清敏說,“中國人處理外交關係往往從感情、關係出發,羞於談利益,而是代之以朋友的稱謂。”對於這一點,我們之前的視頻中也談到過跨文化語境的問題,作為高語境文化代表,中國非常喜歡老朋友這種說法。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對於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中國政府不吝給予高度禮遇。
高級領導人的會見和宴請是一種常見的款待方式。只要認為與中國人民的友情足夠深厚,即使是像斯諾夫婦,荷蘭導演伊文思、英國作家韓素音這樣不具行政級別的文化界好友,也能夠與中國領導人聊天吃飯。除了宴請,國家領導人還會親自拜訪老朋友,王震就曾以中日友好協會名譽會長的名義到日為日本友人岡崎嘉平太祝壽,還轉交了鄧穎超向其贈送的“壽”字盤。
當然,中國政府款待好友,也期待著他們能“講義氣”給予中國回報。在中國看來,朋友就意味著不應該做對不起自己的事情。如果危害中國最核心利益的事情,自然也不會是老朋友。非常諷刺的是,大多數諾貝爾和平獎的獲得者都是中國人民恨之入骨的反面教材。
跟斯諾形成鮮明對比就是,前美國駐華大使,燕京大學校長,對中國的教育業產生巨大影響,在抗戰中給予中國人民巨大幫助的中國通司徒雷登先生,卻沒有得此殊榮。
聞一多在《最後一次講演》中一整段談司徒雷登,這段話如下:“現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國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長在中國,受的美國教育。他住在中國的時間比住在美國的時間長,他就如一個中國的留學生一樣,從前在北平時,也常見面。他是一位和藹可親的學者,是真正知道中國人民的要求的,這不是說司徒雷登有三頭六臂,能替中國人民解決一切,而是說美國人民的輿論抬頭,美國才有這轉變。”
大多數中國人對於司徒雷登這個名字的了解,是來自於毛澤東的那篇著名檄文《別了,司徒雷登》,文中藉司徒雷登,對國民黨和美國當局極盡諷刺。而司徒雷登被長期當作是美國對華政策失敗的代表人物。自然也不會是官方口中的老朋友了。
說了這麼多關於老朋友的話題,我們不難發現,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其實不過是政治宣傳的口號而已。至於是不是雙標,大家自己去判斷。我們反觀目前的中國的國際形勢,無論從川普政府的貿易戰開始,到CGTV和BBC的落地之爭,還是華人導演趙婷的「無依之地」的輿論風波。
我們回到本次的主題,王國委這番話,言下之意已經明確的表示出,對於外媒記者,中國政府只能接受的是對於中國正面的報導。換句話就是說,對於負面報導的零容忍。我們設想如果是一個人,直接表示熱烈歡迎大家來讚美我,但不接受反駁和質疑。你會跟他做朋友嗎?
隨著冷戰結束到蘇聯解體到中美摩擦,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似乎越來越少,誰是敵人誰是朋友,每個人心中自然有自己答案。當戰狼粉紅們打著雞血列出那些反華辱華的清單的時候,我們的老朋友已經離我們漸行漸遠。
最後,我想說的是,真正珍惜的朋友,除了那些熱衷於錦上添花和賣力吆喝的酒肉朋友,更要記住的是那些曾經雪中送炭但也批評過你的最佳損友。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吧。我是瑪力,這是瑪力說的新頻道瑪力再說,如果你覺得這個視頻還不錯的話,麻煩幫忙轉發,分享,訂閱支持一下,我們下次見,88咯。
喜歡我的作品嗎?別忘了給予支持與讚賞,讓我知道在創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續這份熱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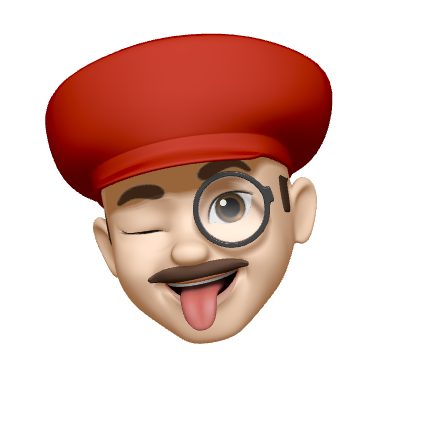
- 來自作者
- 相關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