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围炉,大学生思想、经历的交流平台。以对话为载体,发现身边有意思的世界。 香港大学|上海纽约大学|复旦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 清华大学 | JointU综合联校 | 哥伦比亚大学
对话梁君健:影像的田野,田野的影像| 围炉· PKU&THU

梁君健,1983年生,博士,导演。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人类学系访问学者,学术作品见于《人民日报》《当代电影》等刊物,并在世界人类学大会、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电影节等学术会议上报告过自己的影视人类学研究与民族志电影创作。
从事纪录片拍摄,曾执导作品《喜马拉雅天梯》《我在故宫六百年》等,曾获中国电影金鸡奖提名。
影像已经成为时代文本。
从藏地天梯到西南边陲,从短视频到虚拟现实,影像精准地捕捉了现代社会那些易逝的碎片与永恒的瞬间。对人类社会而言,它早已不仅是一种记录方式,更在形塑我们的生活。
自2012年起,梁君健老师开始执教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生们亲切地称他作「梁导」,他讲授的课程为许多年轻学子打开了理解影像、理解社会的大门;作为一名纪录片导演,他创作的《大河唱》《一张宣纸》等作品已然成为影像中国的留存。
从影十年,梁导的视野横跨纪录片与人类学。
对他来说,田野也许有两层含义:既是鲜活的人类学场景,也是知识与想象的原野。在镜头前,他记录田野的影像;在课堂上,他为更多人开拓影像的田野。
1|影像缘起:课堂十年
问:您现在的研究方向比较广泛,包括影像人类学、媒介与社会等领域。您的学术兴趣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
答:我是在研究生的阶段开始慢慢对学术感兴趣的。因为从本科我动念想转系开始,一直到研一研二的时候我都比较希望做创作,做纪录片摄影师和导演。但是到了研究生之后,个人的视野得到了进一步的开阔。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我特别得益于那时候新闻传播学院和人文社科学院一系列的课程,包括罗岗老师的文艺学、格非老师的小说叙事学,后来又选了汪晖老师、秦晖老师的课等等,但这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张小军老师关于人类学的课程。这些课慢慢地听下来,我开始发现,通过研究资料和社会现象去理解和更深入地回答社会问题,对我来讲是一个特别有挑战性、并且我也特别喜欢做的事。那个时候,教我纪录片的雷建军老师正好在曼彻斯特大学做完了半年访学,带回了影视人类学这样一个交叉学科的概念。我发现在我所喜爱的纪录片拍摄领域和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有很多共通之处。所以在研二的时候,我就开始考虑要不要读博。后来我获得了提前读博的机会,继续在影像领域做研究。
问:您走上学术之路,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是得益于您本科阶段接触的宽口径通识教育。现在国内包括清华在内的很多大学正在推广通识教育,在推动影像教育的过程中,您是怎么看待通识教育的作用的呢?
答:通识教育能够让学生借助这些课程去认识不同领域的顶尖学者,感受到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和看待世界的态度,这对于人文领域来讲是首要的。他们知识的广博、理论的精深自然不必多说,然而他们对待世界和学问的态度,所提供的独特且多元的精神世界才是最核心的价值。现在的充分分工下的社会不支持、不培养通才,因为我们最终进入社会时,不论是从事研究还是行业工作,基本上都必须是专才,但是这样一种价值观和看待世界的方式是要通过通识教育为青年树立起来的。
问:您觉得影视教育是否应该作为通识教育的一部分进行推广呢?
答:我认为是有必要的,这些年也一直在尝试。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影视作为现代社会的大众流行文本,不可避免地会和社会的各个领域发生关联。我们现在所遇到的一些前沿性的问题,在价值和伦理上所经受的考验和焦虑,都一定会反映在电影里。所以我们会看到电影类型正在变得多样——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出现了科幻片;现在人工智能发展迅速,我们又有很多电影去反思人工智能问题,去思考多元宇宙的问题等等。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电影,包括流行的影视剧,它是一种寓言,也是一种帮助我们去思考广泛的人类处境的一个手段。我们可以通过电影去思考政治,通过电影去思考历史,通过电影去思考未来。
另一方面,我这些年在学校上课时,以及大二暑假我们带同学出去拍纪录片、做清影工作坊的课程时,也体会到了影视教育的通识价值。大多数的同学毕业之后都不会直接从事影像创作,但是借助影像创作,大家可以通过镜头去认识自己,和不同的世界发生交集,让自己的生命经验得到拓展,也会在这个过程中去反思自己对待别人的态度。所以我觉得影像创作作为一种和人沟通的情境能够激发创造力,训练我们团队合作的精神——尤其是在组队拍纪录片的任务中。另外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影像打开了我们与这个世界沟通的多元途径。所以说我觉得从这两个角度来讲,影像教育作为通识教育是很有价值的。

问:您在从教过程中遇到过一些比较让您印象深刻的故事和经历吗?
答:其实每年我看大家的作业和作品的时候,都还是挺有感触的。但是如果说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我觉得是我在课上被同学挑战的时候。这其实也是在教学中不断教学相长的过程。每一年都会有学生对我的品位和我对于大家作业的要求提出质疑,比如,我会要求大家在拍摄作业的时候要尽量多地了解被拍摄对象的信息,要求大家多次反复地拍摄一个人,建立起比较深的信任和人际关系。很多时候同学会认为,这样是不是在剥削拍摄对象?我如果希望能够拍一个不太一样的影像难道不可以吗?这样的一些问题我在教学早年没有特别主动地去思考过,我是在把我自己所接受到的影像教育,以及我在一些作品中慢慢总结出的一套方法和价值传递出去。但是在课上不断地遇到同学们的反馈、疑问和探讨的时候,我也开始思考为什么我会拥有这样一套价值,我也在思考作为一个教师,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主导课程的内容,应该怎么样把我自己的创作经验和教学经验,与大家凭直觉来进行创作和学习的情境进行更好的结合。
另一方面,每一次看到大家的作业,对我来讲都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鼓励。对于任何性格和背景的学生来说,影像不仅有报道的价值,而且也确实给同学的成长提供了很重要的资源。这也会激励我自己更好地去创作、去教学。这些都是在教学过程中让我特别难忘的一些事情。
问:您刚刚提到您会尝试在课堂上向同学们讲授您自己学到的一些方法和价值,那么您现在希望通过影像教育让学生们学到什么样的方法,培养怎么样的价值观念?
答:首先,大家在使用影像的过程中,第一步肯定要学一系列的知识和技能。大家要掌握摄像机,要掌握构图、光线,要学会剪辑,要学会基本的视听语言。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大家要去了解、思考自己的拍摄对象。
第二点是大家要学会长期投入和不断打磨。因为影像的学习其实就是一门语言的学习,我们不论是学习母语还是学习一门外语,都是在不断背单词、大量的阅读和书写的过程中掌握,掌握影像其实也一样。所以我觉得影像作为一门技术和艺术需要大家不断地训练,不断地模仿,不断地去挑战自己的既有习惯。我特别希望,如果真的喜欢影像那就一定要投入——因为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你不能依靠你所期待的「天赋」 、「突发奇想」或者「魅力时刻」来完成自己的梦想,而是需要大量的努力和时间投入才能让你在合适的时候能创作出好的作品。
再进一步来讲,我希望大家首先要发展出对拍摄题材和具体的拍摄情境的亲切感和好奇心。拍摄对象不是一个任务,而是一个等待你去了解,甚至在了解过程中,可能会让你头破血流的未知领域。要有勇气和好奇心去打开这个自己所不太知道的黑匣子——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去认识世界的勇气。很多时候我们生活在舒适圈里面,有意无意地去回避可能给我们带来刺痛的一些现实。
再接下来是基于理解包容的所谓人文关怀,或者说一种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或者「人文关怀」这样的词语很多时候会被滥用,会变成一种自我感动或者廉价的怜悯,一种从上往下的施舍。要去试着理解和认可他人,但是也要承认,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完全理解别人的感受,我们只能去倾听,去接受「完全理解」的不可能,接受我们共情能力的有限。然而,我们仍然要尽量地去理解、去表达,并且认识到这是有缺憾的、不完整的。
创作是一个「开盲盒」的过程。有些时候各种条件都具备了,拍的东西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但有些时候因为技术条件和当时情境并不太理想,拍出来的东西可能只打动了少数人甚至只有你自己,但这也并不代表着失败。这就是最后一点,我们应该怎么看待我们的创作。不要用一种功利性的态度去看流量影响,而是要把影像作为生命中的一部分去认识它对于自己、对于报道对象更长远的价值。
问:您之前在文章中谈到过您对90后创作者的分析和观察。 90后到00后这十年,技术设备还有社会心态都发生了很多变化,您会觉得00后的学生又有什么样的一些新趋势和变化?
答:首先00后的创作者对于技术和设备的熟悉感肯定增加了。我想今天的大学生或多或少都有一点自己制作视频的经验,最基本的也会做一些vlog,剪一些小视频发到社交网络上。而且大家观看各种各样的影视文本的机会在增加,影像越来越成为了我们主流的文化形态。因此,技术恐惧感,或者说拿起摄像机所需要跨过的技术门槛是在变低的。
但是,困难变小了也意味着我们往往容易「滑过」从业余使用者到专业使用者的训练区间,而这个训练区间有助于我们反思技术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因为我们常常带着一种比较天然的技术乐观主义去进行创作,而更少意识到影像技术的缺陷和问题。
还有一点是随着社会和媒介的发展,这一代比上一代所掌握的知识面和所触达的社会广度一定是在增加的。但是反过来,这种碎片性知识的增加并不确保对于社会的理解能力的增加,
知识过多时,我们的理解能力反而会退化。因为信息爆炸之后我们不再珍惜信息,不再去对信息进行总结归纳,而越来越习惯于不自觉的去相信结论,这可能是信息过载之后给我们带来的普遍性影响。

2|影像何为:虚拟、真实与私人叙事
问:您刚刚谈到当下信息爆炸对整个影视创作乃至青年一代带来的影响,我看到您也在去年发表的文章中谈到了新兴短视频对于视听话语形态带来的变革。作为一名研究者,您认为影像领域将来还会有什么样的发展趋势?
答:首先,影像的使用语境现在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扩展。我们现在无论做什么事都可以用影像作为文字之外的一个选项,而且往往影像会更受欢迎。在未来,我想影像会更大程度突破摄影和电影最早期“机械复制”的特点。例如,现在在网络会议上面对面的时候,人的背景都可以是虚拟的了,有了元宇宙和更强的运算能力之后,未来可能连我们的面容都可以虚拟:我们把自己的面容做了3D扫描,让AI进行学习之后,可能我什至不需要打开摄像头,我的面容就会出现在屏幕当中。未来视频和人工智能之间的结合会更加紧密。
而且现在脑机技术也在发展当中。我们知道大脑思考时是有形象的,思考有时是先出现画面,再用语言去组织头脑中出现的画面和影像。那么有了脑机接口之后,会不会不用经过文字语言这一关,我们也可以直接通过图像去完成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我觉得这将是在我们有生之年能看到的一些重大变革。
另外还有一个方面是,影像的虚拟仿真特征越来越明显。特别是未来裸眼3D技术出来之后,我们借助影像对于环境的感知能力会发生变化,我们个人经验的重塑和获得恐怕也会发生变化。
问:您最近应该也关注到了一个关于“二舅”的视频,该视频因为有虚构成分被b站撤销了推荐,这也引起了进一步的争议和讨论。您怎么看待这样的纪录影像中真实和虚构的权衡?
答:纪录片的真实伦理一直是一个经常被讨论的话题。现在一个比较传统的观点认为,首先,纪录片一定是有真实特征的,但是这种真实不一定是完全的客观真实,它是由创作者对于客观真实的影像展开主观创作所产生的真实。我们一般认为真实性首先在于素材是真实的——当然这个也会被一些影像挑战,比如说现在越来越被认可的动画纪录片。动画肯定不是机械复制的的真实,而是根据真实的史料和个体对于历史的回忆所建构出来的。另外也包括我们在电视纪录片里面经常看到的搬演段落,特别是在一些历史类的纪录片里会用演员、在摄影棚中按照史料复原场景,这个也不是“真实”,而是跟动画有点像,都是用我们今天的影像去帮助大家理解有限的历史记载。
所以我想纪录片的真实性是在一个范围之内波动:最极端的是最严格定义上的真实,而这种真实往往是很难实现的,因为一旦我们架起了摄像机,我们就有把镜头对准哪里的选择,这其实都是在对所谓的真实进行加工建构。所以我想纪录片不存在绝对的真实,只有相对的真实。
它是行动主体,是创作者,当然也包括观众,是主体对于真实的理解,是一种再现和一种重构。
问: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影像人类学这门对中国大陆来说还很新兴的学科。
答:影像人类学是以人类学研究和文化理解为本位的,更具反思性和主动性的一种影像创作和针对性研究。
从历史上来看,这个学科其实经历了好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最早的阶段是人类学家在田野调查时用照相机和摄影机去进行记录,包括人物肖像、物质文化和仪式性文化的记录,因为影像记录会比文字更直观,而且信息量会更大。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有一批人类学电影的工作者超越了简单记录,希望把视听语言作为和文字民族志平行的手段。因为传统人类学作品,像《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等是用文字写就。到了五六十年代的一批人类学电影工作者或者是人类学电影的导演认为,也可以用视听语言、纪录片甚至是用电影的方式去完成民族志和对于社群文化的完整表达,而不只是把他们拍摄成一个档案数据库那么简单。在使用影像作为一门组织思想的语言的过程中,人们发现,因为媒介特质的区别,影像和文字在进行文化表达和民族志写作时有不同的偏向。因此除了制作人类学电影和纪录片之外,研究者也开始慢慢去研究影像本身作为一种媒介的特点,比如语言学方面的一些特点。另外还有一批做影视人类学或者视觉人类学的学者倾向于研究不同的文化群体怎么使用视觉手段,既包括没有文字的民族的用岩画等视觉符号去表意和组织他们的社会生活,也包括今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如何去看待和使用影像——影视人类学包括了这样的一些研究。
问:如果说在纪录作品中影像是不完全的真实,那么在影像人类学的研究中,影像的作用到底是什么?
答:在研究的过程中影像当然首先是一个档案。比如,我的面前发生了一个传统的仪式,我可以用影像把它记录下来并且不断地回看这些影像,去分析我在现场可能没有注意到的细节,这个就是档案和记录的重要性,它可以弥补人的认知的不全面。
另一方面,它和刚才讲的影像的教育功能是类似的,也就是说影像是一种进入和沟通的方式。当我们有了影像之后,其实是在对我们的拍摄对象,对我们所研究的社区进行介入;而当别人看到你拿着摄影机进来的时候,他们也会意识到你是在记录他们的生活,这会促进我们和拍摄对象之间的更多的交流甚至是合作。如果影像用得好的话,我们可以帮助被摄对象展现他们所认为的这个世界,帮助研究者更好地去理解他们的世界观。
我之前拍摄《一张宣纸》,是一部跟非遗相关的记录南方手工造纸的纪录片。当时我住在拍摄对象家里。我自己习惯晚上要整理素材,但拍摄对象特别热情,经常晚上也会陪着我聊天,于是慢慢地就变成我们一起看素材。当他看到我镜头里拍摄的他的生活和他的手艺,会给我补充好多新的信息,我们会围绕影像素材展开进一步的讨论。他会评价我的素材,也会给更多的建议。从他的反馈建议里面,我对他的技艺的理解,对于他的世界观的认识,也会不断得到强化。这时,影像就提供了合作和交流的渠道,而非仅仅地记录。
问:不同于影像人类学这样严肃的学术创作,近来出现了很多独立纪录片,“私影像”、“家庭影像”也大量出现。您是怎么看待这样一些独立的、地下的个人创作呢?
答:它们有自己的独特价值。因为它们是更个人化的表达,这也就意味着在表达的过程中,独立纪录片是和个人的体验,和“小世界”更加紧密相关的,更便于我们去认识和理解这个世界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像人类学会受到它的学科规范影响,在大众媒体上播出的纪录片就会受到行业规范性和观看市场的影响,它们都受缚于一种很强的外在结构。当然,独立纪录片——哪怕是vlog这样的个人创作,也并不是所谓的完全价值无涉和完全无立场,反而是个人性很明显,因此我们在观看这样的作品时,既看到了它所记录下来的客观生活,也看到了不同的个体是如何把自己的主观认知和主观情感与他们所经历的生活结合。这是今天在大众传播的平台上不可或缺的一种组成。

3|影像实践:用影像温暖世界
问:了解到您会参加一些电影节的选片工作,在参与电影节选片的过程中,有遇到过一些让您印象深刻的经历或者作品吗?
答:前两年我看过一个特别让我印象深刻的纪录片,叫《The Flat》,是2011年由以色列一个青年导演拍摄的一部纪录片。主人公在收拾去世的外祖父的遗物时,意外地发现外祖父居然珍藏了几份纳粹的报刊。而在这与之前他对自己外祖父的理解完全相反,外祖父经历过二战和大屠杀,是一个与纳粹英勇战斗的爱国主义者。因此,他很奇怪为什么外公会珍藏纳粹报刊。后来,他进一步地发现,外祖父有一个特别要好的朋友居然是纳粹军官。于是,他开始去访问他的妈妈和爸爸,又曲折地找到了他的外祖父朋友的后人去进行采访。当然,受访者对这些话题都三缄其口,但是经过不懈努力,他最终奇迹般地还原出来了这段个人史。
在我们今天看起来,这样的事情不太可能,但个人的历史和国家的历史在那时的确产生了特别复杂多元的交织,这是一个超乎我们对于历史的刻板印象的和一般性认知的纪录片。这部片子既特别私人——是一个孙辈对于祖辈生活的探寻,同时也是一个很公共的话题——它反思了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理解历史的不同面向。
问:可以聊一下最近的一些研究方向或者拍摄兴趣吗?
答:从2017年至今我在拍摄一部和流动儿童相关的纪录片,现在还在后期的过程中。这部片子拍摄的是蒲公英中学的合唱团——一群从小生活在北京的初中生们。通过他们和音乐的故事,去看城市的发展,尝试去理解少年怎样对待生活。
另外我还在继续关注非遗和历史相关的一些题材,比如,我这些年一直在陕北地区拍摄当地的道教民俗。还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题目,但是一直还没有开始拍,就是我们中国传统一句老话叫「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和山川草木的关系是很丰富的,这是我当时在拍摄《一张宣纸》的时候开始有所体会的。到了南方之后我发现,许多花草和动物我都完全叫不上名字来,但这些做宣纸的匠人们会如数家珍地告诉我们这个东西长在哪里、什么味道、能被用来做什么。在以前那种传统的生活中,人们发展出来了一种特别宝贵的对于自然万物的知识和情感。我特别希望能够通过影像的方式,把现在仍然生活在山水旁边、饲养着牛羊的人们的生活,以及其中所体现出的自然的诗意的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表现出来。

问:现在有许多青年学生和创作者希望自己能够拿起机器去拍摄,但他们可能会遇到各种来自自己或者外界的阻碍,您作为一个前辈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建议和提醒呢?
答:我觉得有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第一,如果不是一时兴起而是心心念念要去创作,那说明影像对你的个人的生命经历是有独特价值的,那就去找个机会把它给做出来——不要管实现得好还是不好。就算不好也是一种人生经历,最终会成为个人成长的养料。
第二,在开始之前仍然要谨慎。因为拍摄毕竟很耗费时间精力,不仅是自己的也包括他人的,还会影响你的社会关系,「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正是因为开始拍摄是一个成本很高的事情,所以事前一定要周密准备、充分调研。进一步地,在做的过程中也要自己不断地去激励自己。基本上我做每一个纪录片的过程中总有那么一段时间是充满着自我怀疑的,觉得这个片子可能做不成,觉得这个片子可能是我做过的最烂的一个片子,这种时候一定要学会直面自己的情绪和焦虑,要多找一些能够激励自己的方法。比如说我会跟别人聊一聊,去看几部好的纪录片。
问:您参与的清影工作室的标语是「用影像温暖世界」,您是怎样理解影像对于这个时代的意义的?
答:首先像我之前谈过的,影像是一个档案。我们想象一两百年之后,要了解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了解这个星球,可能我们会从影像中获得很多文字中所获得不了的知识。
另一方面,影像对于社会来讲,是人类进行情感交流和凝聚共识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土壤。为什么今天许多像二舅这样的视频引爆全网,其实正式因为它们凝聚了我们的一些共识,在表达着我们一些共同的心理焦虑和共同的期待。虽然说这个视频可能有夸张不实、有粉饰苦难的地方,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承认,这段影像确实切中了今天我们的心理需求,它短时间内的强大传播力意味着我们今天需要借助影像去做一些表达和宣泄。
问:最后想请您向想进入影像世界的初学者们推荐一两部纪录片或者一两本书。
答:有一个片子我自己特别喜欢,并且对于想学纪录片的同学我觉得是很有帮助的。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叫《有熊谷守一在的地方》,这是一部很安静的纪录片,看上去没有什么悬念,也没有很强大的张力,但是它体现了一种独特的生活诗意,以及微小但是美妙的生活体验。
第二个推荐是我在我的影视制作课上会给大家推荐的一本书,是罗伯特麦基的《故事》。这本书首先是一个编剧指南,但是不管是对于虚构的编剧还是对于纪录片的表达都是特别有参考价值的。另一方面,书理论性也很强,给我们展示了人类为什么那么喜欢故事,能够给我们带来文化上的启示。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影像的痴迷停留在一种奇观层面——我欣赏它,把它看作一种完美的表达媒介,然而却始终与其保持着距离,这恰像我的生活,在清华园里终日面对行人匆匆,焦头烂额。
直到梁导的第一堂课,他的第一次作业是以「我」为主题拍摄一组照片。在这堂课上,我们被要求在拍照时和被摄对象进行交流、建立联系,当然也包括与自己的联系。
从那时起我才真正触摸到影像。影像不应该只作为一种技术、一种娱乐方式而存在,它应当成为理解的桥梁。采访中,每每谈及自己喜欢的影像和自己的创作,梁老师总是喜悦而真诚,我想,对他来说,影像已然成为一种生活,他在此流动于田野和课堂之间,用创作和教育实践理想。
文| 蒋一凡
图| 来自受访人
审稿| 童不四言冰
编辑| 李婧轩
matters编辑|邢奕萱
围炉(ID:weilu_flam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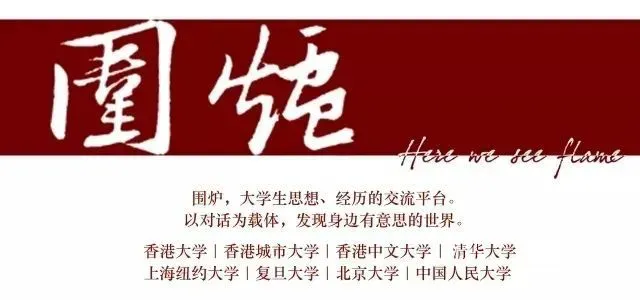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