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一个致力于介绍人类学观点、方法与行动的平台。 我们欢迎人类学学科相关的研究、翻译、书评、访谈、应机田野调查、多媒体创作等,期待共同思考、探讨我们的现实与当下。 Email: tyingknots2020@gmail.com 微信公众号:tying_knots
200 | 阿布- 盧戈德| 女權主義民族志是否可能?
近些年來,性別議題在全球各地均得到廣泛關注。就人類學視角而言,女權主義民族志的理論化、實踐化也得到了更多關注。本文分享的是莉拉・阿布- 盧戈德(Lila Abu-Lughod)於1988 年2 月29 日在紐約科學院人類學部所作的演講,具體探討了在當時語境下,“女權主義民族志是否可能” 這個問題。雖然距離如今已有三十餘載,但其中涉及的“客觀” 與“主觀” 二分法、民族志書寫與理論化、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關係等議題,不僅在當時頗具爭議,在全球聯繫日益加深、學科不斷交叉、科技媒體飛速發展的當下,更是值得繼續探究。
阿布- 盧戈德教授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系,她因其在阿拉伯世界的性別和婦女研究、後殖民理論、文化表達和媒體方面的工作而被廣泛認可。 1978 年至1980 年代中期,阿布- 盧戈德在埃及與來自Awlad'Ali 部落的貝都因人一起生活了兩年半,為她的民族志《遮蔽的情感:貝都因社會中的榮譽和詩歌》(Veiled Sentiments)和《書寫婦女的世界》(Writing Women's World)奠定了基礎。她曾在訪談中提到,“我最初選擇與他們一起工作,是出於對沙漠生活的浪漫迷戀,但當我到了那裡,一切都變了。我參與她們的世界,試圖理解她們的世界,並且傳達她們如何理解自己的世界,特別是通過她們的詩歌和故事。我與她們保持了近30 年的聯繫,有種共同成長和變老的奇妙感覺。” 她還撰寫或編輯了許多性別、媒體相關作品,包括《重塑女性:中東的女權主義和現代性》和《民族性的戲劇:埃及的電視政治》。自9.11 事件和美國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以來,阿布- 盧戈德教授也一直致力於從民族志、性別、經濟、政治等多重視角,打破對於阿拉伯社會的偏見,呈現這一地區復雜的歷史、文化和政治面貌。
原文作者 / 莉拉・阿布- 盧戈德(Lila Abu-Lughod)
原文標題/ 《婦女與表演:女權主義理論雜誌》( Women and Performance: A Journal of Feminist Theory )
原文發佈時間 / 1990 年翻譯/ 王瑋禕校對/ 王菁、馬景超編校 / 王菁
01. 講故事,也講理論
開始這個演講時,我有些惴惴不安,因為我並不太習慣這類演講。人類學家們更擅長用他們從田野帶回來的故事來吸引觀眾。
就我自己而言,我一直得益於在埃及生活時,當時接待我的貝都因家庭給我的東西,包括淒美的詩、有趣的歌、離奇的民間軼事、關於愛情和婚姻考驗的動人故事,以及那些關於死亡和失去的悲劇。就在你要打瞌睡,抓不住我論述的主線時,我就會用其中的一個故事把你拉回來。但講故事不僅是為了這些,我常常通過這些材料來進行理論化的工作,並在談話中保留這種理論與故事的互動性和民族志的優先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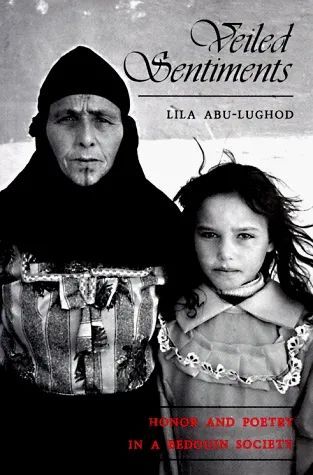
但是,在探討“女權主義民族志是否可能?” 這一問題上,我沒法提供一些故事來讓你保持清醒。我會更多地去考慮一些理論問題,我現在正在寫的書也是這些理論問題的一次實踐。因此,研究的這一方面是沒有故事和民族志的。
而這本書將充滿敘述,就像我所居住的社區裡一位老年女族長會說的那類故事。這位老族長向我生動講述了60 年前,在她還年輕時抵抗婚姻的三個事件—— 她曾哭著並拒絕進食12 天,曾在峽谷前長時間祈禱只希望神靈附體讓她發瘋,也曾用黑色顏料塗滿全身,逃跑到她舅舅家,還把裝滿食物的碗扔出帳篷。
這本書也將涉及避孕和生育的故事。比如有一位婦女,她的大女兒自豪地說,正是因為她踩碎了七個白色蝸牛殼,蝸牛殼裡裝滿了她母親最後一個孩子的臍帶血,她的母親才終於不再懷孕(在生了9 個孩子之後!)。她踩碎了這些蝸牛殼,便可以讓母親不再懷孕;而如果她把它們放在罐子裡埋起來,用浸泡過它們的水讓母親洗澡,母親便可以再次懷孕。
本書也會涵蓋那些在狂熱的掌聲和慶祝的槍聲中會唱的歌曲—— 為了讚美在婚禮上展示的貞操布而唱的歌曲,這代表著女孩的榮譽,以及她父親、新郎和他的家人及到場客人的榮譽。書中也有貝都因婦女對於婚禮的各個方面的詳盡評述—— 從誰來了,到如何安排用餐,以及新娘帶了多少件衣服和多少黃金。這些故事展現了生活在這個電視、廣播、學校和伊斯蘭運動時代的人們身上所發生的複雜轉變,包括貝都因未成年少女對埃及最新的廣播肥皂劇《電腦新娘》的討論。這部連續劇以大團圓結局告終,主人公使用了電腦婚介服務,在被迫嘗試了三位不合適的新娘之後,終於成功地與他所愛的女人結婚。當時,我正和幾個貝都因女孩坐在一起,邊烤麵包邊聽廣播,煙刺痛我們的眼睛,風從沙漠中吹來,雞群嘈雜地互相追逐,這幾個女孩向我介紹了我錯過的劇情。她們講完後,怯生生地問我:“什麼是電腦?”
這個講座無法詳述這類故事。當我們在討論是“女權主義民族志是否可能?” 以及“女權主義民族志可能會是什麼樣” 的問題時,我將不得不談論諸如認識論和表徵(representation)、人類學、女權主義、自我和他者等問題。我將不得不引用許多名字,由於他們來自不同的學科,所以並非為所有人所熟知。你們需要靠自己保持清醒。
我想要論證,我們正處於女權主義和人類學發展的關鍵時刻,這將使女權主義民族志的發展更有可能,也更值得期待。為了論證這一點,首先,我將探討在人類學和女權主義領域中對“客觀性”(objectivity)的批判—— 這種態度也可能被援引來宣布“女權主義” 和“民族志” 無法共存。然後,我會討論人類學的危機和女權主義的危機,正是這些危機使得女權主義民族志項目恰逢其時。
但是,首先要對術語進行定義。若問是否可以有一種專門的女性主義民族志,我們必須先了解民族志的定義。事情已經很複雜了,因為民族志是一個模棱兩可的術語,它既指從事人類學研究,又指這種研究的書面成果,現在,這種文本或民族志被認為是一種獨特的半文學體裁。我暫且擱置女權主義的定義,這不僅是因為我們都對它有一個粗略的概念,也因為女權主義這個術語太有爭議,若要定義它就會立刻陷入麻煩。
我們問“女權主義民族志是否可能”,就是在問女權主義對人類學的研究和描述其他文化社群生活的寫作會帶來什麼改變。考慮這些問題,就需要我們重新思考客觀性問題。若客觀性是人類學研究和寫作追求的理想,那麼主張一種女權主義民族志就是在主張一種有偏見的、有興趣偏向的、片面的、且因此有缺陷的研究項目。客觀性在社會科學領域中是一個令人肅然起敬的問題,而且人類學對它有著自己的看法。我會先談談人類學領域的“客觀性” 問題,然後再概述女權主義理論家在思考客觀性方面的突破。對她們而言,認識論一直是大量理論研究的顯要關注點,她們在客觀性的大本營—— 科學本身—— 中試圖應對了這個問題。
0 2. 反思及文本人類學
不知為何,女性主義民族志的前景似乎並不像女性主義政治學或女性主義經濟學的想法那樣令人震驚。沒有多少人會對此發出驚呼。在某種程度上,人類學有著悠久的文化相對主義傳統和關於多重真理的概念,而這也意味著人類學中已經隱含了對客觀性學說哲學基礎的批判。
但是,在過去二十年裡,人們對客觀性的可能性提出了更明確的質疑。這與其說是來自知識社會學,不如說是來自闡釋人類學,而知識社會學在其他領域中對知識的客觀性的顛覆更為有力。在闡釋人類學中,克利福德・格爾茨(Clifford Geertz)提出了“文化作為文本” 的隱喻及其著名的推論,即人類學“不是一門尋找規律的經驗科學,而是一門尋找意義的闡釋科學”。 【1】這為當下流行的、人類學對客觀性批判兩個最重要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一個是對田野察過程中反思性的關注,另一個則是對書面表達中的文學性關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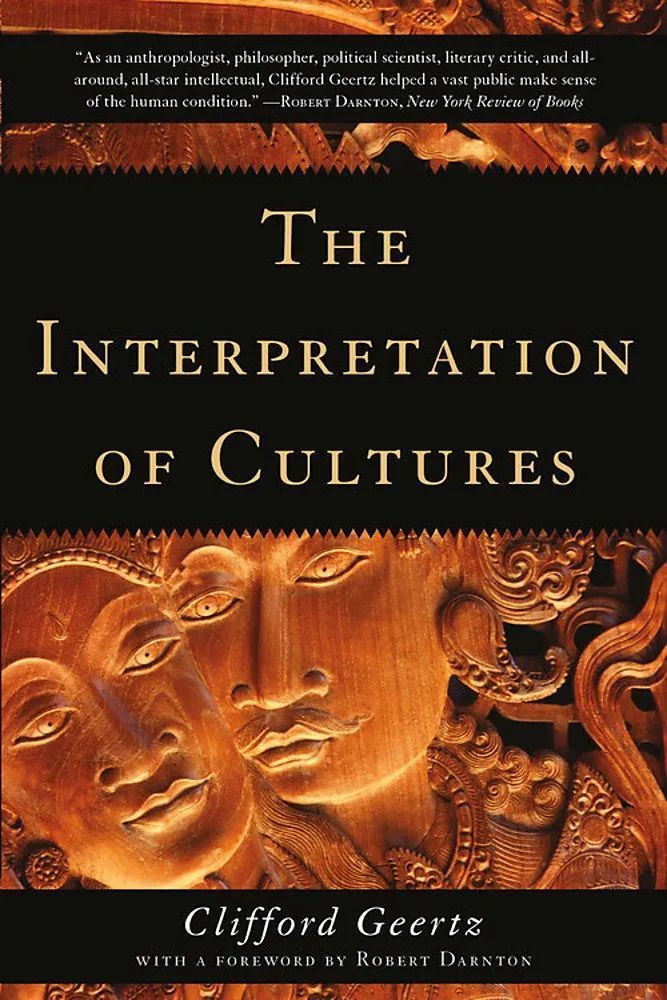
以反思人類學為評測標準的那些作品,關注的是在田野中得到的所謂“事實” 如何通過在特定社會和文化背景下,人類學家與特定個體的私人互動構建而成。這類研究的主要人物有溫森特・克拉潘扎諾(Vincent Crapanzano)、讓- 保羅・杜蒙特(Jean-Paul Dumont)、凱文・德懷爾(Kevin Dwyer)、保羅・拉比諾(Paul Rabinow)和保羅・里斯曼(Paul Riesman)。儘管方式不同,這些學者都把田野調查的相遇看作主體間生產出“事實” 的所在之處。 【2】作為人類學家,如果我們是通過情感上極為複雜、交流上十分模糊的社會相遇來獲得相關的田野知識的,那麼必然不存在什麼客觀性,人類學也不應該被比作科學。
第二波對客觀性的批評風潮角度稍有不同。格爾茨的出現還讓人們逐漸意識到,人類學家實際做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寫作。從民族志寫作的文學傳統來看,一些人類學家指出,現實主義和體現客觀性的透明化語言被用來維護了經典民族誌中敘述者及人類學家的權威。在此,人類學敘述的構建方式至關重要,並且這些構建方式和民族志作者與研究對象之間的距離以及不平等的關係緊密相關。 【3】
克利福德在《寫文化》的導言裡寫道,也許作者本人意識和控制之外的因素,才真正塑造了民族志寫作和描述的種種方式。他寫道:“民族志寫作至少由六種方式所決定:
(1)語境上(它取材與充滿意義的社會環境,並創造有意義的社會環境);
(2)修辭上(它使用有表現力的常規手法,也被後者使用);
(3)體制上(寫作既處在特定的傳統、學科和觀眾讀者之中,又對立於所有這些因素);
(4)一般意義上(民族志通常區別於小說或遊記);
(5)政治上(表述文化現實的權威的分配並不平等,有時也有衝突);
(6)歷史上(上述所有常規和限制都在變化之中)。 ”
這顯然是在說,所有民族志都是情境性的,沒有一個是對現實簡單客觀的表述。 【4】如克利福德所說,這些決定性因素” 支配了內在一致的民族志虛構的撰寫”,然而絕大多因素還未被系統地探討過。 【5】大多數的自我意識是關於文學傳統的(以上第二點和第四點),並導致了一些關於(文學)形式的有趣實驗。另一個流行的解決方案是引入對話體(dialogical)或多聲部(polyvocal)的民族志。這種民族志旨在文本層面上去殖民化,清楚地體現出敘述者/ 人類學家的聲音只是眾多聲音中的一個,並使研究對象的聲音也能被聽到。
在這種對作為文本的民族志的批判中,認識論的問題(即我們如何認識的問題)和我們如何表述的問題被迅速地混為一談,某種程度上迴避了人類學最核心的基本政治問題—— 來自西方的認識者和表述者,以及非西方的被認識者和被表述者。這是一個有關自我和他者、主體和客體的問題,我之後將回到這個問題,因為它與性別和女權主義民族志也息息相關。
03. 女權主義理論和“客觀性” 問題
另一方面,對於女權主義理論家而言,性別、方法、理論和描述之間的關係一直是跨學科研究的主題。持續至今的第一波女權主義浪潮指出,對許多現有理論和知識的非難,往往說的是它們並不是真正的客觀或不夠客觀。
學者們指出,在對社會和文化生產的研究中,女性是如何被忽視的,他們也指出,通過提出或迴避某些特定問題,以致於忽視了性別或女性的存在。在科學研究中,那些支持性別差異和女性劣勢論的流行假設的有效性開始受到質疑,並被指責為“壞的科學”。在多數研究領域中,記錄下因男性中心主義而扭曲的研究是相當重要的,對它們進行糾正的相關研究也同樣重要。 【6】
學者們批評現有的學術是帶有偏見的,而女權主義學術研究的目標是完善記錄,並通過納入女性的生活、經驗、文學和藝術等,使理論更客觀、更完整,並且更有普遍性。在這種表述中,對客觀性的追求仍然是毋庸置疑的,而其反面則被認為是偏見或偏袒。 【7】
第二波女權主義對客觀性的批判從另一個不同的角度出發。她們對客觀性進行了多方位批判,也同時批判了“客觀” 與“主觀” 二分法,而客觀性這一概念的意義正是通過該二分法而來。由此,女權主義者開始將辯論的重點從傳統的擔憂,即“客觀性的局限”(多少帶有一種將客觀性作為理想的傳統科學假設),轉向了對客觀性概念本身的地位和價值更徹底的質疑。
在這一思潮中,由於在社會科學領域,將客觀性作為一種理想或是切實可行的可能性始終具有爭議,因此第二波女權主義中最猛烈和最激動人心的部分並非來自社會科學,而是來自自然科學的哲學或歷史。之所以如此強而有力,是因為科學似乎是客觀性理想最堅不可摧的地方,而且對認識主體和研究對象之間的區分也是最明確的。女權主義理論家指出,科學所謂的客觀性不僅是性別化的二元論的一部分,也是一種權力的模式。一些觀點認為客觀性的概念應該被廢除,另一些則認為這一概念應被重塑。
我來舉個例子讓大家體會一下。伊芙琳・福克斯・凱勒(Evelyn Fox Keller)提出過一個有趣的觀點,即客觀性的定義來自於它與主觀性構成了一組概念。而在我們的文化中,這種二元論與性別的二元論是相互呼應的,也就是說客觀性與男性氣質相關聯。 【8】一系列被認為是陽剛的特徵,正是因為和“感性” 對立才成立,就像精神相對於身體,疏離和非個人的相對於個人興趣和參與—— 這種關聯性使得科學的威望與男性氣質的主導地位互相都得到了增強。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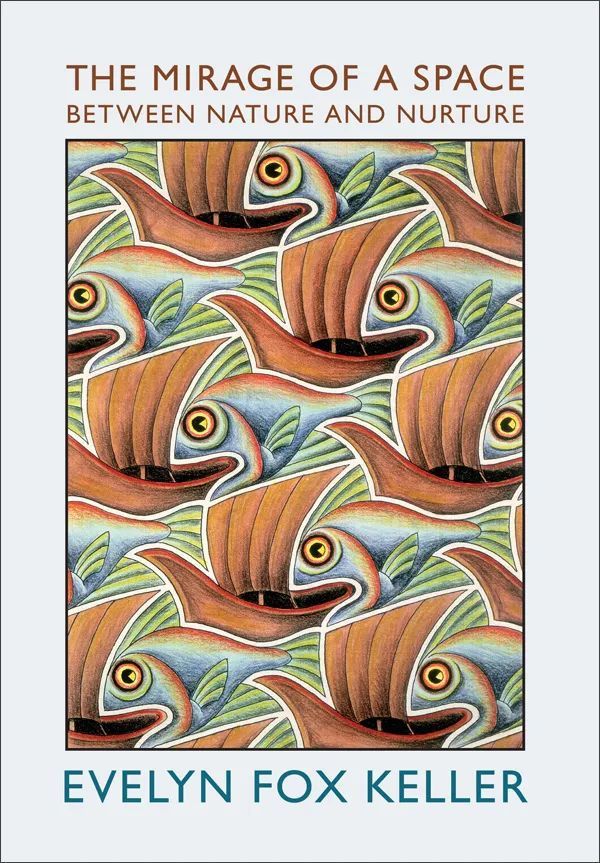
凱勒還提出,她所說的科學中的客觀主義意識形態,是通過一種自我選擇的方式進行自我再生產的。她認為,科學吸引了那些共有特定價值觀的人,或至少其自我形象與這些價值觀一致的人—— 主要是男性。此外,她還提出了一個更偏向推測性的心理動力學論點,即一些人的嬰幼兒經驗使他們覺得科學事業所承諾的疏離感和邊界的清晰感對他們來說十分舒適—— 同樣,大多數是男人。
她的論點還有很多。然而,在我們這次講座中,我想指出的是這種文化解釋是多麼具有說服力。只要想想科學中主體和客體之間關係的兩個軸心—— 認識者和被認識者的地位,以及他們之間的關係—— 你就會得到像主觀/ 客觀、有偏見/ 無偏見、個人/ 非個人、被認同/ 被疏遠、局部/ 普遍、特殊/ 一般、有意思/ 無價值、情感/ 理性等等這樣的對立。這些都與“女性氣質/ 男性氣質” 有關。然後,我們就能得到作為一種主體/ 客體關係意義上“科學/ 自然”、甚至是“人/ 自然” 的關係,畢竟這其中的“自然” 總是與女性相關。
凱勒希望能保留“客觀主義”(objectivism)與真正的“客觀性”(objectivity)之間的區分。她認為,客觀主義是科學的意識形態,而不是對科學實踐的描述。然而,從凱瑟琳・麥金儂(Catharine A. MacKinnon)到多蘿西・史密斯(Dorothy Smith),這些更激進的女權主義者則不會接受這種區分。
麥金儂是最激進且飽受爭議的女權主義理論家,她的理論涉及了客觀性如何在像我們這樣的、在根源上是以性不平等為結構的社會中發揮作用。她認為,客觀性主要是男性權力的一種策略,而不僅僅是一個通過與男性氣質相關聯而被賦予文化意義的概念。她提出,“女權主義不認為自己的觀點是主觀的、片面的或不確定的,而是認為這是對過去說法中所謂的一般性、無私性和普遍性的批判…… 女權主義不僅挑戰了男性氣質中傾斜的天平,而且進一步質疑了普遍性要求本身。女權主義揭示出無視角性(aperspectivity)是男性霸權的一種策略。”【10】她認為,男性總是占主導地位,從他們的角度、尤其是物化女性的角度創造世界,然後採取了某一種認識論的立場,也就是客觀性,以符合他們所創造的世界。
麥金儂經常因為她指責男性理論家的全面化傾向而受到指責,她在關於“女性受壓迫的根源在於男人的性統治” 上,表現出的普遍主義和非歷史性的論點必須謹慎看待。然而,她對客觀性和統治相聯的直覺,在社會學家多蘿西・史密斯的工作中得到了更細緻詳盡的支持,史密斯論證了客觀性、社會學話語、男性和統治機構之間的親和性和關聯度。通過把分析限制在一個特定的學科和社會領域中,史密斯把她的論點建立在了具體的細節上。她認為,社會學的議程和領域都是“建立在男人的工作世界和關係上的,他們的經驗和利益在參與這個社會的統治機器的過程中產生。社會學的公認領域—— 組織理論、政治社會學、工作社會學、精神疾病社會學、偏差等等—— 都是從專業、管理和行政結構的角度以及從他們的觀念出發來定義的。” 【11】她接著指出,社會學的理想視角—— 科學的、客觀的、阿基米德式的—— 與社會學家參與統治機器有關。她寫道,“社會學的獨有特徵是通過懸置認識者實際的、特定的位置,從而來反思社會、反思社會關係、反思人,這種學科傾向必須結合學科自身所處的地位來理解…… 這是一種局部的視角,起源於社會中佔一種特殊的位置的人。”【12】這個視角來自上層和占統治地位之人,至少在現代西方社會,這種地位主要被男性佔據。
麥金儂補充道,這種視角不僅僅是對男性作為支配者、統治者或管理者經驗上的反映,而且就是他們統治的有效工具。她指出,“如果兩性確不平等,而視角僅參與到了其中一種情況,那麼就不存在所謂無性別的現實或無性別的視角。而且,這一切都是相通的。在這種情況下,客觀性—— 無定位的、普遍的立場—— 無論是聲稱的還是所追求的,都是對性別不平等的存在或不平等程度的否認,且沉默地參與了主導觀點構建現實的過程。”【13】
由此,女權主義學者對客觀性批判主要有兩類回應方式。一些人譴責了客觀性概念,並探索女權主義是否可能創造出一種替代性方案。這些當中的許多人承認了主客二元論中先前被貶低的主觀性的價值,提倡建立一種新的主客關係—— 強調關係而非距離,平等而非支配,依存而非疏離或無關利益關係。
另一些人或許太過清楚這種態度只是將等級制度頭尾倒置,其背後仍然保留了性別二元論。換句話說,以上僅僅是一種對傳統上女性氣質的重估,沒有去挑戰使等級制度存在的二元論。因此,後者強調批判中暗含的另一個意義,這些學者的觀點建立在傾向性(partiality)的基礎上,認為所有的知識都是有傾向性的,都是某種視角的具象。他們希望重新認識並定義客觀性,使之恰恰意味著“情境觀點”(situated view)。他們會認為,沒有什麼研究是不置於某種情境之中的。女性的觀點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具有特權的,因為就像任何庶民觀點一樣,我們無法假裝它是一個沒有來源的觀點。
作者註釋

阿布- 盧戈德教授對本文的介紹:
這是我於1988 年2 月29 日在紐約科學院人類學部所作的演講,內容略有修改。演講是學者們經常進行的一種獨特的表演形式;儘管有缺點,我仍決定將這篇演講原樣保留。自從發表了這篇演講,我重新思考了很多問題。關於女權主義者們和halfies 的共同點,和她們對於人類學有何啟示,我在《反“文化” 的書寫》(Writing Against Culture)一文中進行了更多討論,收錄於Richard Fox 編輯的《介入:當下人類學》(Interventions: Anthropology of the Present;校注—— 此書後來出版時題為Recapturing Anthropology: Working in the Present)。我感謝NEH(國家人文基金會) 的研究經費,使我能夠於1987-88 學年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進行研究,也包括為這次演講所做得準備。我受益於性別研討會的討論,來對這些問題進行進一步思考。我也感謝Cathy Lutz 的評論,以及Connie Sutton 和Susan Slyomovics 鼓勵我將這篇演講以更永久的方式發表出來。
譯者介紹
王瑋禕,古鎮人,在日本讀人類學,愛好小鳥和野生三色堇
校者介紹
馬景超,哲學系博士在讀,現居美國費城
王菁,喜歡沒有(以及看起來沒有)脊椎的海洋生物,人類學視角的跨學科研究和公共對話
本譯文受作者本人授權,若要轉載,請在本平台留言,或者郵件聯繫。
Posted in 世界人類學, 中東, 公共人類學, 性別, 編譯
最新文章(持續更新)
194. 小鎮做題之後? | 弗雷勒的地平線(V)
196. 書訊| 英文人類學新著| 2021 年11-12 月
197. 發明“瘋癲”:現代中國的百年“精神病史”
198. 爪夷文:馬來西亞現代性之症
199. 教與學|訪談張巧運:做人類學老師,在沒有人類學的地方
200.阿布- 盧戈德| 女權主義民族志是否可能?
歡迎通過多種方式與我們保持聯繫
獨立網站:tyingknots.net
微信公眾號ID:tying_knots
成為小結的微信好友:tyingknots2020
我們來信、投稿與合作的聯繫地址是:tyingknots2020@gmail.com
喜歡我的文章嗎?
別忘了給點支持與讚賞,讓我知道創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發布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