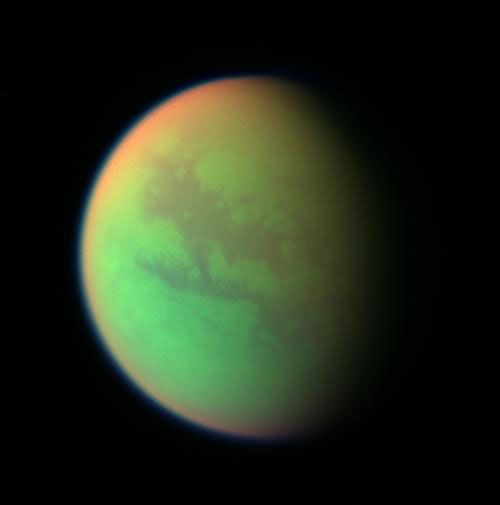
Volo ut sis.
回归
「拜拜!」离开机舱之际,空服员对我招手。
「拜拜!新年快乐!」我补了一句。
「新年快乐!」她回过神来,似乎意识到了当天是2022年的最后一天。
「新年快乐!」站在旁边的男性空服员也补充了一句。我率先踏出机舱门,一路疾走了十几分钟来到边境检查,官员把旅行证件递给我,我跨过那条用黄色油漆标示的但又无形的线,又径直朝行李运输带走去。那也许意味着这19天的独自旅行的结束。
旅行在历史中的角色,无论是私人的还是能载入著作的历史,类似于一些星体。我从地球上观察这些星体瞬间的光芒,但星体本身大概早已消亡。提取行李的我正处在星体本身消亡的那一刻,但爆炸产生的光芒才刚刚开始它的旅程。上次旅行(我认为旅行必须满足「独自」和「跨越国境线」两个条件)是从中国东北陆路前往俄罗斯远东。在这三四年间,世界的本体乃至是作为概念的「世界」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一些人依然试图用暴力和意识形态垄断其他个体看待世界的视角,这些个体要么自愿要么被迫接受了这种带有些许历史实证主义意味的世界观。
我个人对「旅行」的定义基本没有改变:旅行依然开始于念头产生的一刻;旅行依然不存在「结束」。回归不是结束,它甚至只是开始的一部分。然而旅行不能没有回归(于我而言暂时如此),没有回归的旅行叫做流亡。不过旅行可以被称为短暂的自愿流亡。回归是一种力,把人拽回原来的生活或世界中,并强迫旅行者理解世界的差异:写字楼里的生活与德里贫民窟的生活都没有脱离生存的基础,但旅行者固然会更注意到差异而非基础:「我这样的才叫生活;他们连喝的水都不干净,能活下来已算万幸」。而流亡者眼中的世界是均质的——回归的力消失,他们得以不受限制地进行移动。当然,这不意味着旅行比流亡要好,毕竟流亡者写出的佳作不计其数;更不意味着流亡比旅行要自由。
「今天为各位服务的机组人员来自18个国家,会说17种语言。」阿联酋航空的机长广播如是说。他尝试打消乘客对基于语言障碍而要求服务的惶恐,展现公司对多种文化的包容。从杜拜前往伊斯坦堡的航班,机长广播也讲了类似的内容:「机组人员来自16个国家,会说15种语言……机长名叫艾哈迈德,来自埃及。」
在出发前正好一个月,伊斯坦堡的独立大街发生恐怖袭击,6人遇难,81人受伤,为此我获得了许多朋友的告诫。我惶恐了两三天,但没有对旅行计划做出任何更改,尽管来到伊斯坦堡后的我,依然没有(勇气)走进独立大街。我仅站在塔克西姆广场,即独立大街的尽头,望向大街里的人海——那儿迅速恢复了往日的生动,只有零星防暴警察持枪巡逻,提醒人们潜在的危险;价格比非游客区略贵的旋转烤肉商贩不受干扰地进行交易;而我十几分钟前刚在附近的塔迪姆(Tadim)餐厅饱餐一顿,那碗价廉物美的辣椒牛肉汤令我终生难忘。
降落后,在步行进入尼什(Niš,塞尔维亚第三大城市)机场航厦处便是护照查验。由于只有两条队伍,坐在房间里没事干的多余的官员便走出来随机检查护照。塞尔维亚边防会仔细翻阅外国护照,检查里面是否有科索沃的出入境盖章。由于塞尔维亚将科索沃视为其领土的一部分,任何不经由塞尔维亚领土入境科索沃的行为(如从阿尔巴尼亚/北马其顿经陆路或由其他地区乘飞机抵达科索沃)将被视为非法入境,官员会在这本护照的科索沃出入境章处盖上「撤销」。
从房间里走出一位官员,礼貌地向我索取护照,检查内部的签证与盖章。而一翻到护照中间的美国签证,她的神态发生了变化,开始详细的问询:
「您来塞尔维亚是什么目的?」
「旅游。」
「您会待在尼什吗?」
「是的,待到后天。」
「您什么时候离开塞尔维亚?」
「26日。」
「也是从这个机场走吗?」
「不是,我之后会去贝尔格勒,从那里的机场飞回伊斯坦堡。」
「好的,谢谢。」她递回我的护照。在我把护照交给前方窗口内的另一位官员核查身份时,同样的检查科索沃盖章的流程又重复了一遍,不过窗口里面的官员没有注意到美国签证的存在。
在尼什的第二晚,朋友嘱咐我千万小心,巴尔干可能会再度爆发战争。我一时感到十分费解,在网上搜索后才发现塞尔维亚和科索沃的冲突再次(因为一些常人无法理解的小事)加剧,即便我从窗外望到的人们依然在以合理的步速走路。欧洲小城晴朗祥和的气氛似乎抵抗着那些荒谬的传言。我是否有在尼什陷入惶恐?也许有,也许没有。但是几天前我站在伊斯坦堡独立大街的尽头,对恐袭的惶恐已经消散,或者已经无畏。因为我就站在那儿,在共和国纪念碑下,与所有人,那些早已摘掉口罩的多样化的个体一道,用参差多态的真实重构着仍在经历阵痛的世界。
我坐在贝尔格勒的塔马登公园(Tašmajdan,旁边就是圣马可教堂)的某张长椅上,一口酸奶,一口从附近糕点店买来的芝士布雷克酥饼(Burek)。我面前踉踉跄跄走来一个小男孩,拿着玩具枪,向我喊「砰」。我也用拇指和食指向他比了手枪,喊「砰」。他的母亲立刻跑来道歉,并把孩子抱走。我长期以来认为塑料枪是最糟糕的玩具,因为它正在阻止孩子理解现实世界伦理问题的复杂性。暴力不能解决问题,问题也并非只有好坏或正邪两面。
在中文大学的头两天,我旁听了两节课,分别是人类学系和哲学系的课,主题都关于「伦理」。人类学教授说:「对于伦理,人类学家不去评判,不会尝试建立一种普遍的标准。」她警告课上带有哲学背景的学生,她随后可能会对康德作出十分不公允的评价。哲学系的教员则说:「我们试图建立一种普遍的伦理规范。」但他们在讲课的过程中都提到了电车难题,并强调:「电车难题不过是一个对现实高度抽象化的模型,我倒希望我的生活像电车难题一样简单。」
我记忆的气力都集中于这19天,以至于2022年的其他月份自己做了什么都被不幸地被抛之脑后。也许是站在一种反对线性叙事的角度,这次旅行我选择了「回归」作为游记的序幕。之前阅读过一本人类学的书籍,作者质疑人类所谓的「发展」是否是倒退的:人最高级的阶段在山洞里啃树皮;而最原始的阶段是生活于科技无处不在的社会中。这19天内,我似乎平安地与恐怖袭击、可能爆发的战争以及病毒感染擦肩而过,但我仍在绞尽脑汁理解着那些猝不及防的荒谬所带来的狐疑、死亡和泪水。世界也许正是如此,没有那么简单。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