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虛無中誕生︰探索文學邊界。香港文學館經營網上發表平台「虛詞」、實體紙本月刊《無形》。 香港文學館有限公司由一群香港作家及學者組成,並設立香港文學生活館。常與大學、藝術單位合作,策劃各種文藝活動及展覽。 linktr.ee/houseofhklit
【2022诺贝尔文学奖】书写是死与生的创造──安妮.艾诺《Happen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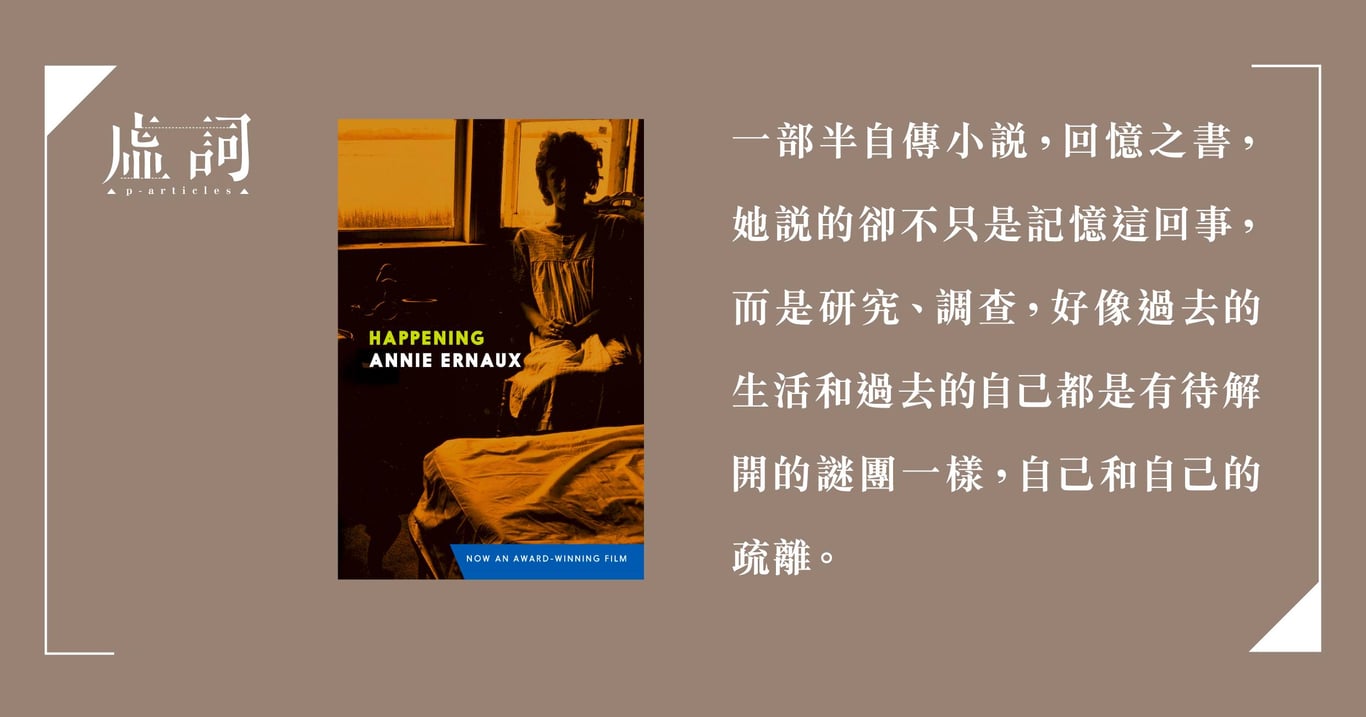
( 原文刊载于虚词・无形)
文| 黄柏熹
一、
“I want to become immersed in that part of my life once again and learn what can be found there. This investigation must be seen in the context of a narrative, the only genre able to transcribe an event that was nothing but time flowing inside and outside of me.” (19)
这是安妮.艾诺(Annie Ernaux)写在小说《Happening》(L'événement,中译《记忆无非彻底看透的一切》)前言的句子。一部半自传小说,回忆之书,她说的却不只是记忆这回事,而是研究、调查,好像过去的生活和过去的自己都是有待解开的谜团一样,自己和自己的疏离。当我读到「nothing」这个字时,不知为何内里感到分外难过,一下踏空,或是面前明明有字但妳在内里把它念出来的时候,妳觉着一种虚无。她所说的「时间」。所谓创伤就是,时间不是线性或可量化的姿态,而是在一个人的身体里来回翻滚,意义在事件框架的里外始终拿不定主意,碰上言语之际又总是说来话长,不知道应该从何说起。
就像当妳以载满情意的眼神凝视着我,我听见风在窗户上猛撞的声音,但我不敢直视。或当我直视,就必须以身体为代价。重探过去必须是一趟以生命为载体的冒险,妳底赖以存在的根本,它要经得起痛和彻底翻转的可能。
二、
我是看完那部在威尼斯电影节得奖的改编电影后,才回个头来读艾诺的原著小说。撇除若干情节改动,或许是出于戏剧性的考虑,电影相比小说更像一个「完整」的故事,围绕着戏剧发展、声影、镜头调度和角色的建构,提供一个在叙事结构中得以完满结束的过程。而小说,正如艾诺所言,是以「叙述」(narrative)为目的,让记忆和回忆的过程──包括所有迟疑和内心挣扎──都得以被赤裸呈现的书写。赤裸的意思是,它总是分心和分裂的,这边厢以冷静的口吻叙述往事,那边厢在剖析回忆之于自己的意义和其不可能性,突然停顿又重新开始。
我无意在这里比较电影和小说的呈现手法,也不是要比较其高低。我的意思是,两者本来就基于截然不同的目的,才会出现相异的表现形式。我会这样形容:艾诺在小说里的书写是一种纯粹的书写,或一种僭越的书写;她写,不是为了迎合任何故事结构或外在目光,而是不得不写,在秘密和禁忌的樊篱前,不得不去僭越,唯有形塑成字才能从中确认身体的存有,才能爱抚,或触碰,那个被埋藏在内里的自己。
文字,在这里成为身体一样的物质存有。妳必须说,才能在场。
三、
什么身体?一个被父权法规加以禁制,透过禁止堕胎使女人在自己内里异化成物的身体。身处严格管制堕胎的法律随时从历史灰烬中重燃起来的现世,我几乎是抖颤着写下这句句子。
在被管制的身体之外,却是艾诺笔下一个又一个在她之前或紧随其后的,一个又一个透过不同方法尝试终止怀孕的女人。小说里的叙事者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时间不是线性或可量化的姿态,它回来,又再回来)。
我记得,改编电影的镜头常常以一种逼近的距离紧随着主角Anne的女体,譬如母亲用身体来量度她的体温,譬如好几次看到胸围肩带留下的印痕,譬如淋浴间里,赤裸女体之间的距离和互为凭证,或房间里的自慰和情欲探索。电影没有离开过Anne,也没有离开过身体,一切痛苦与快慰都源自这里,身为女人,身体是给予也是抑压所在。
小说也一样写到身体,写到她的欲望和恐惧。艾诺在小说里写,“When I made love and climaxed, I felt that my body was basically no different from that of a man.” (16),性欲的充盈,俨如一个没有区别、没有言语的伊甸乐园。但意外怀孕让她看见作为一个女人,或女人作为众数的命运,如果没有终止怀孕,在工人阶级背景加上年少怀孕和社会污名加诸的恐惧中,她,会成为一个怎样的女人─ ─或许就是一个这边厢把孩子安抚进睡,那边厢又得为客人奉上晚餐的家庭主妇。没错,我们仍是必得重提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的名句。她不是活在自己的性欲里,而是在法律和恐惧中「成为」一个女人的。
四、
所以她写。写有时是一个倒转的过程,把铭刻在身上的言语倒过来写,人才能拥有自己,或至少掏出一点空间。毁坏是一种创造。
她会写到昔日在日记中写下的文字,如果文字以物质的形式保存着一个有待考掘的自我。她说,重读自己的日志,她发现过去她只会称呼肚腹里的东西为「it」或者「that thing」,只有一次写到「pregnant」。她觉得没有必要为一个不会在未来发生(而她急欲脱离的)事命名。她又写到,在一次跟男性医师会面的过程里(那一次她希望他可以在终止怀孕一事上帮助自己),两人在整段对话中完全没有提过「堕胎」(abortion)一字,仿佛它在语言中根本没有位置。
──如果语言不只是机械性的运作原则,而是因应使用者的意愿而得以隐没或无名。如果语言因为禁忌而在我们之间扩展成为一个黑洞。所以妳写,所以妳說。
艾诺在书的前页引用了超现实主义作家Michel Leiris的句子:“I wish for two things: that happening turn to writing. And that writing be happening.”。如果书写不只是对语言的运用,而是创造语言。如果唯有透过书写,人才能抵达自己。与其说《Happening》是有关一个在禁止堕胎年代,勇敢面对世界并得以实现自己的女性,不如说小说书写本身就是一个「成为」的过程。书写总是「正在发生」的,不是先有一个完整的真理在她面前等待,没有应许之地,没有流奶与蜜,而是一次又一次,通过回忆,通过与文字碰撞(而不至心碎),我得以成为我、拥有我、亲吻我。去写就是把整个身体交托出去,是创造,是重新讲述自己。
或换句话说,去写就是自由得以实现的物质条件,把无物换成礼物的神圣时刻。 「我」因为书写而得以存在。
五、
小说《Happening》所包裹着的,其实是一种生死的倒置,或词义转换。
其中一个现在仍然盛行的反对堕胎理由,是把终止怀孕等同于剥夺生命。在小说里,当艾诺写到那个替她秘密施行堕胎手术的年长女士,把冰冷的医疗用具伸进她的两腿间时,她形容是“is giving birth to me” (53)。被等同于杀害的手术在她笔下倒置成重生的契机。她又紧接着写,“At that point I killed my own mother inside me”。直接挪用一个掀起争议的词汇,却把一整个意思翻转过来。
「母亲」的意思未有在她笔下被确认下来,俨如将解未解的一词多义。谁是「我的母亲」?是指那个在战前年代出生,在压抑和羞耻的性文化中成长的,她的母亲?抑或是那一个以生育为核心的,负责给予爱给予照料的母亲形象?又或是一整个把她复制再造的性别矩阵,现在她得以告别过去,重塑自我?她没有写明,她在这里留下一个可供解读的密码。她只是一再提到她觉得那位替她做手术的女士很像她的母亲,在血脉之外,为女人自己创造可能性的阴性连结。
而连结就是创造的意思。
后来,她会写到自己在大学宿舍的房间里,跟另一名女生一起剪去脐带,继而大量出血被送到医院。她会再一次挪用生与死的语言,形容她的房间,自己的房间,“I had given birth to both life and death” (69)。她这样为自己的回忆作结,为自己的书写作结,为自己讲述自己,因为书写她的生命得以展现,得以重生。禁忌不再是禁忌,死亡被翻转成重生,父权律法在女性叙述的复写/重写下,生命或语言的主权得以被重构,改变在发生的当下发生。正如她在小说里写,终止怀孕使她更懂得折磨和牺牲是生育必要付出的代价,因为更懂得才能作负责任的决定,从「选择终止」生出「接受生育」的可能,到底也是一种转换。
一切始于书写,终于书写,亦系于书写。
一切可能的。
六、
发现自己怀孕前,她本来有一份大学论文还未完成,主题是有关女性在超现实主义写作里的角色。在小说结尾,她提到终止怀孕的经验──穿过生死、时间、法律、道德和禁忌,甚至席卷身体的经验──使她前所未有地接近这个论文主题。但她的经验无法转换成整全的意念或理论化的辩证,而是如梦一样的视角,没有形状的概念,一种「wordless intelligence」,或未知或未被发现的言语。在禁忌和剥削的文化里,试图去言说那些僭越的经验,不正正符合超现实主义那革命性的创新精神吗?
而言说,就是构筑身体本身。意思是,任何书写,最终都是一种生命书写,一种意志的展现和交托。唯有身处如海浪般的叙述中,自我才得以显露(unfold)。这种自我不是自我沉溺的人格,而是通过自我考掘,展现或预视生命的可能性;正如艾诺在最后几番提到,她仿佛是走到一个女性的前沿地带,未来的世代将会比她走得更前。
很喜欢她写在小说最后的句子,是为记──
“Among all the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reasons that may account for my past, of one I am certain: these things happened to me so that I might recount them. Maybe the true purpose of my life is for my body, my sensations and my thoughts to become writing, in other words, something intelligible and universal, causing my existence to merge into the lives and heads of other people.” (75)
參考書目: Ernaux, Annie, and Tanya Leslie. Happening. Fitzcarraldo Editions, 2022.虚词・无形网站
虚词・无形Facebook
虚词・无形YouTube
虚词・无形Patreon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