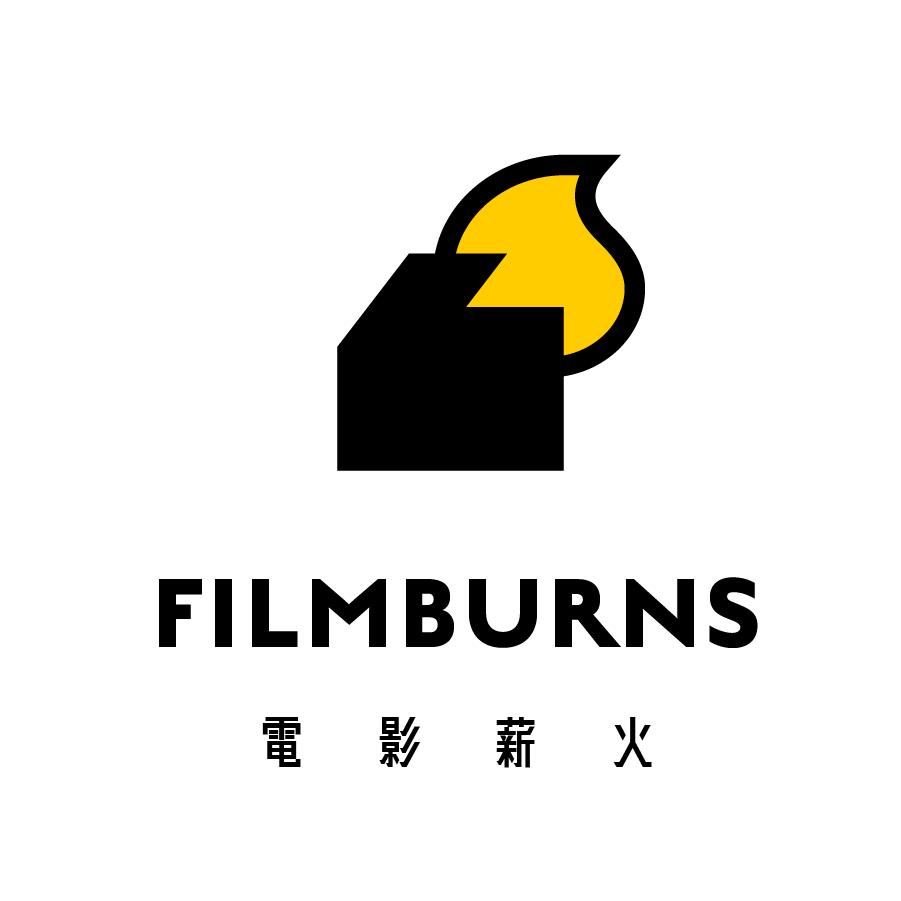《長夜盡頭的微光》:心之科學

文|安娜
日本導演三宅唱新作《長夜盡頭的微光》(下稱《長夜》)給我最強烈的感覺是,這是一部「減法」的電影,這是一部充滿省略,以否定作為肯定的電影。比起三宅唱之前備受好評、以聾啞女拳手為題材的《惠子的凝視》,《長夜》從兩個相濡以沫的邊緣人拓展開去,旁及周遭稟性不一的人,頗有以群像形式側寫社會面貌的意圖。《長夜》格局更為開闊,風格調子上比前作更為簡煉而統一,同輩好友導演濱口龍介甚至形容此作是「介乎非常年輕和成熟之間」。

電影改編瀨尾麻衣子的小說(小說和電影原題為《黎明前的全部》),講述患有 PMS 經前症候群的女生藤澤,以及有驚恐症的男生山添,因為無法適應大都市常規上班族的生活,輾轉之間,兩人都來到近郊、以生產天文玩具的「栗田科學」上班。藤澤和山添雖然都是年輕男女,但電影並沒因為安排他們俗套地互生情愫,發展愛情線。藤澤與山添起初彼此都有距離嫌隙,例如藤澤會因山添不停地開梳打水所製造的聲音而心中發毛,山添倒會因為藤澤買和菓子餽贈同事的行徑而感到不屑。兩個異常敏感脆弱,但內心柔軟的人,在故事推展的過程中,因為一點一點的小事而慢慢靠近,逐少逐少的向對方敞開自己(其中最精彩、最令人難忘的,莫過於藤澤主動請纓為山添剪髮,卻笨手笨腳的把他髮型搞砸了)。藤澤和山添最後合力完成了天象投影的節目,向社區鄰里介紹無邊星際的奧妙和魅力;兩個被主流社會排拒的人,結果各自運用自己的能力(藤澤的朗讀演繹、山添的資料搜集和撰稿),將無形、看似微不足道的感動和微妙感情帶給願意傾聽他們的觀眾。

三宅唱在《長夜》中其中一個非常貫徹的做法,就是要「去戲劇化」。這不僅限於對藤澤與山添二人之間的關係的描寫。電影雖然開宗明義講明兩人都受某種症狀困擾,但同時間電影也非常克制地不去渲染兩人的病徵。藤澤雖有失控情緒發飈的境況,但也只限於電影初段偶爾發生。山添的驚恐症也呈現得十分低調,完全沒有在其他電影中會看到那種激烈失控的陳套。電影中有寫及山添有一個益發疏遠的女友,這女友最後一次現身,是在山添家門前,說她要對外地工幹了,想和他說清楚。電影只寫到這裏就剪到下一場戲,沒再交待下文。編導大概覺得這樣已經足夠讓觀眾知道事情的前因後果,同時也不想走入任何會傾向戲劇化、有高度情緒發生的處境。這一種淡然自若,看似若無其事,是《長夜》明顯苦心經營的方向。這不失為一種有趣的嘗試,但在電影中的體現,我並沒有覺得很成功。
三宅唱摒棄了戲劇化的鋪排,也沒有顯著的形式,似乎想以一種最接近平素、真實的生活感取而代之,作為全片的跳動脈膊。這樣的願景相當理想、相當美好,但同時也似乎是像登天一樣難的任務。飾演藤澤的上白石萌音和飾演山添的松村北斗都有高水平的演出,兩人互有錯落磨擦的表演對碰,為電影製造了不停變化的節奏感和驚喜;月永雄太的 16mm 菲林攝影也是賞心悅目,有一種巧心琢磨的工藝品的質感。不過這些都不能夠很有說服力地支撐起整部電影。作為觀眾,《長夜》對我來說沒有甚麼可以推敲探索的空間,我基本上只能對藤澤和山添二人的遭遇和感懷照單全收。《長夜》沒錯是充滿善意,也有它別具一格的溫柔,但於我而言還是太過單薄片面了。

《長夜》推出以後,三宅唱與濱口龍介、電影學者三浦哲哉進行了一場鼎談,詳盡地討論此片。他們的論點我就不一一轉述了,然而當中最吸引我眼睛的,是三宅唱一句非常立場鮮明,甚至帶點激進性的發言。他總結對談時引申到日本電影製作的現況,道:「⋯⋯如果籌備期間過短,就不可能做出好的電影。『拍攝天數延長的話預算也會拉高』這樣的話其實也聽過很多次,解決方式很簡單,要嘛就讓說這話的人離開我的現場,要嘛就好好做前期籌備。如果我們能在開拍前就營造一個良好的環境⋯⋯就能產生良好的化學反應。」這種說一不二,在原則底線前「無價講」的強硬態度,不是在《長夜》中能看出來的東西。「要嘛就讓說這話的人離開我的現場」,很 cool,根本是杜琪峯才能講出來的說話 (as a matter of fact,杜琪峯曾說過在拍攝現場「有用嘅人喺度,無用嘅唔該走」)。三宅唱極度重視跟團隊的關係,製作時每個環節的氛圍,如何能夠「齊上齊落」。這是一個相當罕有的創作理念和堅持。《長夜》於我有點未竟全功,沒能完完全全將構想和製作時的美好刻寫在最終的作品上。不過,只憑三宅唱上引的表述,也足夠讓我期待他下一個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