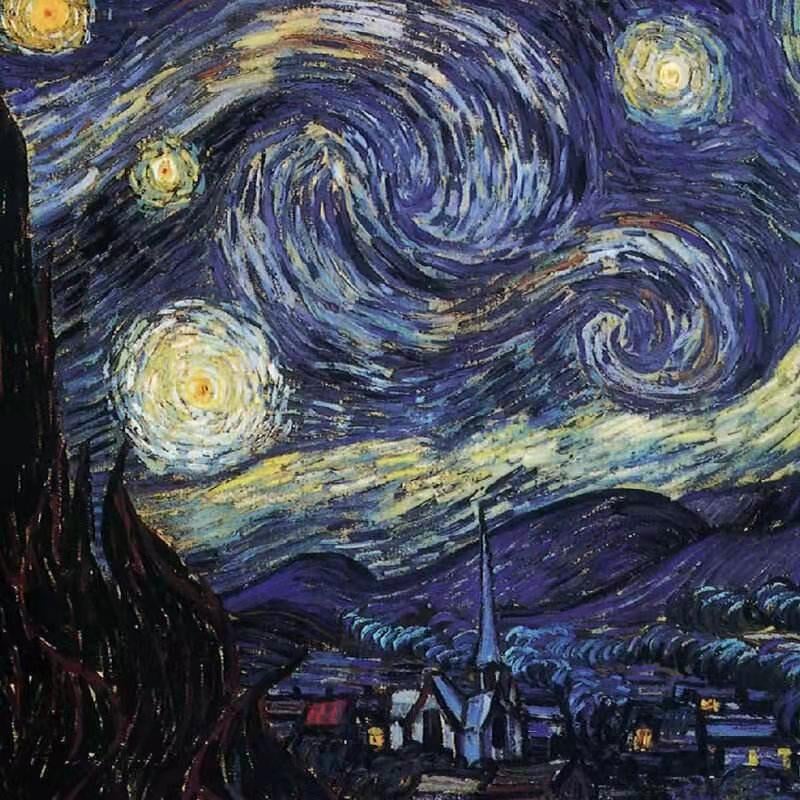讀《笑忘錄》——遺忘之於人是什麼
我是在高中的時候最初接觸到米蘭·昆德拉,應該是從木心先生的《文學回憶錄》中第一次瞭解到。那是印象很深的一段描述,準備離開捷克的昆德拉在移民局辦理手續,移民官員問他要前往那個國家。昆德拉轉動桌上的一個地球儀,然後問了一句,“還有其他地球儀嗎?”初讀此段,我便大為震撼,這是在受到了如何的精神創傷後才對這個世界如此失望。昆德拉在蘇聯社會主義的影響下,也曾是一個左翼青年,可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之後,昆德拉有了一種“反叛心理”:“永遠地,我被注射了抵抗一切抒情企圖的疫苗。那時候我唯一深深地、貪婪地欲求的東西,就是一道清醒的、看破世事的目光。我終於在小說藝術中找到了它。這也是為什麼對於我,作為小說家,不僅是實踐‘一種文學’形式;它是一種態度,一種智慧,一種立場;一種排斥任何政治、宗教、意識形態、道德和集體相認同的立場;一種清醒覺悟的、不屈不饒的、滿腔憤怒的非認同化,它的構成不是作為逃避或被動,而是作為抵抗,挑戰、反抗。”
這是昆德拉闡釋自己小說創作的原因,不是為了一種無聊的遊戲,而是維護他自己思想的獨立性、對抗抒情化世界的一種方式。儘管他提到了“排斥任何政治、宗教、意識形態、道德和集體立場”,但這其實是一種超理想的狀態,不可能達到。因為人是社會關係的總和,是社會的存在物,是類的存在,不可能脫離群體而存在。但我自己受昆德拉的影響也曾告訴自己,“我只想做一個能創立自己的獨立的思想體系的,不隸屬於任何政黨、任何意識形態、任何集體的簡單的讀書人。”現在想想,實屬太理想!我們每個人不一定帶著國籍出生的,但一定是帶著民族情節、民族記憶出生的。以昆德拉的《笑忘錄》為例,這是在他被迫離鄉背井,移居法國後寫的。這個作品展現出的是一種深深地無力感和末日感,昆德拉的處境是國土和精神的國土上雙重的“無家可歸”。這也奠定了《笑忘錄》低沉、壓抑、悽楚的基調。
《笑忘錄》從書名便可看出是關於“笑”與“遺忘”的。“笑”這一生理現象是伴隨著我們每個人的,有“微笑”、“狂笑”、“譏笑”、“嘲笑”······昆德拉的笑是讓人讀後不禁冷笑、苦笑,一種無奈的笑。法國詩人艾呂雅在劊子手殺人的時候,卻在集中營上空高唱友誼、和平與愛情,讓人感慨、歎息。昆德拉也是歎息,歎息這個越來越無序的世界,歎息這個所謂的“文明社會”包裝下的霍布斯所描述的自然狀態下的私利的戰場。這是昆德拉對人類良知泯滅和正義感淪落的歎息,這是一種悲戚無奈的笑、含著淚水的無能為力的笑。還有一個主題便是“遺忘”。生和死是人類的兩大主題,或是起點和終點。死亡就是自我的喪失,不管是肉體或精神上的。而自我又是什麼呢?昆德拉說自我很大程度上就是往事和記憶的總和,死亡在某種程度上就是意味著失去過去、失去記憶。我們都畏懼死亡,但這不是對未來無知的恐懼,而是害怕對過去的記憶的遺忘。遺忘之於人,就是生命的一種死亡形式。
《笑忘錄》由七個關聯性不太大的故事組成,其中都不同程度在描寫性愛場景。因為昆德拉有個信條,那就是性愛場面能產生強烈的亮光,能突顯人的本質及生活處境。如在《不能承受生命之輕》中托馬斯情人對他說,想在劇場的舞臺同他做愛,讓下麵的人都觀看著。這是昆德拉在表現人的生命感受、欲求和躍動,展現強烈的個人主義的欲求。但《笑忘錄》不止於此,這還是一本強權主義的小說。在第一部《失去的信件》中有個人物說了句“人與強權的鬥爭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在這個“偉大”的時代,人與強權鬥爭的結果是什麼?就是失去了過去,被歷史所遺忘。一個強權主義國家想要完全消亡另一個國家,最好的方式就是遺忘,就是抹去那個國家的歷史和文化,讓青年對自己國家自己民族的過去一無所知,把自己的文明強加到那個國家,這就是“遺忘”。我想昆德拉一定在擔憂他自己的國家,捷克的燦爛文明的未來。
《笑忘錄》是我很久前讀的一本小說,最近才重拾。中間的很多情節我不記得了。但讀小說不正是如此嗎?我們從書中獲取的應該是對自己人生、生命的體悟,用自己的生命體驗與作者產生隔空的共鳴,而無所謂小說中的情節。對於“笑”與“忘”兩大主題,我對遺忘更有感觸吧。在第一部《失去的信件》中的開頭,描述了這樣一個場景:捷克領導人哥特瓦爾德在雪花飛舞的嚴寒的冬天向同胞們發表演講,但此時他是光頭,於是他身旁“善良體貼”(昆德拉是如此描述)的克萊芒提斯摘下了自己的毛皮帽,把它戴到了哥特瓦爾德的頭上。這是多麼友愛的、體現社會主義革命同志情感的場面啊,以至於這張照片後來在海報、課本、博物館廣為流傳。後來,克萊芒提斯因被指控叛國罪而被送上了絞刑架。於是,他從此被歷史給抹殺了,原來的照片裏他所在的地方變成了光光的一堵牆,而唯一留下的只是戴在哥特瓦爾德頭上的那頂帽子。我不禁想起喬治·奧威爾《1984》中大洋國的宣言:誰能控制過去就能控制未來,誰能控制現在就能控制過去。歷史是有本來的歷史和書寫的歷史之分,而我們從小瞭解到的歷史往往是經過無數的沉澱與改造後堆積於我們時代個體的集體記憶的歷史。對於歷史本來的面貌我們一無所知,自由主義大師哈耶克說:“歸根到底,有些人即使從來沒有讀過一本書,可能也從來沒有聽過那些影響過他的歷史學家的大名,他們也要通過這些歷史學家的眼睛來看歷史。”我們看到的世界,是透過別人的目光;我們所知道的歷史,也不可是拾歷史(編纂)家的牙慧。
讀到這個場景,我想遺忘的同時也是一種銘記。當局讓人們遺忘克萊芒提斯,仿佛他從未存在過,除了一頂可能早已不屬於他的帽子。而同時人們自願或不情願地“永遠”銘記了哥特瓦爾德。我之所以說“永遠”是因為有時候遺忘比銘記更困難,真正為人民所推崇的,而不是興盛一時於一個時代的,才能為人民真正銘記。
再往後讀,一個時代背景的敘述在我看來也是安排的精妙,也許只有懂得人才懂。“孟加拉大屠殺的血流,很快就沖淡了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特的記憶,阿連德的遇刺又掩蓋了孟加拉的呻吟,西奈沙漠之戰則使人們忘記阿連德,柬埔寨大屠殺又使人們忘記西奈沙漠,諸如此類,不勝枚舉,直至人們完全徹底地忘記每一件事情······”歷史不斷地簇擁著我們向前,歷史的發展可謂稍縱即逝,一個歷史事件在前一天或許還帶著清新的氣味,第二天就變味了,被遺忘了。處在迷霧時代的我們,是什麼也看不清的,或許,這也不是一個迷霧而時代,而是光明的世界。但正如黑格爾說的,“在純粹的光明和純粹的黑暗中一樣,什麼也看不清。”這也是“霧失樓臺,月迷津渡”,在歷史中人們只能是提線木偶,在出演著一場歷史事實的木偶戲,儘管人們可能對此一無所知。
“遺忘”,我書寫於此時,想起最初的題目:遺忘之於人是什麼?我給出了昆德拉的一個答案:遺忘之於人是一種生命的死亡形式。遺忘於我而言,就感性經驗層面,可能就是先前的朋友的形象在我腦海中由生動活潑的立體形象變得單薄、單向度了,只能記得零星的碎片,名字可能會想起,但容貌早已模糊了。曾經以為可以銘記很久的人和事,在時間面前也不堪一擊。除此之外,遺忘也是對於我們整個群體而言,這種“遺忘”也就是一種歷史虛無主義。例如“文化大革命”作為十年浩劫是中國歷史上灰色、甚至黑色的一頁,但同時也蘊含著一些根本性的歷史教訓,這亟需當今中國人認真加以總結,以免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進程中不再重犯那樣的錯誤。然而似乎當今我們竭力把這個歷史事件從集體記憶中抹去,仿佛遺忘一個東西就能超越一個東西一樣。我想,相比於這種“遺忘”,刻意的抹去,我們更需要的是反思。對於一些歷史泡沫,我們可以遺忘,對於有些教訓,我們需要吸取並反思。
歷史是一曲變奏曲,“笑”與“忘”交錯其中。
(去年7月昆德拉離開了我們,當時重讀《笑忘錄》,寫下這篇小文,今日整理文檔偶然翻到)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