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像看过她戏的观众一样困惑 ——专访香港剧作家庄梅岩
“看着一个荒诞剧慢慢变成一个写实剧,我的难过和愤怒不比当事人少。”
戏剧是什么?香港剧作家庄梅岩说,戏剧是“将很多人的人生浓缩给你看。你接触多了戏剧,会更明白人生苦短,更明白人的最终价值应取决于什么。”

曾经的香港华洋杂处,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生活方式上,都留下了很多思辨空间,这位六度获得“香港舞台剧奖最佳剧本”的剧作家,经常会聚焦香港社会的争议话题,和在其中挣扎的特定人物。她写过关于医生理想与现实冲突的《留守太平间》,讲宗教、性骚扰的《法吻》更探讨了所谓“真实”的不稳定性,讲述新闻自由和从业者挣扎的《野猪》,还有关於同志题材的《我们最快乐》。近日,她的《圣荷西谋杀案》谋杀案在港演出,掀起又一波热潮。
庄梅岩十分擅长用戏剧中古典的“三一律”呈现故事,将这个社会诸多痛苦和困惑,在狭小的戏剧空间内紧凑地呈现出来,观众就要立刻处理这些平日被刻意忽视、不愿思考却又迎面扑来的问题。
庄梅岩的每一出戏都是一个香港的隐喻,而庄本人,也是这隐喻的一部分。
舞台带来的勇气
2019年,庄梅岩为六四惨剧所编写的舞台剧《5月35日》,在5月底首演,甫开售旋即在三小时内售罄,后来更在7月加场。2020年6月,因为疫情原因改在网络上众筹直播,48小时内累计有十多万人登入观赏,可谓创造了香港剧场历史的新一章。而该剧也为庄夺得了又一个香港舞台剧最佳剧本奖项。
看庄梅岩的戏,你会感觉到剧作家此刻,正隐在观众戏中微笑的着看黑盒子里的观众们,如何随着剧中人在困境中困惑窒息、如何挣扎辩论、如何寻找答案。不过《5月35日》的上演,庄梅岩却无法这样怡然自得,因为在观众席中还有一双看着她的眼睛。

2019年的一个新闻,是在一场演后谈中,她告诉观众,在她创作《5月35日》期间,有个来自内地的不速之客曾拍她家门,说知道她在内地有什么亲人,让她不要再写“六四”,又问她收了多少钱写六四的剧,背后有哪些外国势力。然后她话锋一转,说,这个人现在就在观众席上。她转用普通话讲:“我要让你感受恐惧,我可以指你出来,让全场都知道你是谁。但我没有,这是我对你最后一点仁慈。”她叫那个人,去游行,去人群中感受一下,香港人在追求什么,有没有收钱。
舞台,是庄梅岩最后的壁垒。在这里,她和“权力者”的关系是逆转的,舞台令庄梅岩有和他对质的勇气。

那是《5月35日》正式演出前一年半,神秘人物通过庄内地的亲戚,摸到她香港的父母家中,再通过她父亲,才联系到了她,向她提出了“礼貌的劝喻”。她瞬间的惊讶迅速转为了愤怒,庄直斥“神秘人”利用自己亲友的善良去胁迫自己。
“这个世界上有千百万种方法去联络我,包括去剧团找我,去‘六四舞’找人联系,若真是公事,通过正常方式找我,为什么要用敲家门的方式?”庄反问笔者。笔者回答,这某种程度上也许是为了显示权力机构的“全知全能”,当然更重要的是让你了解到,你的言行并非只向你自己负责,这都会创造出他们期待的恐惧感。
“我知道这种做法在内地是很‘正常’的,但是NO,这里是香港。”

庄梅岩没有知难而退,但愤怒平息后,便是长时间的害怕和猜忌。庄梅岩像港产警匪片的主角一样,分析起自己是如何暴露的:剧目还没有公开,知情者只有少数几个参演人员,难道是被人出卖?剧本才刚刚动笔,仅仅是去北京做了趟前期采访,就已经暴露了?他们接下来还会自己有什么不利?这些疑问直到演出结束,也没有个确切的答案。
如今再谈及那个南下接触她的“神秘观众”,庄梅岩的恐惧和愤怒少了,却平添了些好奇和幽默感。“当你熬过担忧期,就能够抽离恐惧,此时再看这个体制,就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笑话。于是你便会更加地好奇对方,想去八卦他们的想法。愿意去用调侃的方式来讲故事的时候,就更加不会怕了。”
庄梅岩说,自己是个幽默不起来的人,过去写的《野猪》很沉重,个性不够灵活。这一次经历过后,她想写一个“关注和被关注、监视和被监视”的轻喜剧,“里面会有爱情,也会有很多蠢事和傻事”。生存的幽默感,某程度上也算是对强权的另类反抗。
在香港写六四的我不是勇敢,因为香港还可以讲六四
对于庄梅岩来说,六四这个主题则长久地萦绕在她心中,但却苦无灵感,更怕写出陈腔滥调的故事。十年前,她喜得贵子,才渐渐对“天安门母亲”有了不同的理解。她会将自己代入作品《教授》的困境当中:“作为母亲的自私和对社会的道德观”的诘问。“如果他(孩子)长大一些,出去冲(参与社会运动),也无法劝说他‘不要用危险的方法’,也要接受万一发生的情况。自私一点,当然期望孩子没事,送去外国。”

她的父母生病,庄梅岩很庆幸自己能照顾他们,也不禁想像那些六四事件中子女罹难的父母。“他们不止要承受这种伤痛,在内地敏感时间更被禁锢、骚扰、被旅游。如果我是死去的子女,看到父母在如今仍然被如此对待,真的会很愤怒。”
她关注的始终是人性。六四至今延宕三十年的历史苦痛,被凝炼为剧作中,一对儿子死于六四的老夫妻之间的伤痛离别。三十年得过且过、不敢面对的苟且生活,终于要在妻子患上绝症时面对了,他们掏心掏肺地面对爱子离去的苦痛和自己的懦弱卑微,鼓起勇气,亲自前往广场“堂堂正正”的拜祭儿子。庄梅岩一直在说,她不知道六四难属们是怎样熬过这长久的伤痛,他们的故事比自己的作品还更有戏剧性、更令人肝肠寸断。她在访问时问天安门母亲,这三十年间有没有小说家、剧作家来向你们了解故事。“没有,一个都没有。”
在庄梅岩的创作轨迹中,2012年的《野猪》和2014年的《教授》便已经逐渐涉及了香港的社会政治议题,但是指涉仍然比较模糊。《野猪》讲的是政府与财团官商勾结之下,掌握内情的学者失踪,传媒集体噤声,一位资深报社编辑另起炉灶坚持报道真相的故事,记者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的撕扯。而《教授》则描写了香港大学教育和社会运动的关系,庄创作出了学生和教师在象牙塔内所教授的社会公义与现实社会的脱节的张力故事。“野猪写得虚,是因为压力只在萌芽阶段,更多的是想象,不需要展示你的坚强,但是六四就硬生生地告诉你,你不应该去悼念。正因为此,我们只能更加应该直白且赤裸的悼念。”她想要坚守的,至少是这个小小黑色空间内的自由,“如果不自由,我宁愿去扫大街”。这是她的口头禅。

“在香港写六四的我不是勇敢。只有在危险的地方做危险的事情才是勇敢,我只是大胆,因为香港是安全的。在香港是可以讲六四的,我们希望追寻这段历史,去找真相,去相信真相。”
随心所欲的是梦想,满途荆棘的才是理想。”——《留守太平间》
香港社会的残酷,快到她来不及回应
庄梅岩发现自己的创作,已经无法完全地考量“艺术性了”,因为她的作品在一个个的印证现实。《野猪》之后,香港媒体在权力和金钱的双重压制之下,几乎完全被扼住了咽喉:记者在外采访被骚扰、在内被改稿;时政节目被投诉至停播,“大合唱”的时代越来越近。《教授》之后,在外,社会运动加剧,在内,校园教育成为政府眼中钉,教授们斯文扫地被监视、举报、批判已成常态。庄梅岩意识到香港社会的残酷还在加速碾压着她、碾压过现实。快到庄自己的也越来越多困惑,快到她的创作也来不及回应。

面对冲突逐渐加剧的社会,她同样感受到震荡。“当下的社会对于个人来说当然会成为重要的人生经历,甚至丰富自己的创作;但是作为人来说,我却几乎无法回应,更需要时间疗伤。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会发现自己越写越无知,自己也找不到答案。只能在写作的过程中自我对话,自我疗愈。”但是她所坚持的是,越是不自由的环境,越要在道义上帮助被压抑的人说话“我很怕见到不想见的东西,但是最终仍想去面对,哪怕那是不想知道的真相。”这是庄梅岩创作戏剧的意义。
但庄梅岩不是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剧作家,她商业性剧本的创作仍然口碑不俗,比如她在2017年创作的首部电视剧《短暂的婚姻》,这部由陈奕迅主演的爱情小品引起了不错的反响。

不过这种成功并没有让她滑向那种“食髓知味”的状态,也就是仅仅因为商业作品回报高,便被大众化品味牵着鼻子走,“版权费虽然高,但是就要对市场有一定的妥协,这笔钱就算是补偿作者的精神创伤吧”,她有些自嘲地说道。她认为创作的平衡在于“又可以糊口、又可以探索艺术生命、同时完成戏剧的意义。”对她来说,《法吻》便属于艺术上的佳作,而《5月35日》就是纯粹的具有意义的作品。她不指望后两者能够为她带来什么收入,“重演的多数是没钱的剧团,到最后算了,版权我送给你了,反正也没有几千块。”她也不放弃遐想地笑道,“当然如果有好莱坞买我的剧本,也是很好的事情啦。”
即便没有国安法的阴霾,香港剧坛本身都要面对受众小、资源少、创作自由在不断收窄的问题,早就是“带着镣铐跳舞”的状态。按照庄梅岩的说法,香港会进入剧场的常规观众不过四五千人而已,做戏剧的人往往都要有另一份兼职去维持生计。虽然艰辛,但庄认为这至少能令戏剧工作者不必在创作时还要再去考虑如何用戏剧来赚钱。——她怕的就是市场与金钱阻碍了创作的纯粹和艺术价值,这对她来说是另一种自我审查。另一方面,有剧团为了获得内地演出的机会,逢迎内地审查,也给创作画下了红线。
庄梅岩认为,香港戏剧作为华语世界中最独特、自由的创作空间,在金钱和权力的诱惑之下必须要坚守到底:“爱戏剧爱的不是形式,而是人类长久以来的文化养分。当你去读经典,那些经典启发你创作,你却去做自我审查,这违背做戏剧的初心。”
《圣荷西谋杀案》的隐喻和预言
《圣荷西谋杀案》是庄梅岩2007年下笔的作品,2021年4月底在愁云深锁的香港再次上演。庄梅岩说重看这部作品“是一个过时了的作品,说它过时,是因为捕捉了和现在很不一样的风景、一些不复再的风景。”

剧中一场内地、香港、台湾的身份政治对谈颇为令现场观众触动,男主Tang的生意夥伴、内地人Patrick及女主玲的台湾同事明哥恰巧聚在了他们的家中。Patrick是那种典型张口闭口爱谈政治的内地中年油腻男,看到台湾人便兴奋起来:“台湾?今天怎么搞的,两岸三地的人都来了,小邓(Tang)你厉害,中国在你邓家小小的屋顶下不费一兵一力就统一了。”当年内地人的几句民间吹水笑谈,到如今看来倒已经登堂入室认真的紧了。
香港人Tang是如此典型的香港人,好听些叫做“专业经理人”,其实不过是“掮客”。正如香港作家陈冠中《什么都没有发生》的主角张德志,帮商人排忧解难、为富豪投资增值,不问世事,对六四则是丝毫不感兴趣。Tang也是如此,用“务实”去迎合大势,“如果所谓身份意识阻碍我融入新生活,我就宁愿改变自己去适应环境。”
但是这次重演,香港观众的掌声和欢呼却给了台湾人的答案:“这些身份问题上的争论,甚至争取在历史洪流里不算什么,一百年、五百年後再看它,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浪花。但正正在这小浪花里如何挣扎便体现了人性的尊严,我们是站在完全不同的观点去看这个问题,你说的是生存,我说的是如何生存得有尊严。”
如今的香港,再也不是“什么都没有发生”,一场铁笼中的困兽斗反倒成了当下香港困境的隐喻和预言。庄执意把本剧背景留在当年,绝不是为了怀念,而是为了警醒观众,用这样一出过去的déjà vu让当下的港人回看曾经的自己。很多遗憾和悲怆过后回望过去,她才发现“自己曾经站在命运交接处,却没有为自己的尊严力挽狂澜、把借来的地方据为己有。”和剧中人一样,香港人这个身份在命运的浪潮中经受过丧失、窃取乃至剥夺,从来都是“被定义”自身的命运的香港人,如今关注的是尊严。“我想我跌眼镜了,我2007年并不觉得香港人会这样反抗。历史证明香港人并没有把存在遗忘,而且曾为尊严奋力反抗过。”——钢铁结构的大幕徐徐落下,戏剧内外仍被牢牢困在铁屋子,呐喊声仍在持续。

如今庄梅岩已经有了一男一女两个小朋友,但是她养孩子却似乎没有太多大道理的育儿经,小朋友似乎和她创作的文本一样,作者本人难以控制如何成长和被阐释。“我唯一重视的就是人格,可是人格的正直却很难在如今的环境下培养。”
她此时像一个看过她戏的观众一样困惑:“怎样能解释给他听,警察可以用这样的暴力去对待别人而又不需要承担后果?为什么官员做错事情,乌纱帽却还能够稳如泰山?——当然另一方面我也要和孩子一起理解,究竟前面的一连串的不公义,是否就能够合理化如今示威的剧烈程度?”
她深吸一口气,不懂得形容当下的复杂。“也许对我来说,最大的报应是(子女)会为了钱出卖人格,如果他觉得公义不重要的话,我就会很难过。”她有些自言自语的说道。“不过这一点都要尽量抽离点,陪伴只有十几年,将来(子女)即便和自己切割,都要适应,不止是政治,还有个性、生活方式。”
孩子的上午课结束了,她看到不远处校车驶过,急急穿过马路。他说这是他的“小暖男”,2019年怀有身孕上街游行的时候,“暖男”坚持陪伴在侧,保护母亲。
“你只可以有一种信念,就是到最后会开花结果。”——《教授》
原文刊于《歪脑》:https://www.wainao.me/wainao-reads/Chong-Mui-Ngam-interview-05122021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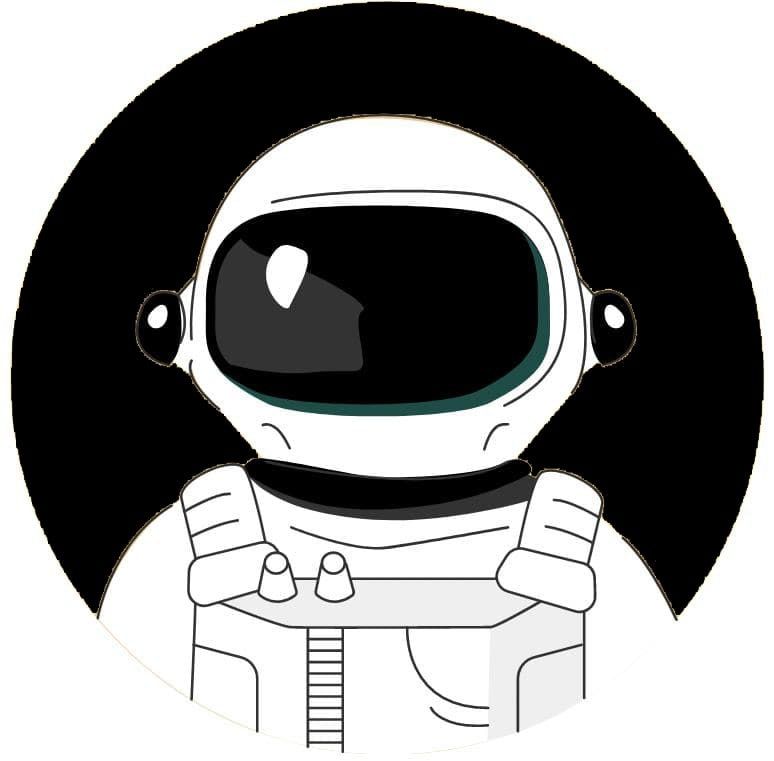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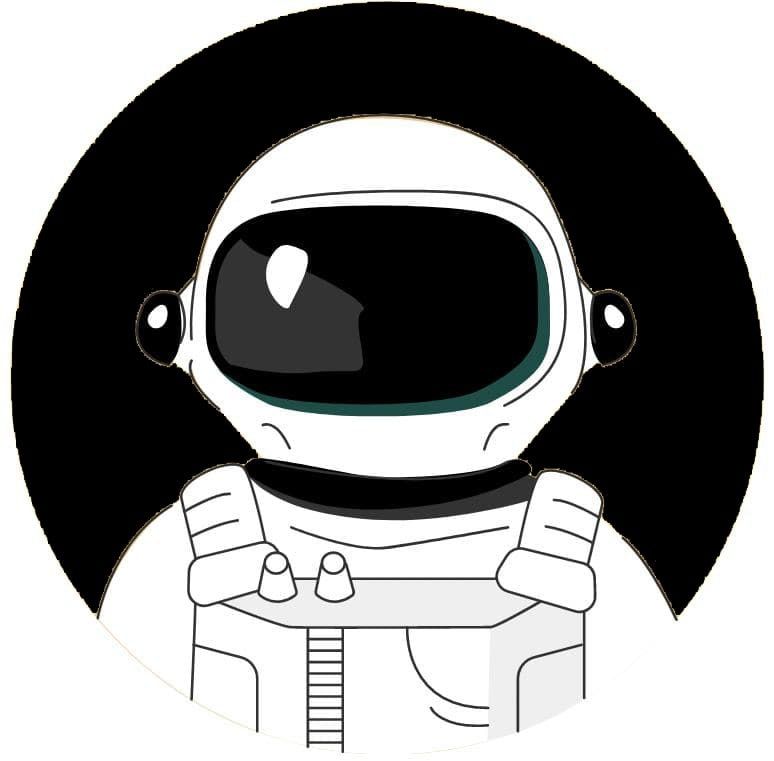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