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刚之气」为什么是一个话语陷阱?

「本文于 2021.2.27 原载于公众号philosophia哲学社」
作者 / 歌川
1 「真正的阳刚之气」:一个话语陷阱
最近教育部对一份名为《关于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的政协提案的答复,让「阳刚之气」一词成为大家讨论的热点,进而形成一场关于性别议题的交锋对阵。这场交锋,围绕着「阳刚之气与美德的关系」进行展开。一些人着力于否定所谓的「阳刚之气」。它未必是美德,也可能只是男性/雄性气质 (Masculinity) 的粗暴表现:譬如性情暴戾、举止鄙陋。相反,也有人试着界定「真正的阳刚之气」。他们认为「阳刚之气」意味着勇于担责、恪守礼义,并且说「女性也可以拥有这些美德,美德是不分男女的」——其中,最典型的观点,是央视新闻的评论:「阳刚之气不只是男性化」。

简而言之,这些讨论主张:「阳刚之气」或男子气概中有很多「有毒」的部分(一般被称作「大男子主义」)。而我们应该重新定义「阳刚之气」,从而剔除坏的,留下好的。「阳刚之气」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美德的追求,这才是「男人该有的样子」。
不过,这种貌似温和的语调,在我看来依旧是在原有的性别本质主义框架下打转:美德凭什么一定要与性别挂钩呢?当人们说「女性做出了某些行为,这也是一种阳刚」,其实依旧默认着,那些作为美德的特质在根本上属于男性;即便人们已经普遍对「男性气概」产生厌恶并严厉抨击它,但结论也只是停留在「让『阳刚之气』这个词纯化,我们要好的、真正的『阳刚之气』而不是坏的『大男子主义』」而已;即便不少人宣称「女性也可以拥有美德」,但这些「美德」最终还是只能在男性身上展现的最彻底、最淋漓尽致。只不过这时的男性便不是「胡子拉碴大腹便便」的「爹味男人」,而是「优秀的男性」罢了。
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一个神话,认为优秀特质或美德似乎在某种本源的意义上与性别相关?美德、「阳刚之气」与性别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这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2 「阳刚之气」的性别政治分析
从一个问题开始:美德与性别有关吗?女权主义者们有一个被美国学者哈维·C·曼斯菲尔德 (Harvey Claflin Mansfield) 称之为「性别中立社会」的愿景。在《男性气概》一书中,曼斯菲尔德将「性别中立社会」的主张概括为:性(sex)只是生理性的(sex一词也可以译作「生理性别」),而人在社会中的权利、义务或地位则是社会性的。这两者根本没有本质性的关联,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因此,我们不能以生理性别去规定社会性的法权或社会地位,所以,社会应当是性别中立的。我们应当在语言、社会政策和社会机构中「去性别化」,从而避免偏见和歧视。[0]
这个主张通过现代科学的目光敏锐地捕捉到了所有性别偏见的一个荒谬之处:生理的性怎能与社会性的地位、美德和个人能力混为一谈呢?社会性的事物,既不属于生理性的范畴,也很难在科学上证明是被性决定的,将直接的相关性强硬地安放在这两者之间,是一种独断又可笑的观点。不过,这个主张却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既然这是两个好似并不搭边的范畴,那为什么这两者会被结合在一起?它们又是怎样结合在一起的呢?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需要借助女权主义性别政治理论 (Feminist political theory)。女权主义认为:性本身关乎权力。虽然从现代人的目光看,性别「不应当」决定权力分配的方式。但是,在根本上讲,是权力塑造了有关性别的一系列仪式和实践 (praxis),通过这些实践,人们被构成为被女权主义者们称之为「社会性别」(gender) 的东西。而性别偏见的话语正是基于这一「社会性别」产生的:「男女有别」、「男人样」、「阳刚之气」等等,都属于性别偏见话语的一环。
让我们从对「阳刚之气」这个具体例子进行分析,以此来考察性别政治是如何运作的。为讨论方便,我们默认它和「男性气质」或「男子气概」属于同一个词的不同叫法。
不妨检视「阳刚之气」这个词在传统意义上所具有的各种内涵:我们会在什么情况下说某人有「阳刚之气」呢?回想这个词会在怎样的语句中出现:「做事拖拖拉拉的,一点也不像个男人」、「张某先的做法虽然以结束对方二人的生命展现了自己的男子汉气概,但带来的结果就是得到应有的刑罚」(吉林市梅河公安对一起杀人案的通报,现已删除)、「男子汉敢作敢当/流血不流泪」……对这些叙述我们往往用以下几个词就能概括:决断、力量、责任心、坚韧……这一切构成了为女权主义学者瑞文·康奈尔 (Raewyn Connell) 称之为「支配性男性气质」(Hegemony) 的东西 。[1]因为这一切都在强调着一个作为理想形象的「男子汉」的独一支配权力或霸权:男子汉必须有力量,从而能够占据决断者的位置,进而为自己的勇敢决断负责,在负责的过程中必须坚忍不拔等等,决策或行动的主体,被天然地与男性等同起来。由此可见,所有男性气概语词,都围绕着对绝对权力的迷恋展开。男性气概最高的表现是对既定规则的破坏,但这正昭示着绝对权力的显现:男性有如至高的主权者或立法者,他把自身认同为一个法外的主体,而对规则的破坏恰好是在构成新的规则。因此,男性对权威的挑衅、对规则的无视和破坏,只是某种彰显他自己才是唯一绝对主体的行动,即「我才是一切的最高主权者」。

而这种支配性男性气质,作为一种能驱动实践的话语,其自身又必须通过一种系统性的排斥才能得到全面并且稳定的定义和再生产。在这里,我们需要解决三个问题:
首先,为何是否定性的「排斥」而不是肯定性的「积极建构」?
其次,这种话语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它生从何来?
最后,这种话语是通过怎样的装置被如何生产出来的呢?
我们首先解决第一个问题。即,为何是「排斥」而非「积极建构」。我们知道,有决策者,就需要有服从决策者;有支配者就需要有被支配者;有行动的主体,必须先规定谁是客体。一个主体,一个自我总是需要一个使自己成立的,为了构成内部而存在的「构成性外部」[2]。唯有先确定了「外面是什么」,我们才能在自我与外部之间划出一条清楚的界限,进而才能知道:我是谁。在这里,出现了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论主奴辩证法一章中所谈到的观点:主体,唯有在他者显现出来的时候才能成立,唯有在他者持续遭受贬抑的时候才能持存。就好像某人如果想要成为支配他人的主人,就首先要有作为他人和客体的人供他支配。所以,他要靠制造出这样的他人,并且通过否定这样的他人来表明自己的支配地位。[3] 如果将这样的主体构建的基本机制,与现实的权力运行状况,以及两性的在父权结构中的相对位置相结合,这就变成了上野千鹤子在《厌女》中提出的著名公式:(阳刚之气)=不是女人/不像女人=男人。[4]
接下来回答第二个问题:这种话语生从何来?我们刚刚已经表明,与「阳刚之气」相关的东西,不是生理性别,而是权力。现在让我们来论证是权力主导了社会性别的构建。如果说生理性别可以使用「男/女」、「雌/雄」这样的字眼加以形容,那么,与之相对的社会性别则可以使用「阴/阳」与之相区分。这样的称呼挪用自中国古代的儒家经典。譬如,《易传·系辞上》中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这就是中国古代特有的「天命之谓性」的性别本质主义;而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阳尊阴卑》中则更赤裸裸地表达出这种性别本质主义的支配性特征:「以此见之,贵阳而贱阴也……丈夫虽贱皆为阳,妇人虽贵皆为阴。」虽然这两句话都是颠倒的意识形态表达,但我们依然能从中把握到一些社会性别构建的脉络:在「天尊地卑,乾坤定矣」的说辞中,虽然至关重要的权力隐身在「自然」、「天命」的大幕之后,但我们仍然可以识别出尊卑秩序是先于男、女而存在的这一事实;而在董仲舒的书写中,个体的贵贱又必须服从于这个貌似先验的总体性权力布局,因而某一特定妇人之贵贱,并不影响她「应当」所处阴柔、卑下之位这一点。在这里我们看到,阴/阳性与男/女性有着以下的关系:首先有一个阴阳尊卑的先验秩序,在这个秩序之下,男/女的生理性别是作为识别标记而存在的。依据他们所拥有的不同的生殖器,他们被分配到了秩序中的特定位置,聆听相应的教诲,学习并遵照这个秩序给出的图景进行相应的支配与被支配的特定实践。这个教诲和图景,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上野千鹤子的公式。现在的问题是:这个秩序是如何形成的?
我们刚刚提到,尊卑秩序,可以视作是权力运行的总体布局。只不过在意识形态的颠倒和掩盖中,一手创造了「先验」的权力不但隐身了,并且打扮成了后来才出现的东西:本来,权力是性别的根据;现在,却被颠倒成性别是权力的根据了。现在,我们就要看看这个秩序是怎样通过权力而生成的。这就涉及对权力和暴力之关系的理解。在很多人(以汉娜·阿伦特为代表)看来,权力和暴力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暴力,是直接刺眼的身体伤害,皮肤流血、肋骨骨折,且常常是违背人意愿,不经过任何同意的,强硬的、没有半点好处的东西;权力,却是政治性的,无形的,不可见的,「人民主权」的,即经过同意而为了某种共同之善去行使的东西。但我的理解却与之有根本上的不同:一种权力,不论它怎样运作,总是以暴力为最终的主保。在这里我们需要介绍齐泽克的暴力理论。
在齐泽克看来,暴力有两大类:首先是主观的暴力。就是我们日常所谈论的那种「暴力」,一谈到它,我们接下来就要谈到杀人犯、暴徒、恐怖主义者,进而把暴力等同于恐怖的可见之物,把主观暴力当做是暴力的全部内容。对这种暴力,我们的态度总是不容置辩地喊道:杀人犯该死!消灭恐怖主义!我们认为暴力是必须被消灭的,如果它一出现,就必须加以治理。但是,我们却「无权」「私自」消灭暴力(在这里,权力出现了)。谁「有权」呢?正是那看上去和平安定的秩序。这样我们就来到对客观的暴力的考察:我们似乎都忘记了,一种暴力只能靠另外一种更强的暴力去消灭。对犯罪的惩罚与预防,难道不是依赖写着各种暴力手段(处死、囚禁、夺走财产)的《刑法》去实现的吗?而《刑法》之所以有效,难道不是因为我们知道在这本书的背后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军队与警察吗?只不过它以一种安排得当,整齐有序的「秩序」的和善面孔出现罢了。所谓秩序,不就是首先垄断了暴力,然后借此划分出什么是暴力并对之加以治理的东西吗?这就是客观暴力中的系统性暴力,也叫制度性暴力。
不错,在我看来,那宣布何谓暴力并能获得一致同意而去处置暴力的东西,才是最高的暴力。它的名字就叫做权力,但我们经常为了使它和蔼可亲而称之为「制度」,以表明它本身是一种稳定的布局和结构,从而构成了「秩序」。权力的功能就是不论他人意志去支配他人。而这种支配之所以成功的理由,就在于权力故意将暴力隐藏在幕后,同时叫它的影子若隐若现:你最好服从我(们)的支配,否则我(们)就可能(经过一致同意而)消灭你的肉体。不论权力在现实生活中以怎样令人眼花缭乱的形式运行,这永远是权力物理学最基本的第一定律。
所以,我们必须直接指出这一点:阴阳尊卑的秩序——或者用它最通用的名字,「父权制」——的形成,只是源于一个根本上关乎暴力的绝对律令:「你去使用暴力 [5] 支配她们」。男性因受「阳刚之气」的感召,从而产生的对绝对权力的追逐与迷恋,归根到底只是要实践这一绝对律令。在这里,唯有支配女人,才能证明自己「不是女人」,因而是「阳性共同体」的一员;而唯有使用暴力,才能支配女人,才能是行动的主体,是权力的掌握者。即便这种暴力可能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强硬的主观暴力,如强奸、杀妻、家暴;或者是面目威严的制度性暴力(第一种客观暴力),如对堕胎的管控、企业招聘中的性别歧视、以及对家暴和性侵的「宽容」等等;或者是潜移默化,不断欺骗人去再生产这些暴力的话语性暴力(第二种客观暴力),如荡妇羞辱、「贤妻良母」、与我们今天所探讨的「阳刚之气」。
这三种暴力(主观的、制度的、话语的)之间存在一个递进关系:即暴力越来越不可见、越来越日常化、因此越来越有效了。暴力变得越来越不像「暴力」,正如婚内强奸不被认为是强奸,家暴被认为是「家务事」,歧视话语也不被认为是任何「值得大惊小怪的事」一样。这正好应验着我们之前得出的悖论:最高暴力是那规定了何谓「暴力」的东西!「阳刚之气」就是这样一种最不可见、最日常化、最有效的话语暴力:这种气质完全基于一系列排斥和支配女性的实践而生成,而这些实践又被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不断通过对话语的生产而再生产出来——在家庭和学校这两个最典型的现代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我们经常能见到以下的情形:在家庭中男孩被教导「不要娘们儿唧唧的」、「有个男子汉的样子」、「男儿膝下有黄金」,并被殷切地期待能够充实和展现自己那似乎是天生赋予的「阳刚之气」,女孩则被相应地教导「有个女孩子的样子」、「女孩要矜持一点,怎么能这么疯?」;在学校中最经典的则莫过于军训了。在军训的集中营里,高强度的操练不断压抑着和量产着「阳性人」(当然这是在小心地阉割掉了阳刚之气中有关破坏规则的部分之后实行的。在同一个「内部」中,决断者只能有一个。但阳刚之气总归是可能越轨的:日本的军队中,不是也常有「下克上」的状况出现吗?),任何对此有过体验的人都会同意这一点。而现今的许多学校不是正在将军训的内容化约散布到学校日常「纪律」之中吗?甚至在学校之中,主观的暴力——性侵害——近来不是层出不穷吗?
正是这样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不断地再生产着「阳刚之气」及其一系列意识形态话语,进而再生产着目下这种权力-支配关系。这种意识形态话语将阳刚之气这个本质上关乎权力且源于权力的实践的产物,规定为掌握了权力与进行着这种实践的性别的「特质」,就是为了将这个权力-支配结构自然化、神圣化和永恒化。如果将权力与性别挂钩,而性别又被看作是天然的、天生的,那么,权力也就成为天然的、天生的了。这就是所谓「男权天授」:既然我生来为男人,那么,我就必定拥有「阳刚之气」了。进而,我禀赋着这种气质去进行展现与培植这种气质的一系列实践,也是理所当然的了。而这种实践本身的内容就是对女性的支配,那么,我学习如何支配女性、践行支配女性的行动、总结和发展支配女性的知识、在语言中将女性预设为性与权力的客体,就更是当然的不能再当然的了!况且,这个庞大的结构——父权制正在鼓励我去展现和禀有「阳刚之气」,不但有大量潜在的或现实的顺从的女性等待我去支配,而且我不这么做还要被羞辱和嘲笑呢!这就是我们对最后一个问题的回答。
3 「它们都更糟!」:为什么不要争论「阳刚之气」和美德的关系?
我们最后简单谈谈为什么不要讨论「阳刚之气」和美德的关系的问题。让我们回想两个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的古老教诲:
第一个教诲是苏格拉底在《理想国》第一卷中说出的:「最擅长保管财物的人,也是最擅长偷窃财物的人。」[6] 最懂得如何藏匿财物的人,当然也知道在哪里如何取得这些财物。这两件事依赖于同一种技艺。相同地,我们通常所说的那些美德不也有这样的特点吗?对自己是勇敢,对敌人则是残暴;对自己是智慧,对敌人则是狡猾。「美德」这个词本身就蕴含了这种可能性:它源自古希腊语的ἀρετή,其本身并不意味着我们现在所称的「道德」,而仅仅关乎能力,即只是「善于做某事」罢了。但我们如今所说的那种,能够定义何谓道德的绝对意义上的「善」或者「好」,往往是以康德所称的「善良意志」(der gute Wille) 为指归的。即,智慧、勇气、正直、审慎等被称作「美德」的东西,如若不是出自一个善良意志,则它们并不一定就是道德的。而那不具备这些美德的人,由于他的行动基于善良意志,就也可以称之为是道德的。[7]
第二个教诲是苏格拉底在《游叙弗伦篇》中诘难游叙弗伦的问题:「好的事物,究竟是因为神认为它们是好的,所以它们才好;还是因为它们本来就是好的,所以神才认为它们是好的?」[8]
我们今天不讨论复杂的伦理学问题。我提到这两个教诲,只不过是想说明这样一件事:在不改变既定权力关系结构的前提下,语词之争毫无意义。统治者既占据了定义者这个「神」的位置,便可以预先将某些东西定义为美德,而在宣扬这种美德的时候,又把它伪装成「本来就是好的,所以是美德」的模样来偷运进我们的思维。而权力总是可以按需定义,借助此前我们提到的保管-盗窃财物的逻辑就可以做到这一点:譬如对个人卫生和外貌的美或精致的注重,被称作「娘炮」;同情心被称作圣母心 [9]。反过来,不卫生被认为是成大事者不拘小节的潇洒或「男人味」,冷漠无情被誉为强人的手腕。可见,这不过是占据霸权地位的话语根据其需要来进行解读的过程,根本不是一个经过反思而确立基本价值的过程。
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在霸权话语的框架下打转,即便是「阳刚之气不一定是男性化」这样否定的表述,也会强化这个权力结构本身。这就像是「你有没有停止殴打你的妻子?」这样的陷阱式的问题。如果回答「我没有停止」,就是在承认自己仍然在殴打妻子;反之,如果回答「我停止了」,就又坐实了「此前殴打过妻子」。无论如何回答,都是一个糟糕的局面。这时,我们要做的事只是「元语言否定」(metalinguistic negation),即:「我从未殴打过我的妻子」——「我认为『阳刚之气』是个没有任何意义的词,任何与性别气质有关的词也一样」,这才是我们应该给出的答案。如果与你辩论的人希望你与他认真地讨论「到底什么才是阳刚之气」、「阳刚之气应该留下哪些好的部分」、「哪些好的美德应该被规定为新的阳刚之气的内涵」这样的问题,那么,我希望你直接回答:「我认为这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并推荐这位人士阅读本文,避免落入这样的话语陷阱。/
参考文献:
[0] [美]哈维·C.曼斯菲尔德.刘玮 译.译林出版社.2009
[1] [美]R·康奈尔.男性气质. 柳莉 张文霞 张美川 俞东 姚映然 译 赵平 审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2] 这里请参考微信公众号「木棉浪潮哲学部」:《什么是构成性外部?》
[3] 虽然按照黑格尔的逻辑,最终这套主人-奴隶的结构会因为其内在的矛盾而解离,进而不断前进到彼此相互承认的共同体阶段,并且它从一开始就没有任何稳定性可言,不过,这不是本文所能讨论的内容。有关「究竟是殊死搏斗还是共同劳作才能取得承认」,以及「这种支配结构是否是基本的或本质的」的问题,请阅读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和霍耐特的《为承认而斗争》。
[4] [日]上野千鹤子.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王兰 译.上海三联书店.2015.
原文为「男人=不是/不像女人」。既然阳刚之气的定义是同义反复式的「有个男人样!」「像个男子汉!」,那么,在这里加入一个「阳刚之气」的常项也就很合理了。不过,「阳刚之气」在词汇类别上毕竟不等同于「男人」,所以这里给这个词加了一个括号。
[5] 齐泽克在《暴力:六个侧面的反思》中对暴力做了详细的分析。他认为,暴力不但包括可见的主观暴力(刺人而杀之),也包括支撑着「主观暴力」这个范畴的,作为「零层面」(Zero level) 的,使主观暴力成为主观暴力的不可见的客观暴力。客观暴力既包括系统性的暴力(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也包括符号性的语言的暴力(曰:「非我也,兵也。」)。齐泽克还区分了一种作为「使实在界乍现」的「上帝之脸庞」的「神的暴力」(Divine violence。这种暴力未必是因矛盾尖锐而爆发的大规模流血冲突,而是泛指社会秩序的平滑景观断裂,实在界得以曝光的时刻(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
[6]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 张竹明 译.商务印书馆.1986.
[7] 我这里的观点总体上是康德义务论式的。但我并不讨论对于共同体而言的「善」,只讨论一个人的行动怎样可以被人们的常识认同为是道德的。「好心办坏事」的情形,即便不被确凿地认为是道德的,但也并不就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而「无心之失」,则往往被确凿地认为是并非不道德的。关于善良意志的观点,详情见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
[8] [古希腊]柏拉图.游叙弗伦 苏格拉底的申辩 克力同.严群 译.商务印书馆.1999.
原文讨论虔敬,这里为书写方便,我将之化约为一般性的「游叙弗伦两难」(Euthyphro Dilemma)。
[9] 也许有人会说:只是「过于」注重外貌才会被称作娘炮,只是同情心「泛滥」才会被称作圣母心。那好,请问,这个评判「过于」与「泛滥」的标准,又是由谁或什么预先确立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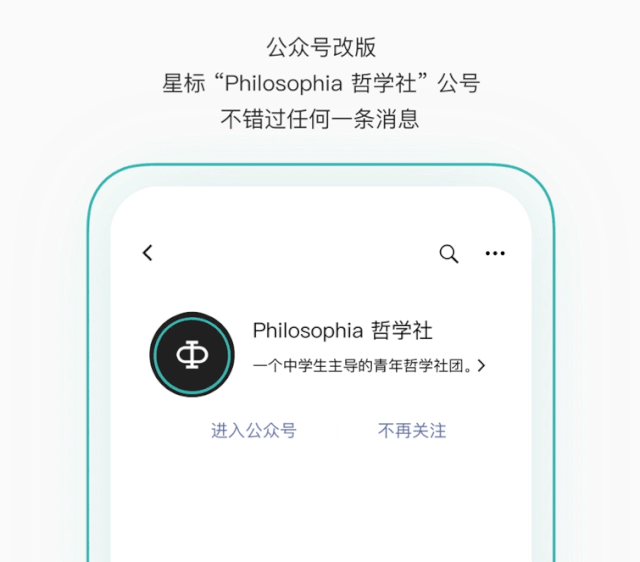

Like my work? Don't forget to support and clap, let me know that you are with me on the road of creation. Keep this enthusiasm togeth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