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和最後的
無論如何也想不到,愛過的人會把我當成對手,當成她最討厭的那個人,寫出「淹死罌粟,奪回自己的語言」。春天的時候,在紐約的氣候種下了加州罌粟,雨水連天不斷,但它們活了下來,如今不到八月,後院裡它們開了小小的深紅的花。我曾寫:
妳柔軟來到世間,全然不顧
神的妒意所降的大雨。
我可以給妳的全部,
只有粗礪的沙子,
和赤裸的心。
自然,它們不再是禮物了。我把它們和薄荷和鳶尾插在一起,罌粟花凋謝得很快,沒過幾天就只剩下另外兩種。收拾筆記,找到幾頁第一次見到她寫的紙片——我那天因為擔心說不出話,所以寫在紙上。第一句話是,「教我一句手語」。她教了我「很高興認識你」。
她後來要赴另一場約定,急急地給我唸一首夏宇的詩,但我那天遲遲也沒有答應下次再見她。我寫在手機上給她看:我害怕妳受傷。她拿走我的手機寫:不會。夏宇的詩是:
已經如此
已經這樣
片面
終止
已經如此
來不及追出去了
即使追出去也不見了
不該這樣
一定有更好的結局
這樣的城市
每天都遇見
今天一天都搞錯方向
弄錯時間
一天都不對
他先付完帳
他會在門口等我嗎
...
他不知道他可以改變某個人的命運這件事
他甚至不知道他也可以順便改變自己的
一物与另一物最大的交集
為了就是發生
發生什麼先不管
但是他付完帳完全不見了
剩下我呆在原地
世界因為他又要分成兩半
很長的一首口語詩。她唸完了,又給我看一張日曆帶打字機的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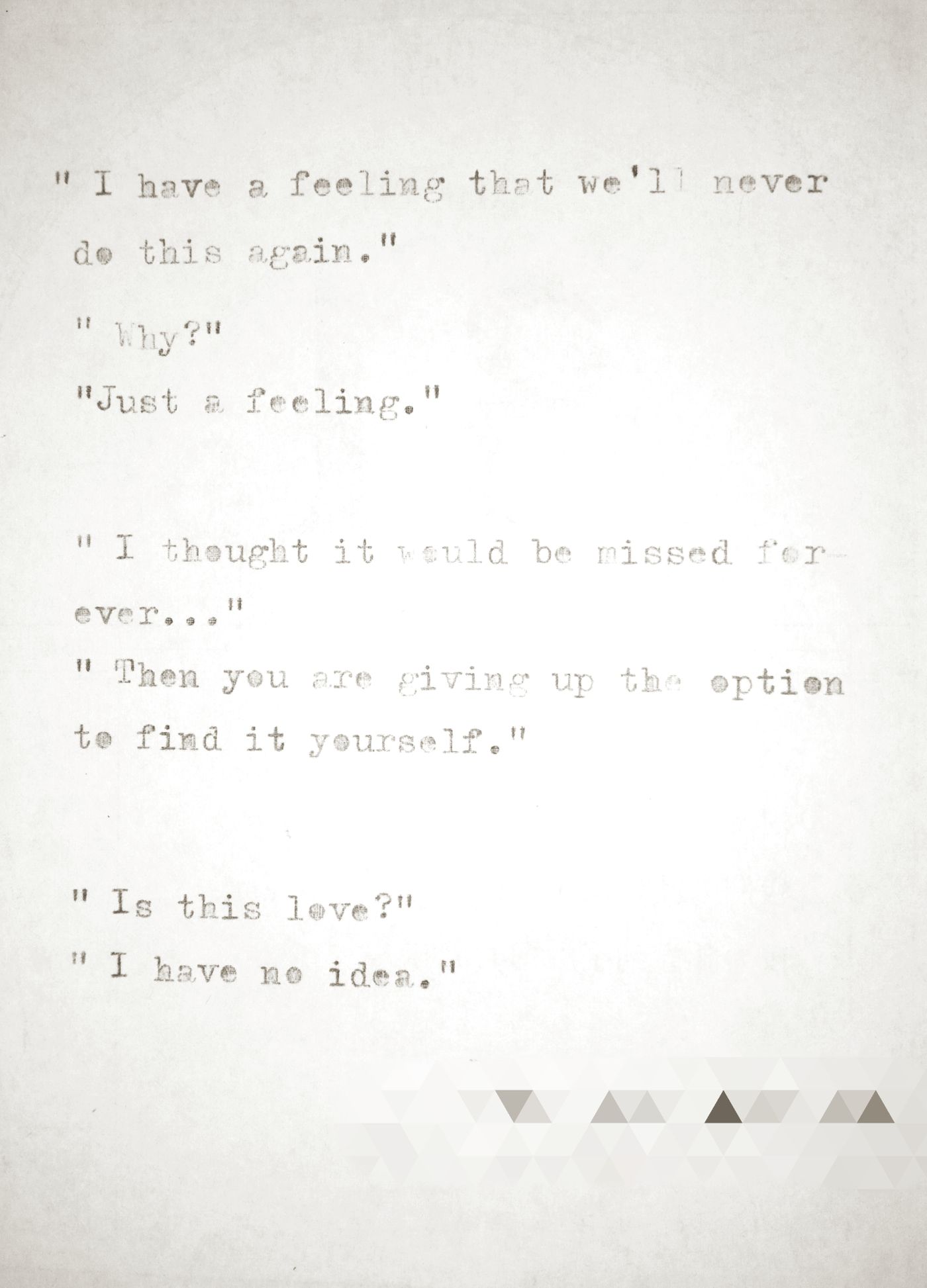
於是我後來寫了那首回應她:
我可以告訴你怎樣馴服一隻猛禽。
它還不能笨拙地回應你的手語。
它是素食和簡練的殺手,
它的殺戮不是為了食物。
你的第一個指令,
需要用幾乎是命令、要脅和懇求說——
「愛我」。
在家剪掉了兩年的長髮,只是不想在做到自己承諾的「留在紐約」之前多說什麼。以致開始了以前從沒考慮過的事情——如實在需要用錢,用一年來準備代碼面試,把靈魂賣給谷歌。在中央公園爬過 Boulder Project,所有的事情現在看起來都像是 Project 了。看過了大家提交在網上的答案,安心地發現只是需要時間。
佈展時抄著這些在牆上,天花板上,我心想,這就是最初的,和最後的了。想要記錄一個開始,再成為一個「藝術家」,被關進這個詞語的籠子裡,像很多人一樣,完成了最初的真實,就是創作的最終了。
對於被當成對手這件事,我與其說其他一切,不如說困惑。也許它和另一種陪伴沒有什麼區別,因為彼此還是成長著,誰也沒有懈怠,這樣挺好。但我不確定,它就是唯一的答案,是必須的答案,是出於怎樣的答案?誰也沒有拿走誰的東西。要奪回的是什麼?如果真要拿走,怎樣才能拿走?但既然如此,那麼好吧。承諾一個對手,公平競賽,誰也不會偷懶,誰都要保持真實。
送給你一隻破碎的杯子,
從此我再不能從杯子裡喝水,
我得到一條河流。
送給你一本空白的本子,
從此我再不能發現更多的空白來寫字。
我失去一條舌頭。
多鹽的身體不缺淚水,
在這城市,有的人來,有的人走。
一個決定。一場誤會。
從今以後我們不再知道彼此。
小小的河流,我們大海見。
這就是,最初的和最後的了。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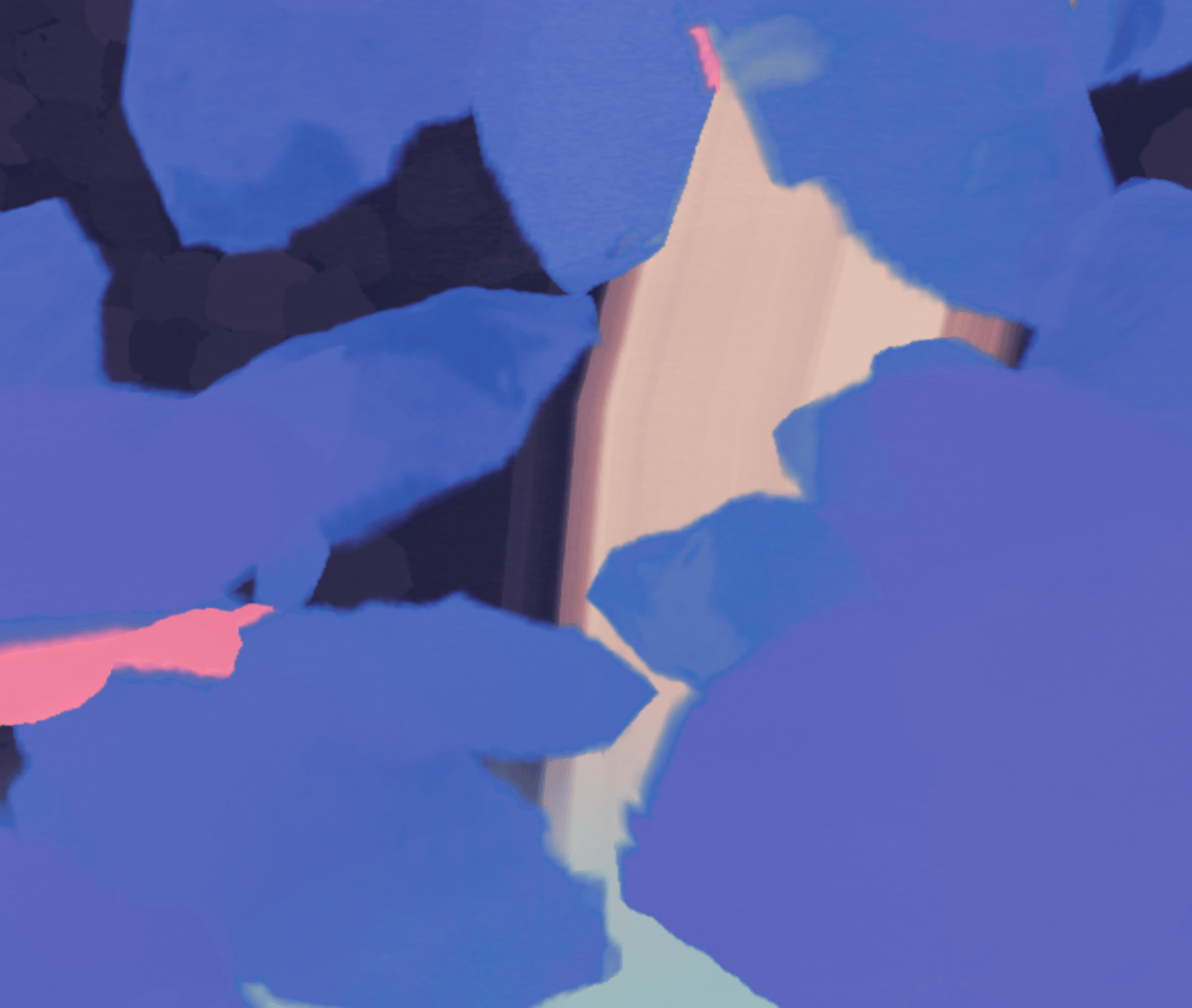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