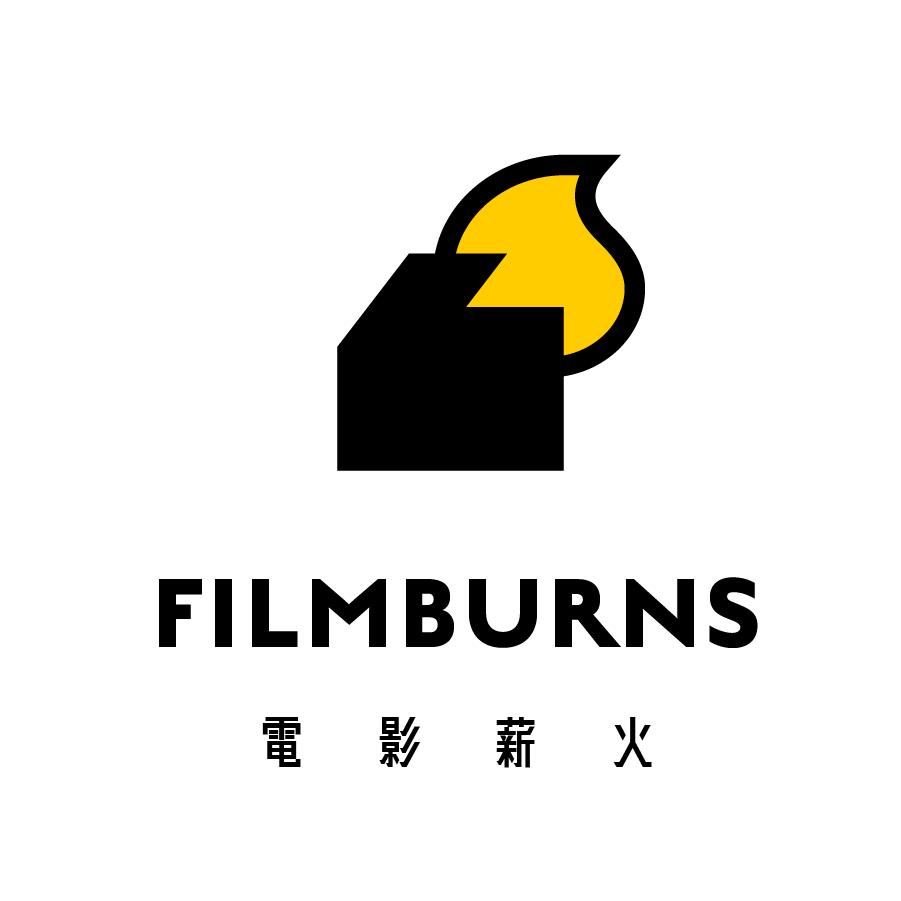《我談的那場戀愛》:原來是個幻覺和幻聽

文|查柏朗
談《我談的那場戀愛》三個有關真假的問題。劇情上的核心懸念,在於余笑琴(吳君如)與李偉祖(張天賦)的「愛情」,有真實的成分嗎?這關乎「愛情」的定義,若指某種情感連繫,觀影過程正見證其從無到有的演化。延伸再問,透過虛假的表演,能否提煉出真實的情感?從戲內到戲外,騙子集團的佈局、角色定位、道具等,都能跟戲劇世界的創作相對應。最後借題發揮,超越這部電影所能盛載的,是我們追求真實的價值何在。要過真實而痛苦的生活,還是潛進美好的幻夢裡更好?

「愛情,你信咪係真」
以余笑琴角度出發,《我談的那場戀愛》是一個剖析現今世代騙案受害者心理的文本。坊間已有歸納各種因素的討論,電影作為說故事的媒介,不靠理性點列,而是讓我們一路看著余笑琴的言行及聽其獨白心聲,去逐步發現。她的職業要保持專業拘謹、不帶起伏,致使情緒無處安放,於是空閒時更想放下精明頭腦,由感受主導;谷祖琳飾演她的唯一好友,她們都沒有談心的空間(丈夫秘書身份、網戀蜜運等都沒有和她傾談);鄭中基飾演昔日戀人的形象破滅;幾場戲一直鋪陳到浴室意外,揭示其脆弱與孤獨。她真的全程相信這個「法國工程師」嗎?因各種離譜的編造而引起的疑心,都被她的渴望蓋過:擁有一個真正關愛她而投契的靈魂伴侶。
深入挖掘受騙者心境只是《我談的那場戀愛》的一半。電影採用雙線平行敘述,觀眾以全知者姿態看到另一邊的運作,亦從李偉祖錄口供的說法帶進他的出身。余笑琴自白她的無聊空虛,李偉祖也在訴說他的無用頹廢,隨著關係發展,在自製虛浮共通點外,直到浴室那場,始揭示兩顆靈魂深處真正共鳴所在。令人聯想到 Gareth.T 大熱歌曲〈緊急聯絡人〉的訊息,兩人首次接通手機,交流脫離了文字,聽到呼吸與心跳聲,是那瞬間、那空間的真實確認。再到札幌之旅,身體距離一幕比一幕近,直至碰觸得到。從通話到接觸,全由李偉祖主導,是他的無意識還是存心?浴室戲正是《我談的那場戀愛》的類型套路轉折,關係再不止於騙與被騙,而變得更有想像空間。

「著返件衫就唔同晒」
李偉祖這人物的寫法,編導由勾勒社會現象的幽默,轉向浪漫純愛。都市寂寞人求愛的單純、真誠,感染了現實、功利、求財的虛假,像余笑琴觸動李偉祖,李偉祖觸動瓊姐(鄧麗欣)。瓊姐、白先生為首的詐騙團隊,本身設計也有別於惡貫滿盈、髒污不堪的刻版,即使是狹隘的工廈空間,都呈現得活力繽紛、花枝招展,尤其鄧麗欣造型搶眼。
不求寫實,反派討好得不成反派,輕盈地看待犯罪,彷彿大規模的網絡騙案只是背景,大局無關重要,僅是服侍主角的工具。這種久違的政治不正確精神,在《我談的那場戀愛》重新體現,繼承了陳慶嘉與秦小珍的小品傳統,也是香港電影長久以來猛烈生命力的特色。
沿此路進,商業娛樂的電影本也是一場精心吸引觀眾的騙局,只求受騙的都能在過程中得到歡愉。《我談的那場戀愛》表現的港片美學,不著重透視真實,而是追求表演效果。虛構的橋段、背後團隊的努力,讓余笑琴墮下圈套,就跟電影讓我們投入的原理相通。片中騙子的理念——穿起合適衣裝更能投入扮演角色,像穿起西裝才更能進入工作模式的心理習慣——一如演員的外型塑造。
回到前段所述,本片標誌性的時刻,因余笑琴的浴室意外而始,兩人打開了真實的情感交流。李偉祖睡在道具床,旁邊是道具鹽水,不知是因著房間道具的逼真,讓李偉祖相信了自己真的在病,過度入戲,還是李偉祖的確在發病,不論真相如何,余笑琴和觀眾們都交出真心去相信他。前者是因為故事裡的設定,後者則是受到影像表現的美術及演員的演繹而被說服。這正是電影的神奇,明明一切皆為假,我們卻能信以為真,甚至因著虛擬的情境而投射真實的感受。余笑琴在那一刻如何相信著李偉祖,我們也一樣。

「一個人嘅習慣,會變成你嘅一部分」
前提是,騙術要足夠高明,或大家一心入戲,不介意甩漏,跟余笑琴一樣,看到也假裝不見。編劇起家的何妙祺首掌導筒,調度演出與節奏尚有提升空間。有時過份著重效果,失卻自然流暢,也會教人意識到「演」的用力,當中不論吳君如或鄧麗欣,都刻意地擺某個動作(撥髮、垂手)才接對白,痕跡明顯。相對少演戲經驗的張天賦,素人質地反而更有效地無縫切換於說謊與坦白的狀態。吳君如說是因看過他在歌唱舞台上的表演而推薦他,也許正正看到他能駕馭魅力騙子與深情小子的兩面,不單在外貌,還有聲音。他那微微鼓腮、裝作無辜的表情,帶上粗框眼鏡,有時戚起一邊嘴角,同時顯現其善良與狡猾的特質。
吳君如與鄧麗欣是次皆挑戰不算拿手的戲路。近距離、面向鏡頭,無感情地述說建議給病人的醫生,讓吳君如無法表現她擅用的身體律動、豐富表情。到後來她展露愉悅時,其手舞足蹈的忘我姿態,又跟這婦科專家設定格格不入,或者是《家有囍事》形象太根深蒂固之故,無法不作此聯想。但吳君如在《江湖告急》時期,把角色的女人味、喜劇感掌握得恰到好處。所以還是專科職業這框架與她並不相符吧。到關鍵幾段高潮,失控狂罵、喝酒落淚、臥坐痛哭,終見吳君如淋漓盡致的發揮。
鄧麗欣經過 2017 年前後的轉型,逐漸確立她作為一個演員的身位。雖然接演的電影水平參差,但她當主演崗位的表現都相當深刻,電視劇亦見其絕對主導地位。在今年卓翔執導的《島嶼協奏曲》,她的部分主要由黃綺琳編劇,延續了她倆在《金都》的合作,那種如同真的在那個空間同步呼吸、存在,定義了現在最好的鄧麗欣,完全進入那領域的能量和生活感。可是《我談的那場戀愛》卻要她表演,而且是缺乏前因後果脈絡的、浮誇的。《島嶼協奏曲》的鄧麗欣是真正的演員,《我談的那場戀愛》的鄧麗欣卻是推進主線的華麗擺設。

「最想呃果個,其實係自己」
《我談的那場戀愛》的公映日,剛好也是 Gareth.T 新曲〈偶像已死〉的首播日,兩者同樣探討真假,亦可連結愛情課題。〈偶像已死〉涉及追星現象,似乎跟《我談的那場戀愛》寫沉浸幻想也一致。只是歌曲短短四分鐘就點出了全片沒有表達的,那幻想被揭破的陰暗面:「猖狂依附症,只留低毒性」。余笑琴始終相信,還似乎換來了少年的真心,若幻想沒有終結的一天,那是否就不需處理背後的毒性,始終能被控制住而不傷及他人?
旁人 / 觀眾 / 看客眼中看到的是瘋狂,當事人沉浸其中卻找到快樂,為何要刺穿泡沫幻象?回溯源頭,網騙、追星、邪教、遊戲、賭博⋯⋯甚至庸碌工作、累積財富、投入愛情、成家立室等既定軌跡,或都是填充現代人的精神空虛,找不到實在價值去實現。
周冠威的《幻愛》及《1 人婚禮》其實也持續在探討這課題,認為幻想是在逃避,應該要面對自己。但我們在逃避甚麼?胡境陽的讀劇會《案內人》提供了一些答案。跟《我談的那場戀愛》一樣,《案內人》借用了日本去當夢幻的場地,但《案內人》的日本,不只是玩樂,也有著災難的面向,從而教主角(同時是場內觀眾)重新憶起香港經歷過的重大事情。《我談的那場戀愛》不帶任何社會議題的重擔,盡責地泵好輕盈的泡泡,分離了「活在真實中」的實在痛楚,當中沒有對錯,而僅是一種怎樣活下去的態度刻劃。正如在《焦點影人吳君如》書中《變形的陶醉》一文所指出,吳君如一直貫徹始終地代言了香港社會某種層面的真實心態,《我談的那場戀愛》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