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3 | 两个女人的故事:巴西黑人女性主义人类学谱系

百年前,弗吉尼亚·伍尔夫受剑桥大学之邀,做了两场面向女性的演讲,之后成书,标题为《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她不无幽默却也相当严肃地指出,女人若要写小说,必须要有钱,还要有一个自己的房间。从我们当下的视角来看,这或多或少是一种典型中产阶级白人女性的立场,忽视了更多其他阶级、不同族裔女性的处境;但从当时而言,这种观点又充满了对男权社会的挑衅和叛逆。这一宣言意味着女性充分认识到,在争取智识发展的过程中,经济独立和空间独立的重要性。
然而,伍尔夫没有提到的是,女性的智识轨迹中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精神上的互相借鉴、扶持、鼓励和指导。用本文作者威廉斯的话来说,就是女性主义“导师形成的网络”,而这一点,在被伍尔夫忽视的其他族裔女性的生命经历中,极为重要。威廉斯通过反思两位黑人女性主义人类学家的研究,指出黑人女性主义人类学家的慷慨精神,有着维持生命的能量。而且,导师指导既可以通过非正式谈话中说的话来完成,也可以通过学术出版物中写的字来完成。
或许,正是在认可女性的创造力和慷慨分享的这些特质上,百年前的伍尔夫和百年后的女性主义人类学家会达成共识。正如伍尔夫自己在《房间》中写道,“女性身上有一种高度发达的创造力,生来复杂且强大……她们的创造力和男性的极为不同。这种力量是几个世纪的严厉约束换来的,它不可替代,如果遭到遏制或者白白浪费,那绝对是一万个可惜。”
原文作者 / 艾丽卡·L.威廉斯(Erica Lorraine Williams)
原文发布时间 / 2021年5月24日
译者 / 王立秋
编校 / 王菁
01. 导师形成的网络
当A.林恩·博尔斯(A. Lynn Bolles)邀请我来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脑中想到的是我职业生涯中有过的不同的女性主义人类学导师。与其说一个包揽一切的导师或“上师”,我更想谈导师形成的网络。

在这一点上,我沿袭了国家发展与多样性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Development and Diversity, NCFDD)的克里安·洛克莫尔(KerryAnn Rockquemore)的说法。在这方面,我还会把柳迫淳子(Sylvia Yanagisako)和宝拉·埃布隆(Paula Ebron)算进去,她们在斯坦福大学共同指导了我的学位论文。
由于加入了黑人人类学家学会和女性主义人类学学会,我和其他黑人女性主义人类学家也有交集。比如说像达娜-艾恩·戴维斯 (Dána-Ain Davis)、A. 林恩·博尔斯、伊尔玛·麦克劳林(Irma McClaurin)和乔尼塔·B. 科尔(Johnnetta B. Cole)那样的学者。虽然只有零散的互动,但她们一直是我的良师益友。一路走来,这些黑人女性人类学家的工作启发了我,给了我帮助。
不过,在这篇短文中,我将具体地聚焦于两位黑人女性主义人类学家——安吉拉·吉列姆(Angela Gilliam)和吉娅·莉莉·卡德维尔(Kia Lilly Caldwell)。她们不是一代人,但多年来,她们都是我心目中的模范和导师。
02. 两位黑人女性学者的学术经历
初次遇见吉娅·莉莉·卡德维尔的时候,我还是本科生。当时,我在做一个暑期研究项目,而她是研究生,才刚刚开始她对巴西黑人女性运动的研究。她后来的著作《巴西的黑人女性:重新想象黑人女性、公民身份和认同政治》(Negras in Brazil: Re-envisioning Black Women, Citizenship,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2007)正是我在实地考察巴西的性旅游时,心心念念寻找的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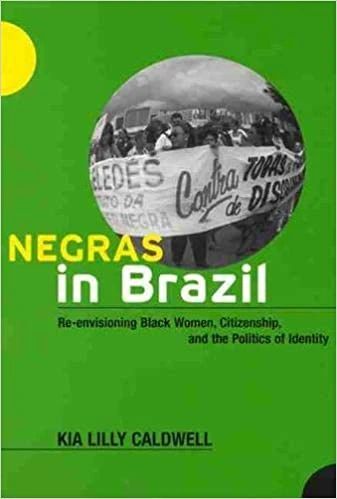
事实上,我无缘与安吉拉·吉列姆见面,但她的书为我后来在巴西做的工作提供了一个模型和基础。我第一次读到安吉拉·吉列姆的作品,乃是她的章节《在新全球文化中,关于女性被性商品化问题的一种黑人女性主义的视角》(“A Black Feminist Perspective on the Sexual Commodification of Women in the New Global Culture” )。该文收录在伊尔玛·麦克劳林的《黑人女性主义人类学》(Black Feminist Anthropology, 2001)中。我惊叹于她的智慧、风趣,还有她敏锐的分析。在这篇短文中,我会简要地谈谈这两位学者的智识轨迹,并将她们作品中对我有所启发的主要洞见稍作总结。

安吉拉·吉列姆出生于波士顿。1958年,她在UCLA拿到了拉美研究学士学位。在墨西哥国立人类学与历史学校(墨西哥城)读完民族学和人类学硕士(1958-1962)后,她到联合研究生学院读博,并于1975年拿到学位,论文做的是萨尔瓦多、巴伊亚和圣保罗的语言态度、族群和阶级,之后曾在老韦斯伯利的纽约州立大学和常青州立学院做过教员(1988-2004)。
吉列姆是真正的全球学者,她能流利地使用英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也精通法语。她还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大学(1978-1980)、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1976)和巴西利亚大学(1993-95)做过客座教授。1989年,吉列姆任当年美国人类学会年会程序委员会主席,并被选为1990年在委内瑞拉正式举办的世界考古学大会的北美高级代表(Spears 1989)。她于2004年退休并一直担任荣休教授直至2018年去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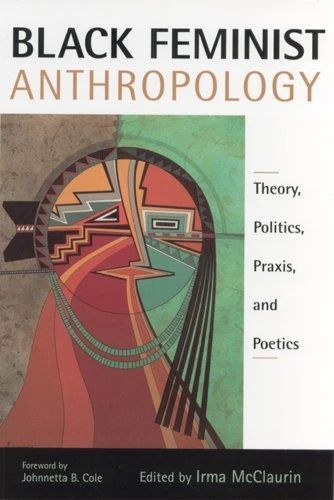
吉娅·卡德维尔本科获得普林斯顿大学西班牙文学与文明项目学士学位,硕士就读于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拉美研究项目,博士期间致力于非洲侨民研究方向,就读于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社会人类学系。目前,她已经晋升为正教授,除任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艺术与科学学院非洲、非裔美国人和侨民研究教授外,她还是负责“团队提升”的院长特别助理。除《巴西的黑人女性》一书外,卡德维尔还与人合编过《性别化的公民身份:关于知识生产、政治活动主义和文化的跨国视角》(Gendered Citizenships: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Knowledge Production, Political Activism, and Culture, 2009)和《巴西的健康公平:性别、种族与政策的交叉》(Health Equity in Brazil: Intersections of Gender, Race, and Policy, 2017)。从吉列姆在《黑人女性主义人类学》中的那个章节那里,我第一次知道了那句巴西谚语:“白种女人是用来娶的,混血女人是用来搞的,黑种女人是用来干活的”(2001: 165)。事实证明,这句谚语对于我理解萨尔瓦多、巴伊亚的性旅游经济来说,是如此地重要。安吉拉·吉列姆在阐述这句谚语的时候说:
在巴西,黑人女性的生命经常包含一个复杂的双重现实:在年轻时,她们被客体化、被描绘为诱人的混血儿,在上了年纪后,她们又被去女性化、被用来代表黑人女性养育者-保姆-佣人(2001: 169)。

卡德维尔的书《巴西的黑人女性》也引用了这个说法,但略有不同:“branca para se casar, mulata para fornicar, preta para cozinhar”——这句话出自吉尔贝托·弗雷列的《主人与奴隶》(英译版标题,从葡语翻译更常见的是《华屋与棚户》——校注)。卡德维尔是这样诠释这句话的,她指出,“非裔巴西女人的社会认同是从肉欲的角度来划分,还是与体力劳动相关,肤色是起决定作用的首要因素” (2007: 51)。
吉列姆则描述了巴西的民族文化是怎样塑造了对非裔巴西女人的情色迷恋,以及巴西政府机构是怎样通过“挑逗性地营销巴西女人”来推动旅游业的发展的(2001: 173)。多年后,在萨尔瓦多实地考察性旅游的时候,当我看到旅游区突出展示印有情色化的巴西黑人女性形象的明信片的时候,我又想起了这一点。吉列姆还讨论了“贫困的嘉年华化与巴西对旅游产业的依赖”的交织,以及欧洲中心的审美标准的影响,这些因素合力引出了性旅游业(2001: 1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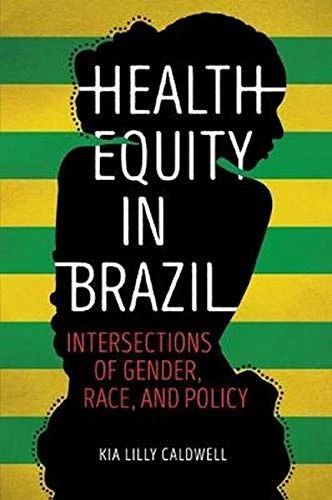
在一篇和她的女儿奥尼卡合写的开创性的文章中,安吉拉·吉列姆反思了她1963年第一次去巴西的经历。当时,吉列姆注意到“在某种程度上我看起来是巴西人,我的主体性充满了模糊性”(Gilliam and Gilliam 1999: 66)。那时,她才二十来岁,头发又长又直。她之所以会想去巴西,是因为墨西哥城的人告诉她,巴西的种族主义没有美国厉害,她可以假装巴西人。她写道,
在抵达巴西时,在说葡语的时候,我特别努力地让自己听起来像巴西人。我成功了,因为我被拘留了,他们把我当成了盗用美国护照的巴西人,更确切地说,试图向这个国家走私违禁品的穆拉塔(mulata,黑白混血女性——校注)。
(GILLIAM AND GILLIAM 1999: 67)
十年后,在巴西的军事独裁如日中天的时候,吉列姆正在边带娃边做博士论文研究(Gilliam and Gilliam 1999: 71)。事实证明,在巴西田野时身为母亲的经验,从民族志的角度来看,也是一个适于反思种族在巴西的意义的时刻。她写道:
我的身体被编码为morena(黑发或褐发的白人),而我的孩子则被编码为黑人。无论如何,看起来,人们回应我的方式,取决于我露出我非裔形状的头发还是把它遮起来。由此,头发建立了一个我们无法摆脱的定义。
(GILLIAM AND GILLIAM 1999: 72)
03. 维持生命能量的学术网络
我欣赏这些关于黑人女性对田野经历进行的个人反思。在《巴西的黑人女性》序言中,卡德维尔论断,侨民人类学家“往往要服从许多种族化、性别化的话语和实践,而我们在自己研究中着手考察的,正是同样的话语和实践” (2007: xxii)。她反思了黑人女性的性客体化如何同时影响非裔巴西女人和非-巴西黑人女性,她们经常在“巴西的种族、性别和阶级的话语中被构建为妓女”(2007: xviii)。她说出了我在田野中经历和观察到的某种东西——在巴西做田野的时候,我们身为黑人女性的认同,使我们“易受性别化的种族主义的个人经验影响”(2007: xix)。

在这方面,吉列姆和卡德维尔也是模范:她们向我们展示了,如何用我们的人类学工具包来参与学者-行动主义,以及如何跨越国界支持各种为社会正义而进行的斗争。2010年3月,吉列姆以美国女性与古巴合作代表团成员的身份访问了古巴。后来,她写了一篇关于古巴的文章,文中写道:
是时候恢复那种道德勇气和活力……加入在另一半球其他反对针对古巴的经济和政治封锁的人的行列了。无论多难,进步人士都有责任知道在拉美和全世界,别人打着他们的名义做了什么。
(2014: 180)
类似地,卡德维尔的著作《巴西的黑人女性》和《巴西的健康公平》,也为英语读者提供了关于巴西黑人女性运动的历史和发展的信息。《巴西的黑人女性》对巴西美景市的黑人女性活动家进行了深入的民族志考察,还探索了促使非裔巴西女性发展出关于种族和性别的批判意识的各种因素(Caldwell 2007: 14)。这是第一本帮助我思考“种族民主的性别化意味”的书(Caldwell 2007: 55)。也是从这本书中,我第一次理解到,在巴西,黑人性是一个“生成的”过程,用葡语来说,即assumir-se——即一个人变成黑人或开始把自己识别为黑人。卡德维尔还从公民身份的角度,分析了黑人女性的生活经验。
说到底,我做过的关于巴伊亚的性旅游的工作,和我正在做的关于巴伊亚黑人女性主义活动主义的工作,深受安吉拉·吉列姆和吉娅·莉莉·卡德维尔的工作的影响。她们为我和其他研究巴西的种族与性别的学者铺平了道路。不幸的是,我没有机会认识安吉拉·吉列姆,不过认识吉娅·莉莉·卡德维尔给了我很多快乐。卡德维尔给我写过推荐信,看过我的书稿,邀请我去她学校演讲,并一直为我提供专业的建议。
通过反思这两位黑人女性主义人类学家的研究,使我明白了以下两点。第一,黑人女性主义人类学家的慷慨精神,有着维持生命的能量。第二,导师指导既可以通过你在非正式谈话中说的话来完成,也可以通过你在学术出版物中写的字来完成。
作者
艾丽卡·L.威廉斯(Erica Lorraine Williams),斯贝尔曼学院社会与人类学系助理教授和系主任,纽约大学人类学与非洲研究学士,斯坦福大学文化人类学硕士与博士。著有《巴伊亚的性旅游:暧昧的纠缠》(Sex Tourism in Bahia: Ambiguous Entanglements, 2013)。她正在写一本关于巴西巴伊亚非裔巴西女性主义活动主义的书。
译者
王立秋,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比较政治学博士,现为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译自
Williams, Erica L. 2021. “A Tale of Two Women: Genealogies of Black Feminist Anthropology in Brazil.” In “Genealogies of the Feminist Present: Lineages and Connections in Feminist Anthropology,” edited by Lynn Bolles and Mary H. Moran, American Ethnologist website, 24 May 2021, https://americanethnologist.org/features/collections/legacies-and-genealogies-in-feminist-anthropology/a-tale-of-two-women-genealogies-of-black-feminist-anthropology-in-brazil
最新文章(持续更新)
144. 东北的今天:当代网络平台东北思想的兴起 | 东北研究 2
147. 哲学人类学|「礼物」的哲学谱系
149. 让剑道成为奥运竞技项目?——不了,谢谢
150. 反思男子气概:作为照护者的父亲们
151. 蜜蜂照料的生态化:瓦螨疫情中的多物种身体和信任关系
152. 哲学人类学 | 人类学不同于民族志
153. 两个女人的故事:巴西黑人女性主义人类学谱系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