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對動物的虧欠:從食物到寵物的動物倫理
本文以标题“你对宠物的爱,实际是自私的欲望?”首刊于新京报书评周刊
動物,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動物是人類生活中的重要夥伴,我們會與貓狗共同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同樣,我們也會將動物送上餐桌,不管這個方式友好抑或殘暴。甚至遠在草原或者深入雨林的無數不同種類的動物,都與我們的生活緊密相連。更不能質疑的是,我們人類也是動物世界中的一員。作為共同體的成員,人類應該如何對待作為遠親近鄰的其他動物,是我們無法避免需要思考的大問題,即使我們常常逃避面對這樣的問題。
哈佛大學哲學教授克莉絲汀·柯思佳(Christine M. Korsgaard)的新書《生命夥伴:我們對其他動物的義務》(Fellow Creatures: Our Obligations to the other Animals)正是直面這些問題的新嘗試。柯思佳是道德哲學領域的佼佼者,對康德倫理學的詮釋喝發展影響非常大。在她的新書里,她嘗試從康德式的道德義務出發,重新奠基我們對其他動物的道德要求,通過嚴格的道德哲學論證來探討公共議題,從抽象的動物倫理到具體的素食與善待動物運動。無論是道德哲學研究者還是普通的讀者,都可以從這書中獲益。
要深入柯思佳的《生命夥伴》所討論的議題,我們就不得不首先瞭解動物倫理或者動物解放這一議題的討論背景。在這一背景中,最耀眼的當數澳大利亞哲學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他的名著《動物解放》(Animal Liberation)堪稱是引起了革命的哲學著作。「這本書旨在討論人類對非人類動物的暴行」,辛格在此書1975年初版序中點明瞭目標。
辛格的動物解放革命:效益主義的動物倫理
引起「革命」的《動物解放》實際上論證結構上十分簡明。在辛格看來,最基本的原則是,痛苦是壞事情,是負價值。我們不應該在世界上徒增不必要的痛苦。而人類對待動物的各種行為恰恰給動物帶來極大的痛苦,而且這些痛苦毫無必要。
在書中,辛格給我們展示了我們對待動物時候的殘酷,例子數不勝數。不管是軍事領域還是科學領域,我們都經常使用動物進行殘暴的實驗,比如書中描述的對動物釋放毒氣、放射線等等。而且,正如辛格展示那樣,這些實驗往往並沒有準確的實際作用。
我們將動物變成餐桌上的食物的方式,同樣也是極其殘忍。我們想象中,城市人熟悉的動物好像都悠閒地生活在浪漫的農場里。然而實際與我們的想象相距甚遠。日常消費的蛋奶肉品,基本來自工廠化農場和流水線屠宰場。在這些農場里,蛋雞被強迫在日夜顛倒的日光下不斷產蛋,甚至固定得絲毫不能移動。肉雞在擁擠的雞場雞籠里無法伸展。豬被不斷餵食,但又不能走動。小牛剛出生就從母親身邊被帶走,在屠宰場里變成餐桌上的高貴食物。更別說在屠宰場中產生的動物承受的痛苦。正如保羅•麥卡尼(Paul McCartney)的記錄片《如果屠宰場的牆是透明的……》(If Slaughterhouses had glass walls…)記錄的情景一樣,那些痛苦既巨大,又毫不必要。
所以,在一系列的經驗事實之下,辛格可以總結,既然我們對待動物的這些方式對動物產生如此巨大的痛苦,我們就應該至少停止這些活動。這些活動,首當其衝就是那些殘酷的動物實驗,還有我們因食用動物和使用動物製品而帶來的殘暴飼養。素食主義是辛格的動物解放所指引的首要行動。
辛格的論證是典型的效益主義論證。在效益主義者看來,世界上存在著客觀的價值基本單位:效益。而道德的行動,就是做能夠帶來最大效益的行動。效益主義的基本原則非常貼近我們日常的直覺,正確的行動就是能夠帶來最大好處的行動。跟利己主義不同,效益主義堅持客觀的價值,所以最大好處或者最大效益應該是客觀上所有效益的考量。按照辛格的理解,最基本的效益是世上的快樂,以及免除痛苦。既然如此,減少世界上的痛苦便是道德上應該做的事情,不管這些痛苦的承受者是人還是其他動物。一視同仁對待所有痛苦,是辛格觀點中對待動物的平等。
柯思佳的動物倫理:從康德式義務出發
辛格的效益主義論證十分直接和間接,是奠基動物權利非常有效的哲學基礎。不過,儘管在很多方面同意辛格的動物解放,例如停止因食用動物和使用動物製品上帶來的殘暴飼養,柯思佳反對辛格觀點背後的道德基礎。最明顯的一點是,柯思佳並不同意存在毫無差異的價值基本單位,特別是跨個體之間的價值比較,並非如辛格的效益主義所描述的那麼簡單。
從她對康德的道德哲學的詮釋出發,柯思佳認為,所有的價值都必須是捆綁的(tethered)。簡單來說,所有的價值都是與個體相關,也就是所有的價值都是「對她有價值」(good-for)。柯思佳認為,從定義上講,動物就是具有最終價值的東西,所有事物的價值都因為對她重要而出現。書對我重要而具有價值,貓薄荷對我的貓重要而具有價值。正因為這樣,辛格的論證設定了獨立於任何個體的價值——快樂或者免除痛苦——而有問題。任何的價值,都因為與之捆綁的個體才出現和有意義。
不過,雖然價值是捆綁的,這不等於說價值完全是個體意願決定。某些事物可以同時對於多個個體而有價值。一個安靜的環境對於整個校區的居民都重要,因此對她們有價值。城市的空氣質量對市民有價值。價值是捆綁的,只意味著價值的源頭來自於與之相關的主體。價值並非無源而生。正如柯思佳所說,我們追求所謂絕對的價值,其實就是追求對所有個體都重要的價值而已。如果我們能夠找到對所有個體皆重要的事物,這事物自然具有對所有個體都重要的價值(good-for everyone)。
如果價值是捆綁的,那麼那些認定人類的生命價值高於其他動物的生命的斷言,就會是錯誤的,甚至,柯思佳認為,這些比較本身就是沒有意義的。反對動物權利的一方,通常會嘗試通過說明其他動物與人類之間的差異,來說明人類高於其他動物。這種高於不僅僅是能力上的比較,而且還是道德地位上的比較。我們可以承認,人類與其他動物之間具有不少的差異,包括身體能力和認知能力上的不同。但這些不同往往不能推導出道德和價值上的高低。如果要斷定,人類具有更高的認知能力,因而比其他動物價值更高,柯思佳的第一個反問便是:對誰價值更好(good for whom)?我們的生命(以及生命中的價值)對我們來說具有價值,甚至比其他動物對我們來說更有價值,但我們不能忘記,動物並不單單具有工具價值(柯思佳用的是functional good),而且還是價值之源。這意味著,其他動物的生命對她們來說具有十分高的價值,因為生命中包含著各種對他們十分重要的事物,同樣甚至比我們的生命對她們而言更有價值。僅通過工具價值意義上的重要性來比較人類與其他動物的生命價值的高低,是有問題的。
同樣的,我們的生命對我們的價值,比其他動物的生命對其他動物的價值更高,這樣一種捆綁式價值的比較也是有問題的。作為價值之源的人類,可以將看到的世界詮釋為具有賦值的世界(valenced)。不同事物具有不同的價值,我們生命也是。我們的生命具有價值,生命中包含的不同事物具有不同的價值。而同樣地,同樣作為價值之源的其他動物,也可以看到具有賦值的世界。為了讓生命的功能持續,其他動物眼中的世界同樣因此具有不同的價值:從食物、到飲水、到居住地、到天氣、到同伴等等,都是對她們具有不同價值的事物。她們的生命對她們而言具有價值,她們的生命中包含著各種不同的價值。我們如何能夠說,我們的生命對我們的價值,比其他動物的生命對她們的價值更高呢?
在柯思佳看來,人類比起其他動物而言,在這方面的區別僅僅是我們具有理性的能力。這種理性的能力讓我們能夠去反思我們去賦予價值、去行動的方式。換句話說,理性的能力使我們能夠反思我們的理由,讓我們的信念、思考、行動更融洽。我們可以去評價我們的信念與行動,進而去評價我們自己。但是,這一點並沒有影響價值本身。其他動物或許不能反思去覓食或者去休息背後的理由,然而這遠遠不等於覓食或休息對她們而言沒有價值。事物對她們而言仍然是「要躲避的」,「要追捕的」,「要深究的」,「要照顧的」,等等等等。這只是兩種不同的心靈而已。
如果我們具有應有的共情力,我們就應該可以理解,其他動物的生命對她們而言所具有的價值,也應該可以理解,她們的生命會為她們帶來怎樣的生命經驗,綻放抑或悲慘。她們的生命和生命經驗對她們的價值,與我們的生命和生命經驗對我們的價值,同樣的真實和重要。去比較這些價值的所謂絕對高低,是有問題的,而且毫無意義。我們不能用僅適用於我們的評價標準來判斷動物的生命價值更低。
從上面的論證來看,柯思佳論證動物權利的哲學基礎與辛格的理論的確不同。柯思佳不承認獨立於所有個體的價值標準,而是從康德式的道德哲學出發,說明所有的動物本身就是價值之源,反駁對人類和其他動物價值高低的比較。避免了使用效益主義的計算式策略,柯思佳的觀點似乎更尊重動物個體,而不僅僅將動物視作快樂與痛苦的單純載體,也比辛格的論證更可以強調動物生命本身的價值。然而,即使她在書中嘗試修改和發展康德的理論,柯思佳的論證仍然遺留很多康德式的人類中心主義。正如芝加哥大學教授瑪莎·努斯邦(Martha Nussbaum)指出,柯思佳的論證仍然是通過動物與我們的相似,以及我們對於動物的共情,而給予動物道德上的尊重。柯思佳認為,即便動物沒有道德能力,具有道德能力的我們仍然可以動物納入到道德考量之中。這一點或許就是努斯邦說不滿的地方。努斯邦認為,我們對動物的尊重應該來自己於動物本身,以她們的能力(capabilities)出發。另外,柯思佳的理論借用的是一種非常具體的關於個體和價值的觀點,在今天的價值多元社會,甚至極化的社會中,能否提供有效的公共原則,似乎是值得懷疑的。儘管柯思佳的理論會得出同樣的結論,但似乎依賴更少價值前提的辛格的效益主義理論更能成為有效的公共原則。
從餐桌上的食物到陪伴左右的人類朋友
柯思佳的新書不僅只是給出關於動物權利的不同道德理論,而且還認證討論了具體的動物倫理議題。從餐桌上的食物,到陪伴我們左右的寵物,都是非常具體的問題,而且這些問題都與我們息息相關。
關於食用動物的問題,已經是大家熟知,並且已經常常出現在公共討論之中。科學早已表明,人類所需要的營養,基本上不需要通過食用動物就能充分獲得。食用動物,往往只是出於我們對食物味道的追求和習慣而已。因為對肉類食物的市場需求,我們過分地殘酷飼養動物,對動物施加了極大的痛苦,同時也將動物的生命視作人類使用的簡單工具,無論辛格的效益主義還是柯思佳的康德式道德,都會極力反對。既然這些都是毫無必要的錯誤行為,我們就很有理由去反對食用動物,特別是像玉林狗肉節這些近乎瘋狂的宣示式過分屠殺,更加需要強烈反對。
但是,陪伴我們左右的寵物,我們有應該如何對待呢?在某種意義上,養寵物是沒有進化論意義的。正如動物人類學家赫爾·赫索格(Hal Herzog)在《那些我們喜愛、討厭、食用的動物》(Some We Love, Some We Hate, Some We Eat)所說,人類飼養寵物花費很多時間、能量和資源,但是它們對我們的基因的延續並無貢獻。所以,養寵物除了某些少數的效益以為,更多是為了與我們相伴。寵物更直觀地是我們的生命夥伴,所以我們應該如何對待它們,甚至,我們是否應該留養寵物,不可避免地需要我們去思考。
應該如何對待寵物,這是爭議相對較少的問題,儘管爭議仍然存在。正如喬治·華盛頓大學哲學系教授戴維·德格拉齊亞(David DeGrazia)在他的《動物權利》(Animal Rights)所說,留養寵物最基本的兩個條件是,我們要滿足它們的基本生理和心理上需要,並且我們要為它們提供跟野外生存至少同樣好的生活。柯思佳認為,寵物生活在文明社會裡面,的確是享受了很多從它們的角度看也很有價值的好處。社會為寵物提供了醫療、壽命延長、遠離捕食者、持續提供的食物等等等等。要讓寵物在社會中獲得好的生活,社會仍然需要做得更多,包括我們社會結構上調整,來保障寵物的福祉,為它們提供所需要的社會服務,例如地方社會補貼提供低廉的絕育服務,動物救助中心等等。個人生活可能也需要作出改變,畢竟(我們也需要意識到)留養寵物是一種責任。
而至於我們應否留養動物,德格拉齊亞和柯思佳都並沒有很明確的答案。善待動物組織(PETA, People for the Ethical Treatment of Animals)在官方網站上的宣言表示,我們擁有動物並從它們身上索取愛,其實是一種自私的慾望,甚至會對它們產生不可比擬的痛苦,「從操縱它們的繁殖配種,任意販賣動物,到剝脫它們在自然環境中生活的機會」。所以我們應該逐漸廢除人類留養動物的習俗和實踐。
或許善待動物組織的立場聽起來比較激進,像貓、狗這些已經高度馴化的動物,我們無法將它們簡單放回它們的「自然環境」之中,它們可能無法單獨在野外生存。但這未必不可能,比如我們可以幫助建立屬於這些寵物的保留區域,給予它們必要的支持,讓它們更自在地生活。不過,應否留養動物,仍然是個沒有得到充分公共討論的問題,答案就更加不確定了。
如何對待動物,是我們每一個自稱更進化的人類說需要思考的問題。文明社會意味著我們不再生活在虛構出來的「叢林法則」之下,作為人類生命夥伴的其他動物,需要和值得我們更多的尊重。我們的確無法改變過去我們殘暴對待動物的歷史,但我們能夠改變當下,塑造更好的未來。如果我們虧欠其他動物什麼,那應該就是我們尊重它們生命的義務了。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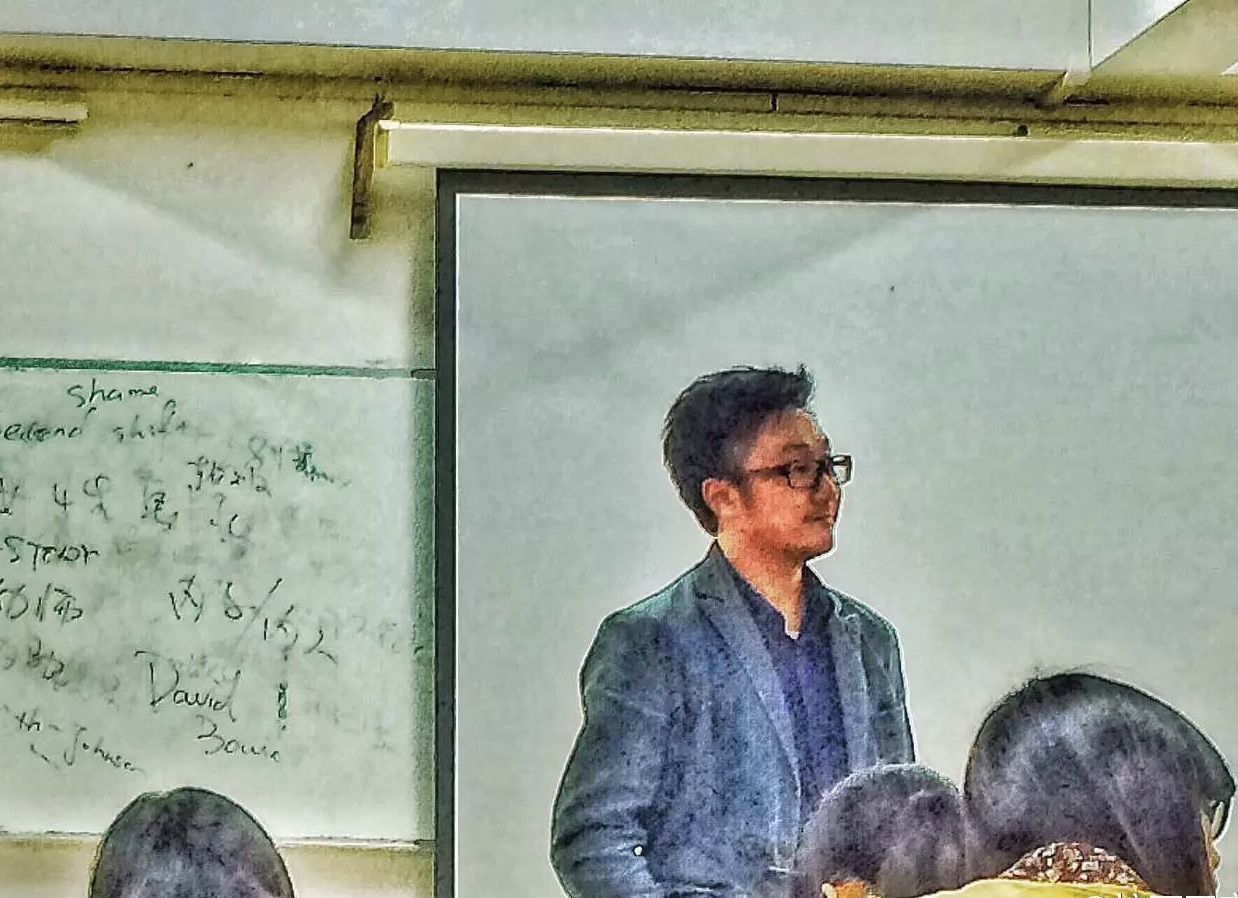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