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吧!?——愛國主義與世界主義(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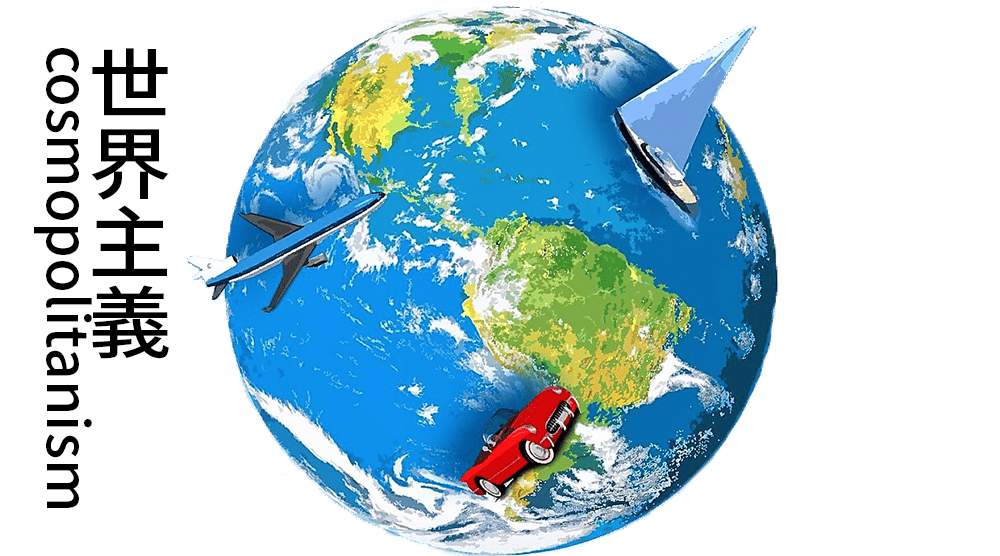
文|豬文
難度:★★★★☆
問:「你認為自己是美國人還是中國人?」
李小龍:「我想,我就是一個人類。在天空底下,就只有一個家。人成為不同的人,不過是偶然。」[1]
前言
國族身分是個極其麻煩以及深入的哲學問題。關於國族身分,我們第一個想到的問題可能是:如何界定一個國族?我們的國族身分是被給予的,抑或是自願?這個問題在兩岸三地的政治環境中,尤其敏感。究竟你是中國人?香港人?台灣人?既是中國人又是香港人?華人?這些爭拗,充斥於我們的社會。明星稍一不慎,說出一句「不用分得那麼細」,立即會被一地網民罵到狗血淋頭,但又會被另一地網民搖旗助威。
撇開這個如何界定國族與國族身分的問題,假設我們都對誰是甚麼人有很明確的答案,還有另一層同樣關鍵的問題:我們應該如何對待這個國族身分?似乎在思考道德、政治、甚至日常生活的問題時,國族身分都是很重要的考慮之一。我們會認為,因為自己是香港人,所以應該支持香港足球隊;因為我是台灣人,所以我應該支持台灣在南海爭取更多利益的政治舉動;因為我是中國人,所以我應該對其他中國人關愛更多。
歸根究底,這此想法都指向一個基本問題:我們應該擁抱自己的國族身分嗎?忠於自己國族這個群體是一件好事嗎?用最日常的語言來說,愛國是一種美德嗎?[2]
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
「她走在一條長長的林蔭大道,這是前往位於耶路撒冷的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必經之路。兩旁的樹,都有一個號碼,一個名字,一個地方。在 1995 年 12 月,這裡總共有一千一百七十二棵樹。每棵樹都向一位曾經賭上生命危險來拯救猶太人的人致敬。這些人都不是猶太人。他們可能是法國人、比利時人、波蘭人、斯堪地那維亞人、日本人或者德國人。他們也可能是無神論者、基督徒或其他信徒。他們都有自己的限定身分(local identities)、國藉與宗教信仰 …… 這些人都不需要如此做。所有考慮都指着另一個方向。但不知怎地,他們的想像力達到某個高度,超越了國族、宗教甚至家庭的呼喚。他們肯定了人類本身的價值,也以此作道德呼應。」

這個故事是美國哲學家 Martha Nussbaum 在一本經典小書《For Love of Country: Debating the Limits of Patriotism》最後一章的開首,大抵表達了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的核心精神:我們最重要而根本的身分是世界公民(world citizen),其他一切例如國族身分(national identities),在道德價值上都是次要,甚至無關痛癢。
世界主義認為,真正值得我們擁抱的不是某國族身分,而是世界公民;真正值得我們效忠的團體不是某個國族或政治組織,而是一個由所有人類組成的道德群體(或康德所說的「目的王國」);真正的道德呼喚對象不是我們的同胞,而是人本身。
當我們能夠忠於世界公民這個身分,如實地回應人的道德呼喚時,我們不會因某人的國族身分而有差別地對待。在世界公民的眼裡,每一個人的福祉都是同等重要,每個人的尊嚴都同樣重要。道德責任不單連繫着我們的同胞、朋友與家人,更牽連了所有世界公民。
從愛國主義者的眼中,那些賭上生命危險去拯救猶太人的行為或許不值得嘉許,因為自己國族的人理應才是要照顧的人。寧願救助非他族類的人,某程度上便是對自己的國族不忠。然而,對世界主義者來說,那些人卻是理想的世界公民。他們並沒有將自己的道德責任限於自己的國族,而是超越了國族、宗教甚至家庭這些身分的桎梏,平等地看待所有世界公民。
那麼,為甚麼世界主義值得我們支持?
世界主義對嗎?
世界主義最大的吸引力在於,世上所有人都納入了所有人的道德考量範圍之內。換句話說,不會再有任何人會被排除在我們的關心之外。正如共同的國族身分,可以使國族內不同的成員連在一起;世界公民這個由所有人類共享的身分,也可以使所有人連在一起。
世界上有大量與我「無關」的人,我和他們並沒有諸如國族般的聯繫。如果最首要的道德身分是我的國族身分,而我只對同胞有道德責任的話,那麼我其實並沒有理由關心與幫助非我族類的人。世界主義的重要,在於即使人無可否認地只有理由關心自己群體的人,但群體內的人不必只是同一國族者 ── 世界主義指出了不同國族的人,其實全都屬於世界公民這個更大的群體。當世界主義指出我們重要而根本的身分是世界公民時,其實它已經把所有人都帶進了我們的道德考慮範圍之內,不會有任何一人被遺留。這是支持世界主義的首要理由。
除此之外,世界主義者認為該理論有助我們認清自己(Nussbaum 指出這種想法早在古希臘的斯多葛(Stoic)學派已提出)。解釋這想法前,不妨想想:究竟我們作為人類存在最根本的價值是甚麼?究竟是甚麼使我們的存在變得有尊嚴,所以別人應該尊敬與關愛我們?我們應該引以自豪的東西是甚麼?

世界主義認為答案便是人類的道德意識與理性思考能力。我們作為人類,有別於世上其他東西,就在於我們會思考道德上的對與錯、事情的好與壞,並且能夠抽離地檢視不同理據,與他人理性討論,追求真理。這些能力構成了人之為人的尊嚴,也構成了世界公民這個身分的內涵。相比懂得說廣東話、懂得欣賞周星馳的電影、聽得懂王菲的音樂這些構成國族身分的能力,上述的普遍能力可能略顯冰冷而平淡。但是,這些能力才是我們作為人類最深刻而不可劃缺的能力。我們值得別人關心與尊重不在於懂廣東話,卻因為我們是一個道德與理性主體。也因此,我們也應該真摯地認同世界公民的身分,而非香港人、台灣人、中國人之類。
從反面來說,愛國主義會使我們不能認識自己。如果我們都只會抱持香港人這個身分,只以香港人的眼光認識香港人的話,則會忽略了香港人身分的內涵如講廣東話或其他習俗只是限定而偶然(local and inessential)。一旦無法理解到這些特質只是限定而偶然,我們便會被這些特質所蒙蔽,誤以為擁有這些特質的人才有(更高的)道德地位。對於自己的道德及理性思考能力,反而懵然不見。
上述這兩個想法(我們關心既對象應該是所有人,且人之為人的價值在於我們的理性),構成了世界主義的基礎。
扔掉國族之後要扔掉家庭嗎?
當世界主義主張我們最重要的道德身分就是世界公民時,意味着我們最根本的道德責任指向全世界的人類。凡是世界公民,對作為世界公民之一的我,都應該有道德地位,而且是平等的道德地位。那麼,世界主義者會說我們應該放棄予自己家庭成員、國族成員特殊關注嗎?的確,有些限定身分我們大抵都會同意是道德上不相干的,例如性別。我們不會說同性別的人對我來說有較重的道德地位,而值得給予較多關注。
可是,在日常道德生活中,一些我們比較重視的限定身分又如何呢?我們都應該放棄這些身分,一律給予世界公民平等的關注嗎?世界主義似乎難以避免這個結論。甚至,一個徹底的世界主義者會說,不單性別、國族,連家庭都不值得有任何額外的關注。也就是說,我應該關注自己媽媽,不是因為她是我的媽媽,而是我和他都是世界公民,就像為甚麼我應該關注男性,不是因為他是男性,而是我和他都是世界公民。在一個陌生人跟我媽媽之間,沒有道德地位上的高低。

這個結論似乎很難被我們接受,也與我們的道德經驗相去甚遠。那麼世界主義會怎樣理解這個問題?Nussbaum 便認為,世界主義其實可以同意我們應該給予自己的家庭成員與國族成員更多關注。在幫助也門與自己的小孩之中,我們應該投放更多時間與資源在後者。
為甚麼世界主義可以這樣說?Nussbaum 認為,世界主義反對的只是這些限定身分本身有額外的道德地位,亦即是說,它反對的是自己的小孩本身比也門小孩在道德上比較重要、較有價值。我們在行為上仍舊可以投放更多資源關注家人或同胞,但箇中真正理由,是因為這是唯一可行的行善方法。
基於資訊的不平均,世界公民這個群體變得美好的理想,也需要世界公民的「分工合作」。我的小孩,作為世界公民的一分子,無論如何也需要有人照顧。我自己作為世界公民的一分子,無論如何,也只有這麼多的資源照顧某個世界公民。剛巧我是我的小孩最親近之人,也最易把照顧他這件事做好。順理承章,我便應該優先投放資源照顧我的小孩。如果我不這樣做,反過來把有限的資源分散給世上每一個孩子的話,世上每個小孩得到的幫助只會小之又小。到頭來,我對世界公民這個團體的貢獻反而會更加少。(再設想一下,那些對自己國族有重大貢獻的人,情況也是一樣。若甘地不把一生都投入在幫助印度人的理想上,而把他的努力平均分配給世上所有人,他對世界的貢獻會增加還是減少?)
因此,世界主義一方面可以認同我們可較關注身邊的人,但另一方面卻堅持我們的家人、同胞不比他人重要。不論家庭,不論膚色,只要他們是人,他們只是地位平等的世界公民。
愛國不單不是美德,更是一種罪惡 ── 自由主義式的道德觀
討論至此,我們大概可以猜想到世界主義會如何理解愛國這個一般會視為德性的東西:對世界主義來說,愛國不單原是美德,更是一種罪惡(假設這裡的愛國不是上述那種策略考慮)。因為愛國的態度,完全違反了世界主義背後的自由主義(liberalism)道德觀。
回想一下,我們平常如何理解何謂「作出道德判斷」?假設一個人說:「同性戀在道德上是錯的,因為我是異性戀者。」他是在作道德判斷嗎?似乎我們都不會覺得他真的在作道德判斷。假如他說:「同性戀在道德上是錯的,因為我不喜歡。」 我們仍舊不覺得他在作道德判斷。如果他說:「同性戀在道德上是錯的,因為同性戀會加深性病傳播,影響人類的幸福。」姑勿論這個論證是否有理,我們都會認為這個判斷與前面兩個不同 ── 是一個道德判斷。
上述區分顯示了很重要的一點:從道德的觀點去判斷事情,等同是從非個體(impersonal)的觀點作判斷。從非個體的觀點去作判斷,即是要我們撇開個別的利益、感覺、社會地位等因素,像任何一個理性存在者般作判斷。所以,若我們要作道德思考,我們要做的便是要撇開那些偶然且個別的事實:要從道德的觀點看同性戀,我不能從我作為一個異性戀者的觀點看,而是要抽離我是異性戀者這個事實,達至到一個不管自己是異性戀抑或同性戀的理性存有者的觀點來審視。
如此一來,這種道德觀自然容不下愛國主義。因為愛國主義要求我忠誠於我的國族,你忠誠於你的國族。我在哪裡出生、受哪個政府管治、屬於哪個國族、父母祖先是誰,這些都只是賦予在我身上的偶然事實。但愛國主義卻要求我擁抱這些事實,容許偶然的國族身分,決定甚麼行為是道德上正確或值得嘉許。「投身國軍是善行,因為這幫助了我的同胞,是愛國的行為」在世界主義者的眼中,與上述「同性戀在道德上是錯的,因為我是異性戀者」一樣,都只是從個人(personal)的觀點作判斷,既非道德亦不理性。
所以,世界主義不單不支持愛國,甚至視這種態度為罪惡。

未完的討論
不過,作為世界主義背後支柱的這種自由主義式道德觀,真的是唯一站得住腳的道德觀?其實不然。
社群主義式(communitarianism)的道德觀正正提供了另一種對道德可能的理解。正如自由主義式道德觀支撐了世界主義,社群主義式的道德觀也成為了愛國主義的重要基礎,也使雙方的辯論變得不分軒輊。欲知對決發展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注腳:
[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9KvUSK4dAw
[2] 為方便起見,本文並不把國家與民族作區分。雖然,國家與民族顯然為兩個概念,通常前者指政治實體,後者指由血緣或文化或政治理念所維繫的群體。而且,民族主義亦時常出現於尚未建立起獨立國家的民族,例如加泰隆尼亞人、庫爾德人。所以,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並不等同。不過,近代的哲學討論,時常將兩者一併討論,因愛國主義者與民族主義者要求我們效忠的對象十分相似。一方面,愛國主義理解的國家,並不是單純一個政治實體。國界的區分很多時候都是任意的,而且時刻在變。愛國主義者實難以證成我們應效忠於這任意的東西。另一方面,近代的民族主義亦鮮以純綷血緣定義一個民族,反而多強調民族的文化面向。結果,愛國主義的國家與民族主義的民族,都是指向同一個東西:一個有共同文化、歷史、生活經驗的群體。本文一律稱此群體為「國族」。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一律稱為「愛國主義」,意指一種認為人應該對自己的國族持有肯定態度(pro-attitude),並在道德與行為考慮上給予自己國族成員更多重要思想。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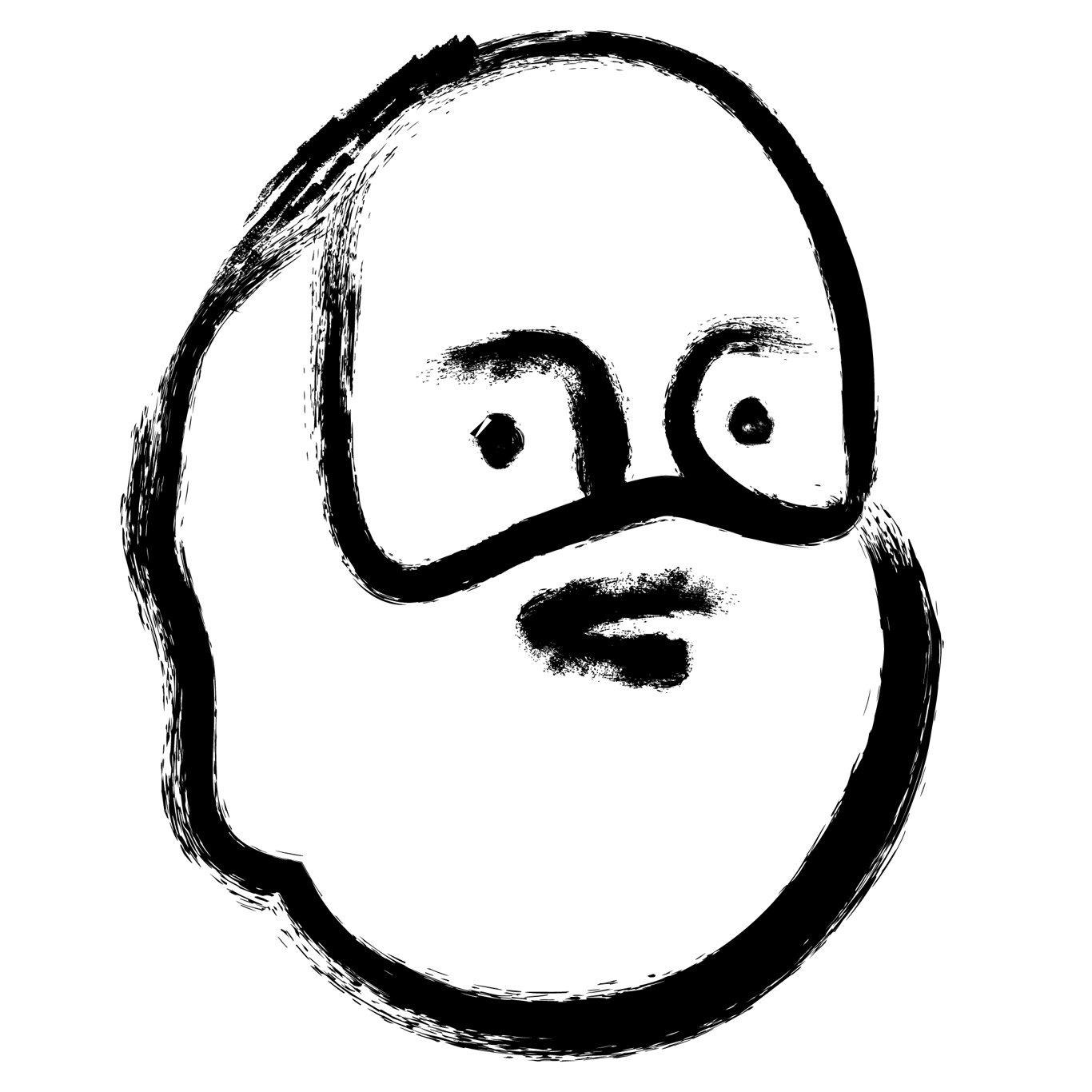
- 选集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