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日书第四天 - 睽违五年,或者更久
如果你的胃有不必然和你相同的身分認同,它的認同是甚麼?是怎樣形成的?
来日本已经第五年了。
我很难说我的身份认同是什么,作为女权主义者的话,我会流利地回答:“作为女人,我没有国家。”但这是一种错位的诡辩,它其实并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我是谁?”
日本是一个处处提醒你是异乡人的地方。讲话的口音、遣词的习惯、不熟练的文法,乃至鞠躬的动作和角度,还有寒暄的开头:你是哪里人?
暴露得太快了。我不是日本人。但我也说不出“我是中国人”这句话,特别是在2018年习近平修宪后,2019年香港反送中事件后,2020年武汉封城后,2021年中国外交部长会见塔利班外长后,2022年上海封城后,2023年编程随想被捕后。“我是中国人”这句话,变得越来越难说出口了。这简直是一个耻辱。
不只我是这样的。我知道还有一些人,激烈反对中国以及和中国有关的一切,他们往往会向往并“认领”另一个国家,努力让自己成为那个国家的人,特别是从精神上。无意评判他们的做法,但我确实对“我是哪里人”的态度不太感冒,对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地区都没有向往,也不喜欢这样的归属感。
大概是因为,我是一个被我的故乡拒绝的人。我在日本是异乡人,在故乡也是异乡人。归属感从来就不是我的人生字典里会有的词。
我是闽南人。刺桐花花开满城,小时候不知道那是花,只觉得是树受了伤,爆出了巨大的血痂。原来,树跟我一样,也会受伤吗?我想我永远都不会知道答案。树沉默不语,只会摇动树叶,在风里用我听不懂的语言窃窃私语。
更常见的是榕树和红砖。榕树的气根绵延数尺,投下巨大的荫庇。红砖掩映在树冠之间,翘起的翼角呈现优美的弧度。有儿童在树上爬来爬去,女人们则在树下交流哪里的超市打折。男人们大多卷起汗衫下摆,打着蒲扇,四仰八叉地靠在竹椅子上,从2亿的生意谈到国家运势。石板是花岗岩,蹲在地上看的话可以看到一些细小的晶体在阳光下闪烁。如果不慎跌倒,砂石会挂在伤口上,不冲洗干净的话可能会长进血痂里。
榕树是公共客厅,红砖则是大家各自的家。但我不具备进入这个客厅的资格,因为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外语的世界。
闽南人都说闽南语,但我不会说闽南语。
我是这个联系紧密的社区中的异质。大家说话时,我只能在旁边尴尬地笑,嘟哝一些异种的语言。于是大家就开始窃窃私语。树的窃语像温柔散开的风,但大家的窃语带有尖锐的形状。
我确实在闽南度过了我的童年,但我父母为了让我说出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并不让我学习闽南语。虽然最后我的普通话也没有说得很好,仍然带着一股地瓜腔,但排挤和差别对待总是如影随形。就连我打个摩的都会被多加价或者兜圈,仅仅只是因为我讲普通话而已,就会被认为是不懂的外地人。我去上学,一定会有同学追着我叫我“阿骚阿”——我回家问我爸那是什么意思,反而被我爸打了一顿,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脏话,是对外地人的蔑称。正是推广普通话的期间,老师不让我学闽南语,学校里也禁止讲闽南语,表面上我被树立为一种典型范本,背地里我却遭到众人唾弃和鄙夷。
不会说闽南话,但普通话一股地瓜味,这像一种对我的隐喻。我不被承认为“本地人”,但我染上了很浓的闽南的颜色。我最熟稔的柔软记忆都来自于闽南的风和土,暑热,台风,三角梅。海的味道吹遍小城;土是红土与黄沙;春末夏初的时节天气太潮湿,会让墙和地都结满水,走磁砖地一定要小心;公共建筑的地板是温润的水磨石,民厝的地板则是花砖;老建筑的楼梯间里有镂空的花砖,白色的颜色被经年累月的台风侵蚀,留下黑黑的印痕;四处都有肆意生长的三角梅,花朵和枝叶都像爆炸一样,艳俗的颜色;拜拜的时候红色供桌放在敞亮的厅堂,女眷们在昏暗的厨房忙碌,男人们在门口纳凉抽烟,小孩满地乱跑,等着吃刚出锅的炸鸡。
我一直以为我讨厌闽南。我不喜欢闽南话,总有人嬉笑着问我听不听得懂,考我,我说我听得懂,只是不会讲——无论我怎么说怎么反应怎么回答,话题的最终都会导向同一个结论:那你是外地人嘛!我不喜欢拜拜,佛香焚太多,烟熏火燎地让我头疼脑昏,炸鸡又腥又烫,我还得装出一副津津有味的样子。我不喜欢祖厝,厅堂里祖先的遗像挂了一圈,每个老头看上去都又严肃又吓人,而且奶奶总是把零用钱都给我弟弟,温柔地让他去小卖部的路上小心点,我只能干等着我弟弟回来,看看趾高气扬的他有没可能分我一点点。
我学会了看书。书里有更广阔的世界,书不会将我推开,书不会说我是“外地人”。书告诉我“远方”会是什么样子的。“远方”是西伯利亚的冻土和冰原,是伦敦阴郁落雨的天空,是爱琴海岸的蓝和白,是雨林和橡胶树。
两厢对比,让我更恨闽南。它尽全力在排斥着我——女性的、外地的我,仿佛不够好,仿佛永远需要学习怎么成为一个“本地人”。谁想成为这样的本地人?我反正不想。恨在一点一滴里累积,逐渐攒出一个具体的形状:我要离开闽南,离开福建,我要去远方。
幼年的我着魔地读书。许愿,勾勒一个我的容身之地。
成年后的我已经在日本住了很久。我清楚地知道我的容身之地可能在哪都没有。我是一只无脚鸟。
这让我好孤独。
当年,我带着恶狠狠的扬眉吐气一样的心情离开了福建,心想,这鬼地方我再也不会回来。你不接纳我,没关系,我有脚,我可以走,我不在乎你。
谁知道新城市并不能抚平我的落寞。闽南像一种风湿病,每当天气潮湿,就隐隐作痛。
季节流转,我在东京看了五次樱花。最后一次看樱花的时候,我跟在日反战俄罗斯人一起,喝了太多伏特加,靠在树干上,视线昏然地扫过众人,看着天空。他们在聊他们没有容身之处的事情。俄罗斯是回不去的故国,因为反战的立场所以跟很多家人朋友都断了联系,但乌克兰人仍然鄙视他们,他们被夹在中间,无处可去,流亡。
流亡。
这个词分外清晰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
我或许也在流亡。我回不去闽南,或者说,我想回去的闽南,在这个地球上从来没有存在过。
但我好想念榕树。东京在温带,气候太冷了,榕树会死掉,它是属于亚热带的植物。自从我离开,我便一次都没有回过头,也没再见到过榕树。日本人有日本人的樱花树,我有我的榕树——虽然羞于承认,但我和闽南,确实血脉相连。我是闽南的水土养出的女儿。
东京有杭帮菜、粤菜、川菜、东北菜、湘菜、西北菜,但唯独不见闽菜。台湾菜并非闽菜,去过几家沙县小吃,味道也都不对。
我见不到榕树,也吃不到闽菜。
我真的,想念榕树了。我是闽南人啊。
我给我的伴侣做过很多很多川菜和杭帮菜。因为我吃不惯日式料理,受不了他们爱往料理里放砂糖的习惯,所以我坚决不让他掌勺,只准他在厨房给我打下手。
来日本五年后。我终于第一次给他做了闽菜。我做了一大锅姜母鸭。
从业务超市淘到整只鸭,粗粗切一下。细细地切出大量姜片,需要切掉好几块姜。一小半拿去爆炒爆香为熟姜,味甜,另一大半则可以直接用,是为生姜,味辛。加入调味料和香辛料,用一两瓶绍兴酒文火盖锅盖慢慢煨。等待期间,将泡好的香菇、干贝、虾仁从水里捞出,胡萝卜切丁过水。下锅,爆香葱头和剩的一点点姜,把香菇干贝虾仁胡萝卜全部下锅炒熟。米放进电饭锅,蒸米水要加一点点生抽,味精,和油,然后再把炒好的配料放上去,开始蒸饭。出锅后把留的一点葱头油在饭里拌开。最后潦草地切点白萝卜,下锅煮清汤,出锅时撒进葱花。
姜母鸭、咸饭、白萝卜汤。我的伴侣吃得把头都埋进了碗里,跟抢食的小猫一样。太好了,这样他就看不到我模糊的眼睛,还有复杂的表情。
熟悉的闽南。厌恶又怀念,魂牵梦萦,难以忘怀,养育我成人的闽南。闽南简直是我的一个,会家暴的父亲。我的血,我的泪,我的吻,我的童年和青春,我的肉身,都给了闽南。
我想我有我的骄傲。我会坚持着,不会再回闽南。我或许会在东京继续做各种各样的闽菜——毕竟料理是无罪的——虽然都是跟着网上的菜谱学的,毕竟我妈也不是闽南人,而且她做饭太难吃了,我跟着她只能学会洗澡泡菜。
这就是我。在异乡跟着网上菜谱做闽菜的,被驱逐的,非典型性闽南女儿。我是刺桐花,我是爆裂又凝固的伤口。
所以,我的胃,是哪里的胃,我的人,又是哪里的人呢?
谢谢你们来看一只阴沟老鼠的散装遗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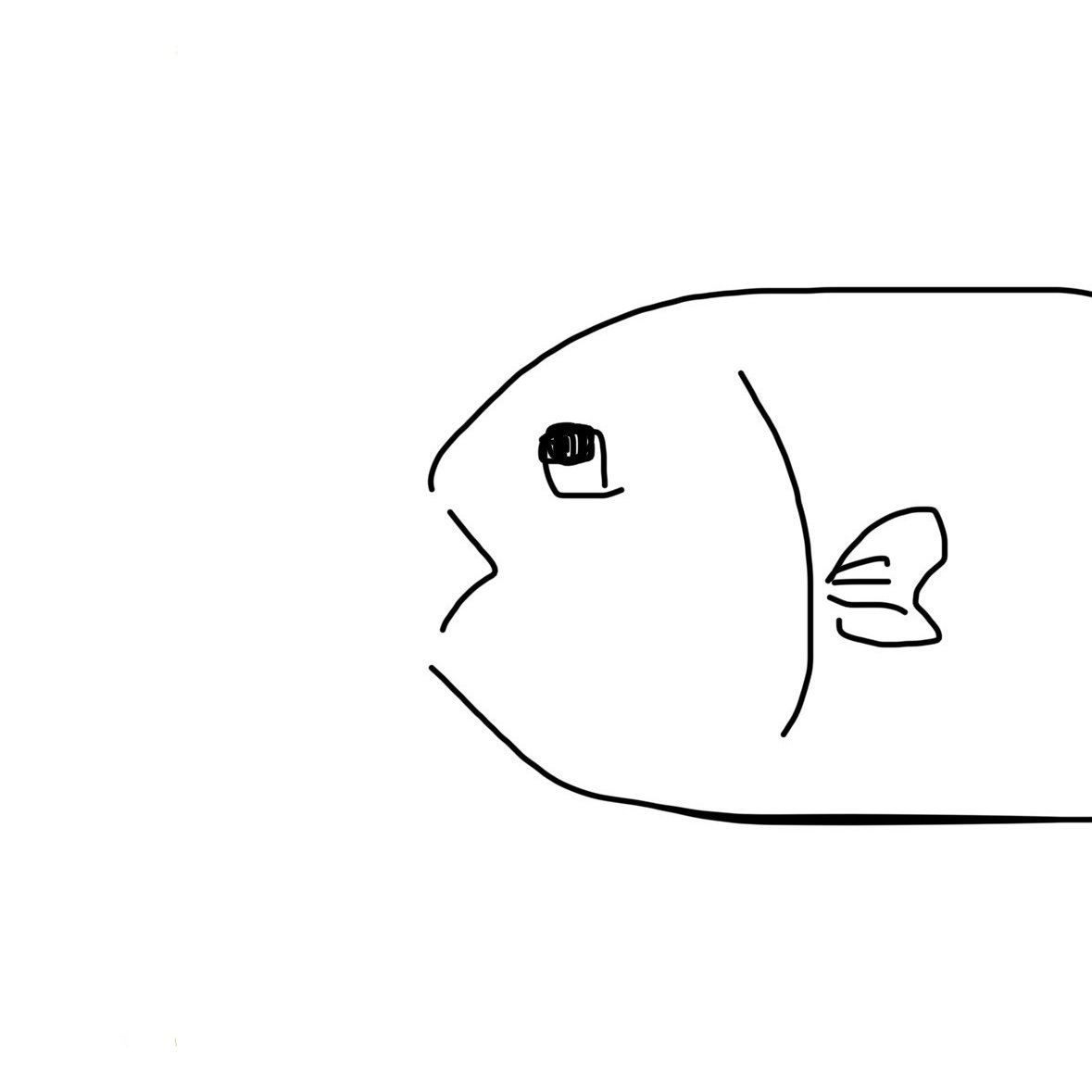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