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要的恶与非必要的恶
最近对两篇文章感触很深,一篇是姬老师的故事的消失 就是唯一的故事,另一篇是我的朋友王抱一在港岛的亲身见闻采写:一些不同的声音。
开头我想先引用姬老师提到的故事《那些离开奥梅拉斯的人》: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叫奥梅拉斯的世外桃源,这里受到神的庇护,每个人都过得很幸福。但幸福是有代价的,神规定,城市里必须选出一个人来承担所有的不幸,一旦让这个人感到幸福,整个城市就会灰飞烟灭。于是,奥梅拉斯的地下室里关着一个小男孩,他只能吃最粗糙的东西维持生存,每天接受无尽的折磨,不能让他感受到一点点幸福。
城镇里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小男孩的存在,他们的成年礼就是去地下室看一眼这个小男孩。于是,奥梅拉斯会出现四种人。
第一种人,他会为小男孩的悲惨遭遇而难过愧疚,这种内疚可能持续很短的时间,也可能伴随他的一生,但总之,他会怀着内疚和感激住在这里,继续享受美好幸福的生活。
第二种人,他看到小男孩的悲惨遭遇后,沉默不语,在夜晚打包行李提着灯笼离开了奥梅拉斯,如同他从未来过,他拒绝享受建立在他人极端痛苦上的幸福。
第三种人,他是神,制定了规则,或者建造了地下室,每天折磨小男,他尽管在做非常残酷的事,但正是因为他,才保证了奥梅拉斯大部分人的幸福,人们称他为“奥梅拉斯必要的恶”。
第四种人,他会闯进地下室,把那个小男孩救出来!哪怕这样毁掉了大多数人的幸福,但第四种人坚信,幸福应该靠奥梅拉斯人民勤劳的双手去创造,建立在一个无辜小男孩悲惨遭遇上的幸福并不是神的庇护,而是神的诅咒。人们沉迷于这种毒品般的幸福,永远停留在美好而原始的世外桃源,不谋求改变,奥梅拉斯因此停滞不前。所以,哪怕毁掉成千上万人的幸福,也必须把小男孩救出来。
在这里我不想讨论这个模型的合理性——是否一定要有人牺牲,是否存在乌托邦政体。或者说,我选择对一切被过度赋魅的乌托邦存疑,无论是自由民主还是共产主义。
现代政治哲学中有无数人讨论过这个牺牲者的角色,而推演出的结论大多证明,这种施加于小男孩的规则之恶是必要的。
反之,如果在一个规则之中找不到这个牺牲者的角色,那么大概率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成为了牺牲者。
If today there is no longer anyone clear figure of the sacred man, it perhaps because we are all virtually homines sacri.
——Giorgio Agamben
关于成为哪类人,我们的选择常常会基于两个维度,一个是审美取向,一个是生活现状。并不是每个想当神的人都能成为神,同理也不是每一个安于奥梅拉斯的幸福的人都能保证自己一生不会被恻隐与内疚击溃。
这里我们暂不讨论第一种和第二种——我衷心地希望他们可以在规则当中或规则之外各凭本事、各得其所。
那么我们先来说说第四种。
我不知道选择做第四种人的朋友中,有多少真的洞悉了这一套规则的运作模式。我觉得他们——毋论是否是我的一种刻板印象——是最富有理想却也最天真的一群人,怀着单纯的善恶观,拒绝一切为利维坦开脱的尝试,抵制与恶龙的共情。
他们的道德约束自己也约束别人,他们是最有资格生活在乌托邦世界里的人。
我愿意相信,在大多数时候他们是有殉道的心理准备的。他们很可能也同样愿意为小男孩承担那些必要的恶,替人受难,割肉饲虎,成为时代的救世主。
然而这样的殉道往往是构建于一厢情愿之上的。他们之所以是他们,恰恰因为他们不是小男孩。
理想主义者的另一个特质是求真。真实、真理、真相,在媒体铺天盖地的谎言中试图洞悉一点握得住的事实。
可是这个时代,求真越来越难了。
这里我们不提鲍德里亚,也不提居伊·德波。我想讨论一个从2016年开始流行的概念:Post-truth,后真相。
尼采认为,人类创造了一些概念,通过这些概念来界定善和正义,从而用价值的概念取代了真理的概念,并将现实建立在人类对权力的意志之上。这是后真相的理论基础。
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和英国退出欧盟公投前后,基于民主政体内部对媒体和舆论的阴谋与操控,“后真相政治”这个词被欧美国家公民频繁引用。
直到今天,普世的判定真理的标准已经消失,共同的基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随之消弭。仅仅靠付诸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成本已不能帮我们在求真之路上迈进一步。
那么理想主义者们的选择,又应当基于什么来做出判断呢?
或许可以选择成为神。
神不是一个个体,而是权力意志的集合。成为神,可以完成由局中人至上帝视角的转换,参与制定规则。
但最重要的是,神可以选择在每一个按钮按下之前思考,这是否真的是必要的恶。
我们向往文明,于是我们建立规则。需要警惕的是,现代性所可能招致的悲剧恰恰是一种被高度文明化的野蛮,一场被合理化的屠杀。
毋庸置疑,规则象征着理性,而理性恰是现代主义的至高要求。在一个国家机器当中,如果每一个环节都以理性作为最高目标,以寻求最优解作为行事方针,那么在一级级传达的执行过程中,罔置道德几乎是一种必然,而在执行的末端导向屠杀的暴力也就不足为奇。
这也是齐格蒙·鲍曼在讨论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时阐释的观点。在“排斥异类”这一规则的执行中,因为:1.现代化的程序体系,2.公众的漠不关心,甚至3.犹太人自身对于这一管理方式的服从,导致了非必要的恶的最终发生。
当然,从今天的视角看,我们也难以断定“排斥异类”是否真的是一种必要的恶,但这件事确实可以给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带来一些启示。
在新近关于港岛现状的文章里,王提到执法者砍杀参与者,甚至持枪威胁普通市民。我很难认同这样的恶是必要的,而这种非必要的恶也恰恰发生在规则执行的末端。
异见者通常喜欢把主权与执法者视为一体,作为邪恶的符号和批判的假想敌。事实上,规则的制定和规则的执行也存在鸿沟,而这恰恰是需要被鉴别、被个体的良知填补的地方。
这样的良知不等同于道德。”良知“是很难被机器习得的,能被机器习得的恰恰是那些以价值为导向、用于界定善和正义的道德说辞,和那些大多数的流于表面的”政治正确“者所捍卫的东西。
近来我们总是在探讨人的异化——我们期待投身时代,却又忧心作为”人“的特性的泯灭。如果主体还需要尊严,那大概就还不能放下良知、放下对人类的悲悯和永恒的爱。
这大概也是有机主体为自身存在的最终辩护,是我们可以用以抵御虚无并负重前行的最后武器。
虽然这个时代很糟糕,但还是要走下去,不是吗?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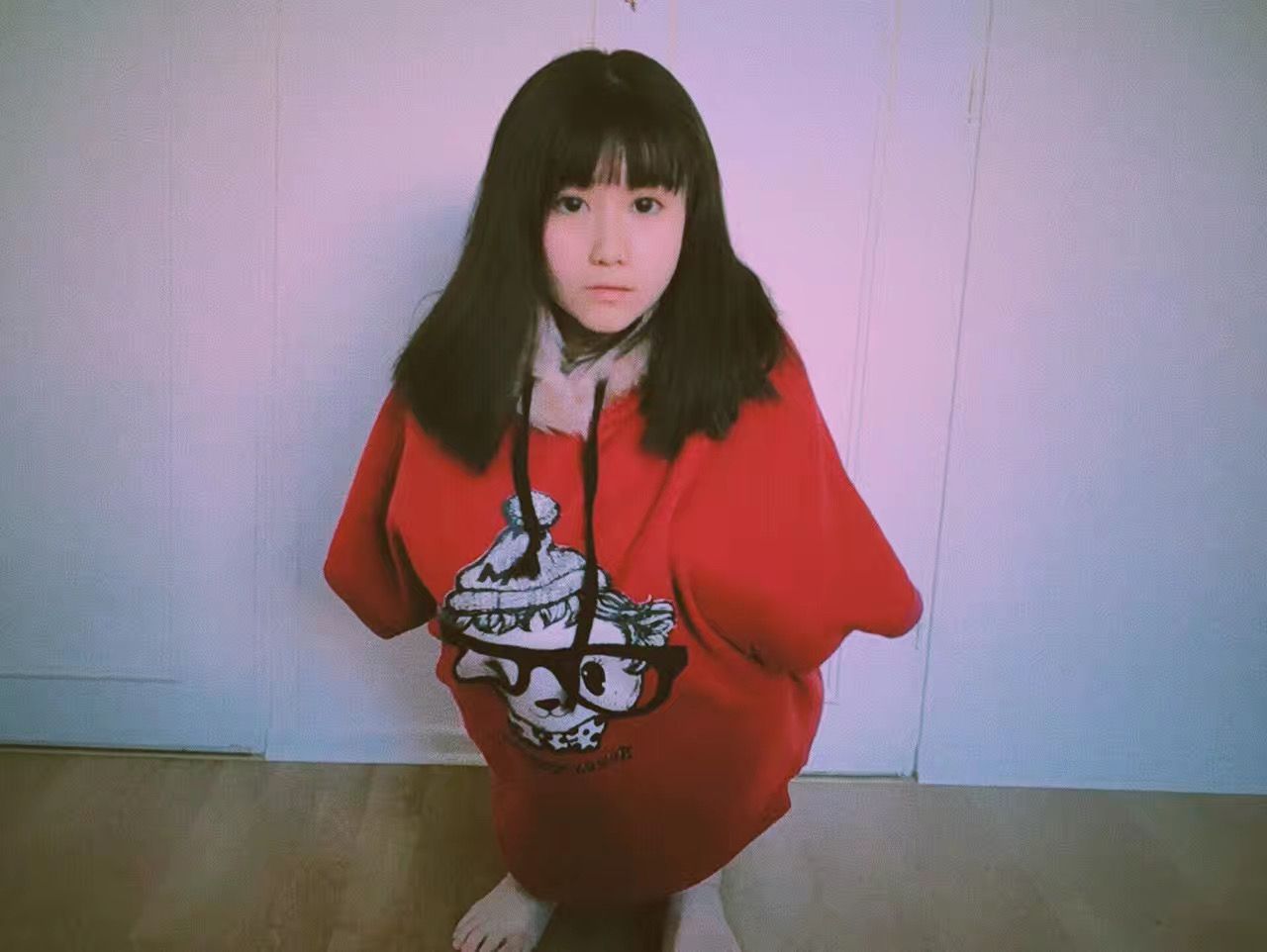
- 来自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