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形・給敬而遠詩的人】詩人有多驕傲,就有多謙卑——訪黃燦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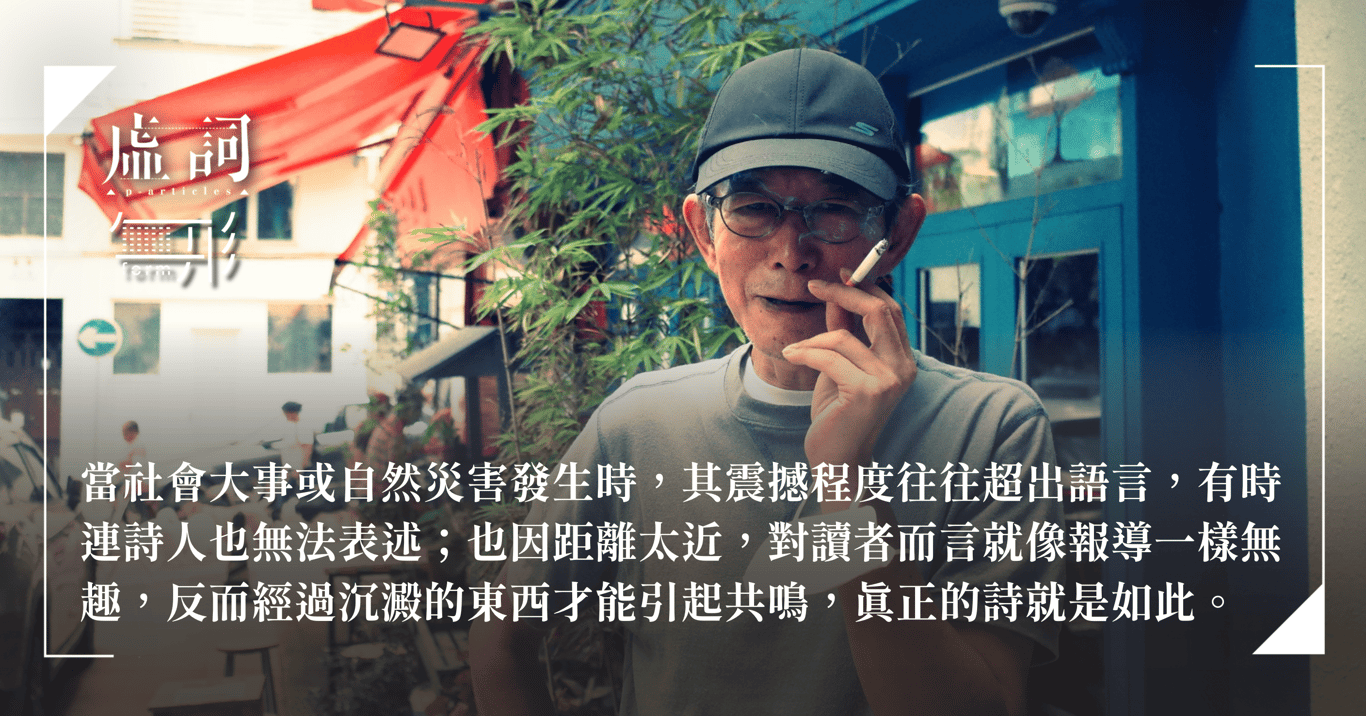
文|陳芷盈
許鞍華的《詩》,黃燦然看了兩次。
黃燦然說,曾有人為他拍攝紀錄片,錄影帶寄來後,他從未打開。後來他受邀出席映後談,卻缺席了放映會,只因「詩人最怕看到自己在銀幕出現,好恐怖。」這次他拍許鞍華的《詩》,初看同樣驚嚇,後來放飛自我豁出去,首映那天他在觀眾席,突然覺得可抽離地觀看這套為詩而拍的紀錄片。問及接拍原因,他輕描淡寫地說:「沒甚麼,拍就拍。許鞍華是有點不同,她是一個藝術家。」
黃燦然沒有為拍攝做任何準備,他自言做甚麼也好,最重要是自然。在《詩》裡,他經濟流亡移居深圳,生活樸素,幾乎深居簡出,一條褲修修補補又穿上,書卻堆滿房屋每一角。這天一大早,他穿著同一條褲,從深圳坐火車來港,完成大半天訪問,留下幾根煙頭,又匆匆回去。黃燦然把所有心力和時間留給詩,因為詩,使他既謙卑又驕傲。
詩從來不在一時一刻
《詩》裡黃燦然說,「我知道我是詩人時已不在世上,這是真正的現實。」許鞍華於是說,「你在追逐永不能追逐的東西。」
但又有甚麼辦法呢?詩人的追求是超世的,所以黃燦然活在地上,比一個凡人更平凡,卻以文字創造詩的國度。黃燦然說,詩人謙卑,因為詩人是最下層的「窮人」。「無論擁有甚麼身份,你寫詩也無人理睬。而且,詩人的精神再高,也只是一個凡身,他必須要從底層感受人生,沒有這個基礎,詩就失去立足點。一個清醒的詩人,更會知道自己甚麼也不是,因為歷代偉大的詩人太多了。」然而詩人也驕傲,因為詩人同時是最頂級的「富人」。「很多人到人生頂峰才意識到的東西,詩人早就知道、感覺到了。當周圍的人看不起詩人時,詩人卻把他們看得透徹,並早早站在他們拼搏半生後才去追求的方向,回過頭望向他們。詩人就是知道得太多,所以才同時有些謙卑又有些驕傲。」
詩人判斷自己的詩作時亦如是,黃燦然笑道對自己的作品「又肯定又否定又肯定又否定」。他解釋,人在不同時期的精神向度與爆發力都不一樣,「我80年代的詩較簡單樸實,到90年代我對語言的密度、激烈度、張力等要求都比較高,也較實驗性。00年後,人到中年,我又回歸樸實,寫得客觀一點,不再集中於個人。」因此,評價詩作的好壞是非常複雜又拉扯的過程。黃燦然近日整理舊作編選詩集,便抽走了一些作品,又新增了一些。「最近我發現不少未被輯錄成集的詩,原來寫得很好,但當時我自覺寫得差,甚至沒有拿出來發表,反而一些已被發表或被視為代表作的詩,如今一看就覺得:哇!咁乞人憎!真係面目可憎。所以我經常跟年輕人說,千萬不要丟掉你的詩,刪改過後,都要將底本留下,因為我們對一首詩的評價不過是一時一地的想法,或是受到當時的觀念或美學追求影響。」
故黃燦然鼓勵詩人肯定自己的作品。「別人說你的詩壞,你可以不理,但別人說你的詩好,你就不可以不理。舉例說,你把作品給朋友看,但大家讀詩品味不一,你又怎能相信他的意見?相反,有時候我看不出自己作品的好,朋友卻讚不絕口,我的詩作〈杜甫〉與〈中國詩人〉就是例子。」說到這裡,黃燦然流露出一臉可惜的表情,「很多年輕人,明明早期寫得一手好詩,但因為虛榮追求他人讚賞,結果適得其反,失去了自己最原創的東西。原創性對詩而言很重要,那種真摯有時候好到超越評價,若用技巧分析是很幼稚的。」
以詩神之名發聲的凡人
黃燦然再三強調詩人的「凡人性」,「詩應包含人的七情六慾、好壞正邪,隨著詩人心情或狀態變化,自然對世界有不同反應,可能上一首詩是讚美,下一首卻在譴責世界。詩人並不代表某一種風向,不應用某種道德或美學觀點過濾或審查自己。」話至此,黃燦然又講得神秘,「詩人只是代詩神發聲而已,你怎麼可以過濾祂呢?你有甚麼理由?難道你自殘嗎?」故黃燦然認為,詩人的感受越多,甚至自身的衝突越多就越好。
詩的誕生往往不由自主。黃燦然說,「我也不知道下一首詩在哪裡,但到臨時就很厲害,你會放下一切,不能自控地寫,覺得自己是超人一樣,何止驕傲,簡直是通神。但當詩神離開了,你又變成一個廢物,多衝擊的東西也無法描述出來,連謙卑的機會都沒有。」說畢他哈哈大笑,大呼「好慘」。如〈致大海〉一詩,黃燦然足足寫了五年,當時正值他人生最忙碌、壓力最大的時期,一個意象醞釀了,往往要很久才能成詩,但他又笑言「這種狀態也很好,有時來得太快,神授的禮物太多,又不會去珍惜。」
《奇蹟集》是黃燦然第一本通神寫的詩集。那時他抑鬱症初癒,從纏繞多年的陰影走出來,但感幸運至極,「所有詩觀、人生觀都拋到一旁,寫出來的都不屬於自己的頭腦,就像手被誰控制著寫成。」第二次通神則跨越兩年,黃燦然自言從未試過,「首先是19年6月寫到8、9月,寫了百多首,然後一直等,到2020年11月又寫到2、3月,然後許鞍華就來拍攝。」在這種無所不能的狀態下,黃燦然隨便想到幾個字就能成詩,他坦言或許跟整個社會環境及時代氣氛有關,是累積成形的憤怒。黃燦然在香港時從事新聞翻譯工作,他自言「作為新聞工作者,對政治經濟、國際形勢一直很關心,但以往這些東西從不入詩,唯獨這次沒來由地把它們納入詩裡。」或者這就是黃燦然計劃在香港出版完整的《詩合集Ⅰ》及《詩合集 II 》的原因。

還未發揮價值的香港詩
但黃燦然也清楚知道,詩人與時代是錯開的。「當社會大事或自然災害發生時,其震撼程度往往超出語言,有時連詩人也無法表述;也因距離太近,對讀者而言就像報導一樣無趣,反而經過沉澱的東西才能引起共鳴,真正的詩就是如此。」他接二連三舉了幾個例子,如扎加耶夫斯基(Adam Zagajewski)多年前寫下〈嘗試讚美這殘缺的世界〉,本來寂寂無聞,直到911事件發生,詩作在《紐約客》上發表後隨即引起轟動;又說奧登(W.H. Auden)的〈1939年9月1日〉寫於二戰發生期間,如今正是時候再讀。「詩真正產生社會或政治作用時,詩人已不知到哪裡去了。像布萊希特幾十年前寫的詩作,現在很多人都說呼應當下,然而當年根本沒有人讀布萊希特的詩,因為他大部分詩作都沒有發表。」在《詩》裡,廖偉棠引用的布萊希特,正出自於黃燦然的翻譯。
黃燦然又緊接著說下去,期間一直沒有點起香煙。他說,「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的洪業,少年時代不懂欣賞杜甫,直到日本侵華後才明白杜甫的偉大;《一滴淚》的翻譯家巫寧坤,也是在歷經文革後才看懂杜甫。事實上,當時他根本讀不到可以表達內心的作品,那個年代的作家詩人連表達的機會都沒有。所以說,詩的作用真是很奇怪,可能你現在寫的只是細微、不經意的事,但幾十年後它卻會發生社會意義,包括香港詩人的詩,到現在還沒有真正發揮它的價值,它要慢慢經過時間淘汰,還有一些詩人被經典化,才會成為一種文化精神,讓人慢慢注目,隔了幾代人後,才演變成精神遺產。」一口氣說到這裡,黃燦然才稍微放慢語速,「不過詩人可能也不太明白這些,他也不會考慮自己在做甚麼,只知道要寫,然後到了某個時候,下一代又會繼續寫下去。」
詩是唯一的精神歸屬
在《詩》裡,兩位詩人黃燦然與廖偉棠都已搬離香港。本土詩人在他方,或非詩人本願,黃燦然卻笑言只掛念香港一間茶餐廳的咖啡,不無諷刺。「移居深圳是很現實的考量,一是解除經濟壓力,讓我有大量時間去做翻譯;二是我本來就在鄉村山水間長大,這種回歸對我而言很重要;三是我一直在大陸成長受教育,但我已幾十年沒有真正在這地生活,我很想知道它究竟是甚麼,所以我才搬到一個小小的地方,那麼很細微的變化,我也能感受到。」
當問到黃燦然可有甚麼歸屬,他先說,離開了故鄉就再沒有家。想了想又再說,「我也不知道,有人說漢語是我的家,我只知道我大部分的詩都在香港寫,四本詩集在香港,兩本在深圳的一條小村、一個小島。我的生活是流放的,但無論如何,我確實是曾在一些地方,前所未有地寫了當地人都不會寫的東西。我不認為詩人需要執著於一個身分,但一些地方性的東西是應該珍惜的。寫本土的東西可能沒有那麼顯眼,但如果它有這個價值,詩人就要讓它顯現,這就是詩人應該做的事。」他稍頓,又笑了笑說,「如果真有甚麼歸屬感,那我的精神歸屬都是詩,沒有其他了。聽起來可能很飄渺、很可憐,但又覺得很榮幸,就跟剛才說的驕傲與謙虛差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