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的“小女人散文”与女性主义
我是偶然间看到“小女人散文”这个说法的,起初觉得很不可思议,以为是说着玩的。但好奇心起了头,无论如何也要来读一读这小女人散文了。
于是找了其中的代表作,素素写的《就做一个红粉知己》。看这个书名让人不禁莞尔,觉得和作者的名字很相配,而且听起来“小女人散文”好像就应该取这样一个书名。带着几分暧昧不明的揣测与先入为主,我盲目地扎进了这本出版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书。
序言唠唠叨叨,一直在闲话家常,好像说“谁谁谁的丈夫”、“妇唱夫随”都超过了作者和这本书本身。这写序的人实在是让人心烦,临了才稍微提一句,他认为作者的文章是“咖啡文章”——“一种明显不同的精致美文,讲究理趣和情调,读来如饮咖啡”。
到这里,我不由得心一咯噔,不知道后面还有什么在等着我。但好奇心始终占上风,索性快速翻过了这篇滥情得不忍卒读的序言,直奔主题。
我看到她头一句是这样写下去的,“没理由地怕一切陌生人。”像是我平时的日记起头,第一篇文章竟然就在这样的语气里开始了。她说起朋友,又谈自己对“天真”和“老成”的看法,有点好笑,但并不讨厌。于是我耐下心来接着往下读,她“突然”提起1992年的圣诞节,却一下子打动了我。
“1992年的圣诞就在老而弥新的房子里过。柔柔的,暖暖的,轻轻的,厚厚的,汨汨的,不招摇,但是有信心。而1992年的日子,1993年的生活,又何尝不是在这一种情绪里过?连这两年的文风,也都自然而然地放弃了声嘶力竭咄咄逼人,代之以又细又厚的情思,就像时装界一枝独秀脱颖而出的砂洗真丝:在好似蒙尘的柔软细致里,在相同的真丝‘名、实’之下,有着一种深厚与优渥。”
这便算是真正地切题了,她所使用的形容是从未有过又有点似曾相识的:砂洗真丝时代。而这便成了我进到她的世界里去的一个入口,也是我所想象的九十年代,与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模样。
我也终于回过神来,意识到她并不是“突然”提及1992年的圣诞节,而是她真正生活在那里。透过这段文字,向我传来了当时较为深刻或普通的、不那么重要的一段投影,却让我几乎落泪。她怎么会是这样的好,我已经彻底忘了,先前在不知所云的序言部分所遭遇的尴尬。
这是一本很小的集子,里面每篇文章的篇幅都很小,她说到吃家常菜、买衣服、荡马路的事,偶尔与朋友重逢,或者也谈谈张爱玲、三毛、宫泽理惠和戴安娜,聊聊电影之类的。好笑她说起自己写的东西,形容是“三五百字的豆腐干”。这样想来,确实是“小”的,也是“女人”的。我倒很喜欢。
由此,“小女人散文”这个说法在我心中清明了几分,最后是一点暧昧也不剩了,变成了最好的一个词,让我想到便觉得:我也要写这样的文章,我也应当和她一起。
这书看完便撒手了,但过了许久,其中有几篇又让我忍不住反复想起,比如她谈女性化妆、思考事业和感情,包括那篇让我震撼甚至是感到震惊的《PLAYBOY》,力量太强了,感觉超过了先前只是让我感觉“亲切”、“喜欢”的“小女人散文”的定义。
她认为那些对于女性化妆的批评是无稽之谈,到底“谁配教谁”,“也许是我们大多数人,过于谦逊、过于忍让了?”虽然文章中从未点明“我们”究竟是谁,但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她就是在说女人,她和她们一起。
有一篇她还提到,说是曾回过一个十多岁女中学生的读者来信,后来这个写信的女孩子给她打电话,说有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要带自己走,“我想不辞而别,我讨厌我母亲,就是想避开她。”
她感到心惊胆颤,但也只是从女孩的家庭关系和个人成长的角度开始劝服:“如果你只是想避开你的母亲,在上海同样办得到,对吗?你不想考大学也可以,十八岁中学毕业就做事也可以,但是,你不要把希望寄托在朋友身上。出外闯世界,我看你还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我时常会想,这样一个故事发生在今天会怎样——是的,一个十多岁的女孩子跟着三十多岁的男人远走高飞的故事,今天也还会发生,纵使那一套说辞变了,我们今天高谈女权,这样的事也还是会不停地发生。
但我们来看一看,生活在九十年代的素素是怎样看待这件事的。她竟然一句也没有提“男人会骗人”,只抓住了一个问题,这个女孩因何要走,有没有别的法子可以帮到她。
那是1993年。为什么会这样地不同?想起后来我搜“小女人散文”一词,在1998 年 05 期的文艺评论上看到一篇《“小女人散文”价值论》,作者叙述“90年代女性与男性共同拥有一片天空(都市白领丽人阶层的出现,表明女性在实现人的价值的同时,亦关注起女人价值的实际)”。
那是怎样的年代啊,人们过圣诞节,欣赏麦当娜,和全世界一起平分一代年轻人的狂喜、迷惘和叛逆。
如今我们再来看,生活在那个年代的素素是怎样看麦当娜的,也就是我最喜欢的一篇,《PLAYBOY》。她从麦当娜佩“PLAYBOY”这件事开始讲起:
“麦当娜从1984年红到如今,名闻遐迩。麦当娜的‘名声’来自她本人不断出新的歌曲艺术魅力,来自她自我标榜的‘性革命’,也来自舆论、权威、正统阶层对她不厌其烦的抨击。……从没有一个女明星,因为性感、因为性而受到公众如此强烈持久的抨击。”
她认为麦当娜是极具才华和勇气的,而且关注到女权运动的支持者、女性主义的倡议者,同样也在大力抨击麦当娜,她们认为麦当娜的色情形象、女性受虐镜头,其实是将女性重新贬为一个性的象征和工具,从而将女权运动至少拉回了二十年。
多么讽刺,与此类似的事情今天也在重演,并且变本加厉,我们的社交媒体用语甚至退步到异口同声批评其“媚男”的地步。对,我们会使用“媚男”这样的词,相比起八九十年代批评麦当娜“将女性重新贬为一个性的象征和工具”,恐怕也至少拉回了二十年。
但素素是这样认为的,“麦当娜不是将女权运动拉后了二十年,而是对整个女权运动的一个总结和反动。麦当娜反叛的勇气和能力是令人堪惊的,然而对女权运动而言,她不是一个高峰,而是一条歧路。”
在文中,她回溯了美国前二十年来的女权运动,非常凌厉地指出:
“遗憾的是,我们竟然沾沾自喜。我们竟然乐于接受‘国际妇女年’如同接受‘国际气候年’,比如第65届奥斯卡电影评选,因以‘女性为主题’而获广泛的称赞,据说是可以以此表彰妇女对电影事业的贡献。女性问题如此不断地引起重视,说明女性依然只是男性社会中众多问题之一,而不能与男性共同面对社会问题。”
这已经很辛辣了对吧,但她又接着补充道:
“更遗憾的是,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兴起的激进女权主义运动,经过岁月的磨蚀,到八十年代到今天,已被偷梁换柱。‘女性主义’一词不再是强调女性优越于男性,也不是理智的男女平等,而是强调女性应安于本分的温柔平和,安于生儿育女,安于辅助男性。”
她一贯嘲讽的语气:这该是又一个世界潮流了?
最终文章又回到麦当娜佩“PLAYBOY”这件事上,素素认为,这并不代表麦当娜是花花公子的玩物:
“相反,她在身体力行地玩弄(PLAY)男人(BOY),她的放荡是她精心挑选的武器,她的性感,也不仅仅是为了取悦男性、左右男性。麦当娜同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女性一样,深知无力反抗男性社会,于是,只好“异化”,只好吸取男性社会的种种恶来施之于男性社会,来反叛男性社会几千年来缔造的种种规矩、种种神圣、种种道德。”
但即便是这样,她的眼中也没有燃起兴奋的火焰,她是失落的,甚至于绝望:麦当娜孤军作战于歧路,麦当娜终会销声匿迹。而女性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今天该踏住哪一个节拍?
我不禁想到在她之后的另一位女作家,在十二年后的三月八日,马雁以十足嘲讽的语气写下,《节日快乐,社会主义的女儿们》,表达了对女性处境的担忧和不满:
“由于1949年开始的自上而下的平等立法,中国女性被无偿赐予了受教育与工作的权利,女性的经济自立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可贵的效益——广大的中国男性们也从细节上(比如说家务)身体力行着两性平等的基本国策,即使,不那么情愿地(从某种意义上说,受教育和工作的权利并非无偿,那只是预付给中国女性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笔代价)。基本国策中‘两性平等’的书写虽然完毕,但社会主义的女儿们,作为乌托邦孕育的后代,她们的故事并未完结。”
后来时隔整整两个月,她好像还是为此不平,又写下一篇《一个女性主义者的寡妇年方案》。
但这里有一个可怕的发现。在素素所处的九十年代,她眼中的女权主义,是国际的女权主义,这也十分贴切,我先前已经说过,那确实是与全世界一起平分狂喜、迷惘与叛逆的时代。但到了马雁所生活的2005年,似乎越来越闭塞,她所书写的已经完完全全是当时中国的情况,即便没有什么别的证据表明,我们也可以从她的标题一窥究竟,她使用的是“社会主义的女儿们”,已经没有麦当娜和她的追随者了。
而如今又过去了七年,那个年代更是消亡得够彻底。按照素素的说法,在愈发狭窄的今天,女性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又该踏住哪一个节拍?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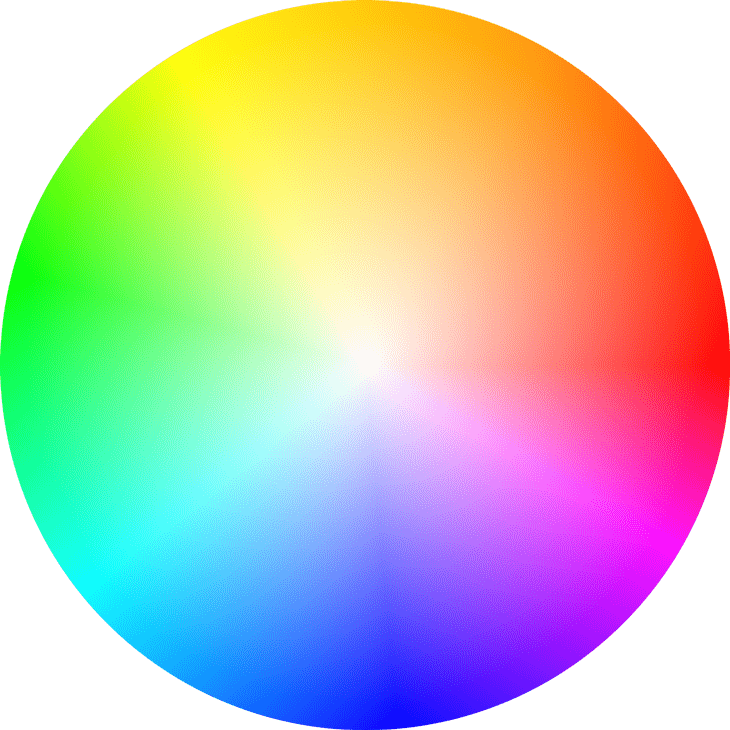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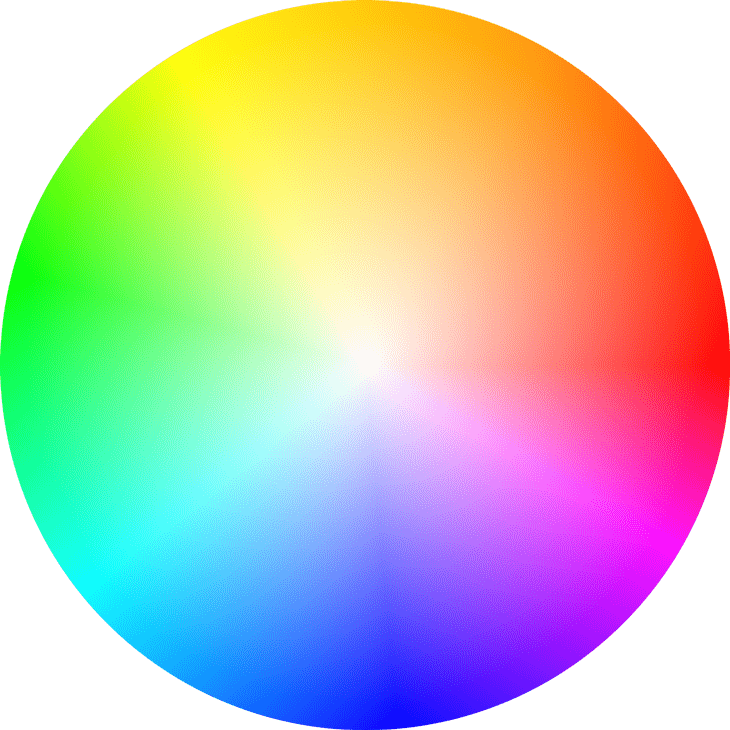




- 选集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