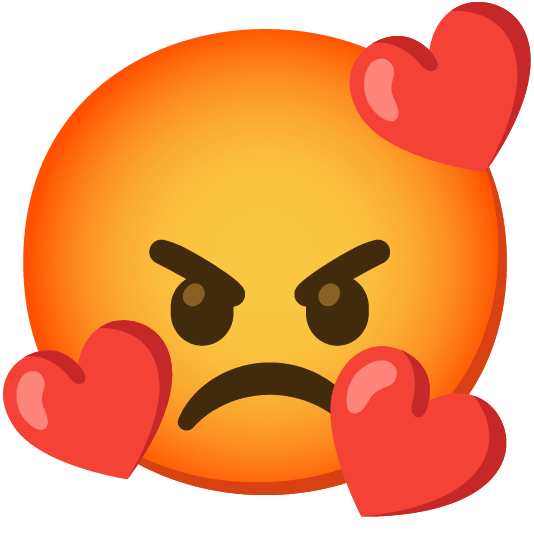我和佟佳言
我和佟佳言
我从很小就迷恋人和人之间奇妙的联结。
不是什么山盟海誓、要生要死,那种很深刻的;也不是上天注定,数世轮回,伫立凝视的那种很确切很长性的。甚至与这些相反,我喜欢的是随机和一闪而逝、去不留痕的那种。把这些话说出来,我才意识到,为什么自己的长期关系总是坠入一种无趣的胶着,直到弃之而后快。
我要讲讲我和佟佳言的故事,以此说出这联结的美妙。
初中的某一天,当我过完周末回到教室,看到课桌右上角贴的名字——名字的主人有想撕掉,无奈粘得太牢,只扯掉纸条的边沿,“佟佳言”三个字都还在。我看着它立马陷入对这名字的无穷遐想中。
我想这个用我们教室做考场,名叫佟佳言的师兄或是师姐坐在我的位子上,看到我的视角下看到的讲台和黑板,我看到的桌椅墙壁以及窗外半棵梧桐树。想着ta考试时的紧张或放松,意气风发或抖如筛糠。
我还会想佟佳言会有一个怎样的家,怎样的父母。在采光猥琐的客厅餐桌上,塑料罩子下,会不会正好有一碗冷粥和一盘炒得烂糊的蒜蓉长豆。
然后我回了回神,把自己也带了进去。我又想,佟佳言会不会想到这个课桌的主人,想板凳和桌面曾经有我坐着的屁股和趴着的胳臂,会不会还能感觉到一点余温。每一个磨到包浆的桌椅都能很具象地表征一个学生,佳言同学不会不知道的。至此,我跟ta的联结已经上了情感,对一个人有所期待就会触发情感线。
老师那筋节虬劲、又青又红的手背撑到“佟佳言”上面,打断了我的视线和思路。我终于听到她说的课文,当我想装模作样地在书本上划重点时,才发现我连笔都没拿出来。于是我把手伸进桌洞里淘了起来,却先掏出一枝签字笔芯。
这突如其来的线索,又一次把我推进“佟佳言”黑洞,我两眼失神,双耳失聪,老师像一团黄色的雾从我面前飘过。
第一,佟佳言的手肯定伸进过我的桌洞,虽然手不会闻味道,但我很希望ta知道我的桌洞有股好闻的樟木味(我趴着睡午觉时也闻得到),不像其他同学有食物的臭味,因为我从来不在学校吃东西。
第二,佟佳言的手伸进来时,会不会想到礼拜五放学前,老师嘱咐我们清空桌肚,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想到能与ta发生这么奇妙的联结。不,当时我根本没意识到这茬,而是在那烦躁倒霉的周五值日,ta要知道这点,会不会怪我呢?
第三,这根笔芯已经彻底写完了,我划拉半天只有前面三下出墨,这说明佟佳言是个节俭的人,家里没什么钱,从小到大都是穿哥哥或姐姐穿过的衣服和鞋。当然也没钱买书,到了五年级才第一次在新华书店买了儿童节特价书,一捆严重缺集的连环画。
不过更重要的是——我换了一边屁股着凳,全身趴在桌上摊向另一边,空笔芯在我下巴枕着的,伸直的手臂末端,在门外很小一片蓝天的背景下,它的笔尖熠熠生辉——佟佳言是个马大哈,这么重要的考试,竟然没有提前检查文具,将这么大的风险一路带进考场。
不知道ta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是管老师,还是管同考场认识的同学借,那个同学会不会是ta从小学五年级暗恋到现在的人,为了上同一所学校宁愿空着最后一道大题的人?
不过也有可能是威胁佟佳言,一会不给抄晚上把你手打折的人。
然后我伸到过道的手差点被人撞折,空笔芯飞了出去,我刚反应过来已经是课间,一个巴掌扇到我后脑勺。
“干什么呢?还在想3班那谁?”一个声音在我上空响起。我没理打我的人,只想抓他手,捞一把没捞住,那人飞快地冲到前面出了门。
“你妈的,给我站住!”我嗷一嗓子叫着跳起来追了上去。
就再没想起“佟佳言”了。
第二节课,我花了十分钟,用口水和橡皮把人名条去掉,我“吭哧吭哧”擦的时候,那三个字没有在我心里激起任何波澜,没有在我脑海里形成任何影音。我把佟佳言忘了个干净,像ta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
这也是这种奇妙联结的美妙之处,光溜溜来,光溜溜走。
我现在想这背后的道理,应该是可能性和空间两个概念支撑的,支撑着这样一线相连关系的美妙。当可能性像肥皂泡一样,在眼前全都坍缩成确切的一饮一啄、一蔬一饭,那简直就是心跳监护仪的平线一样的寂静和绝望。
越少的线索能指向越大的创作空间,用你自己的努力去填补其他的,脑洞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那些类似人名条和空笔芯的线索,就是通往金色大门的钥匙。
当然这里的努力可以是字面意义的臆想,拿《白夜行》里男女主角的关系做例子,作者写在纸面上的内容不多,但读者可以通过寥寥的几次交互为锚点,补充完缺席任何一方的情节。这种臆想都不需要具体的时间地点,只要延续那种感觉就能把自己感动得鼻尖发酸起冷痱子。
也是“雪泥鸿爪”的意境,有所不同的是苏轼用来做比喻,却没有想到飞鸿的一生,那个在雪泥留下爪印的瞬间对观者来说也是很美的。唉,所以中国的文人包括墨客画家,心里只有自己,天地飞鸿都是自己际遇、欲望、诉求、块垒的映射,烦球的很。
还有一种虽然要进行肉体上的努力,但讲老实话,工作量可能还不如臆想。比如在3班那谁家地铁站旁的咖啡厅坐一上午,连隔着窗户望一眼的预设都没有地坐一上午。你可以坐在那紧锣密鼓地处理工作上的事,偶尔抬头想一想那个人就好了,有时候想的是很久以前的她,有时候想的是现在的她。
你不知道她是不是变了模样,是不是已经结婚,甚至不知道她是不是还住在这里,是不是还在这个城市。这都无所谓,你做你的就好了,为了你和你心里的她。
又或者是在图书馆里敲着字,突然手悬在空中,眼光穿过屏幕望向虚空,接着很缓慢地舔了一下嘴唇。这个动作是你最讨厌的一名同事经常做的,在他准备高谈阔论输出观点之前,在他谄笑而尴尬地接领导话题时。
奇怪的是你做完这个动作已经与他和解了,你甚至想到他在他女儿面前应该是个完美的父亲。
后来,在我上大学后,我这“雪泥鸿爪”倒推的能力又上了一层楼,到那时候我连线索都不需要了。我只要在地铁站对面栏杆上坐着,盯着某个人的脸就能做出整个故事。
刚下班的公交车女司机,会把她现在跨在肩上的名牌包挂在驾驶室左边的墙上,每次大拐的时候看完后视镜都会顺便瞄一眼。那不是爱慕虚荣惦记着彰显身份,而是一次美好旅行的念想。
开车的时候她只会撸起一边袖子,因为另一边小臂上有个黑玫瑰的纹身。纹身师傅说黑玫瑰很土,她说就是好看。
她的额前总有一绺碎发,但她从不用发卡把它别住,因为有人说她在上面,俯身看人的时候,那绺头发坠下来,就像它眼光说狂野情话时乱用标点符号,散碎而自由,别提多性感了。
行色匆匆的中年男人佝偻着腰,低着头走出来,公文包夹在腋下,时不时用手去扶一下;另一只手会扣着皮带头,大拇指不经意又很隐蔽地地在内侧轻轻地揉上一揉。他不是尿急找厕所,而是担心尿结石和阳痿哪个会先一步到来。
我从早上第一堂课的教室溜出来,坐两个多小时公车,到城市的另一头,在卖盗版唱片的那条街吃几个包子就溜达到地铁站门口,然后坐在栏杆上看人,想我和ta之间的联结,大部分都是我作为雕刻的手和我要创作的原石之间的那种关系。直到周围的颜色变得很鲜艳,我才打道回府。
我是听到隔壁学校中考铃声想起佟佳言的,它是由我人生中无数个“佟佳言”整合而成,就像你想到某个鲜艳的黄昏,其实它是由你此前经历的所有的黄昏提取纯化,组合而成的。
后记:
我买了个二手钢琴,很偶然的机会听到它原主人的故事,是一个在上海长大的台湾女孩,后来回到台湾念大学工作。我听了她完整的人生,她的家庭、父母,她的性格、外貌,她现在的工作和生活状态。
于是本来冰冷锃亮的琴键一下就暖了起来,而且变得很脏,不是贬义的那种脏,那种龌龊;而是它沾染了很多很多某个具体人的印记。我觉得琴键上到处是小女孩、大女孩的指纹,是她指纹里的盐、汗水,是她吃完薯片带下来的油,是她没擦干的头发滴下的水渍,是她恼怒疯狂砸键扬起的灰。
是她十几年的喜怒哀乐。在某一所房子里,在这个钢琴前,都融入到那些琴键上,在我按下、放开之间,它们都会跃出,洋溢在琴声里,洋溢在光的尘埃里。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