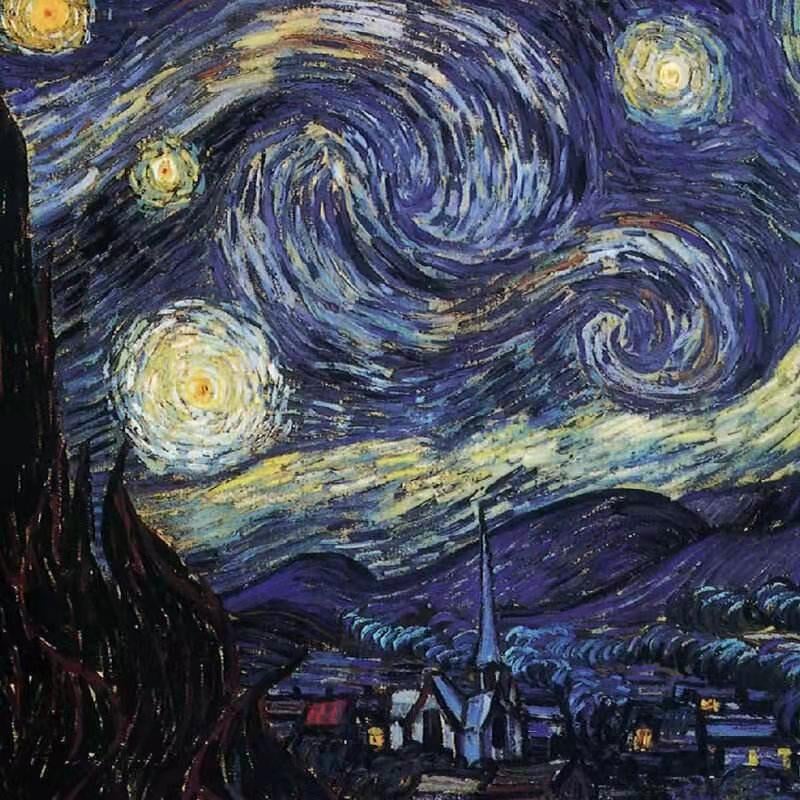被動還是主動:沈從文的思想改造再探析(一)
引 言
沈從文作為20世紀文壇上舉足輕重的人物,其意義已經遠遠超越了一個文學家的角色。在舊中國過來的知識份子中,他已經成為了一個時代的精神符號和人格載體。面臨歷史的渡口,沈從文躊躇了,此時他的心中有只風雨飄搖的小船不知在哪兒停泊靠岸……
在建國初期,沈從文為何離開了他一生為之熱愛的文學領域,封筆轉行,一直為學界所高度關注。經過一次次的思想改造運動,我們可以看到相比於胡風、俞平伯等知識份子,沈從文似乎更為平穩地獲得了進入新社會的通行證。但這種表面上與新政權主流意識形態的步調一致,是否是他最“頑固”的精神基因的泯滅?在自由、詩性的基因與外部要求的價值一致發生衝突時,沈從文是如何處理這種裂隙的?是像以往歷史敘述中所描述的迫於強大政治壓力的被動躲避,還是另有更深層的原因。我們有必要深入他的文字,進入其內心,對他的精神人格進行再探析。
一、向來沉默
1949年,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新中國建立。這在政治上宣告了一個舊時代的結束,也預示著一個新時代的到來。在這一時期,有兩個剝削階級要麼被消滅,要麼完成了自己的“新生”:一個是地主階級,一個是民族資產階級。同時完成“新生”的還有一個社會集團,就是舊中國過來的知識份子群體。
留在大陸的知識份子集團內部,其立場和心態是有很大不同的。按照於風政在《改造:1949-1957年的知識份子》中的劃分:第一種是以郭沫若、茅盾為代表的的激進的左翼知識份子,他們自然滿心歡喜擁護和讚美新政權。第二種是尚在國外的學者和學生,他們幾乎以和郭沫若、茅盾同樣的心情擁抱新中國。這一群體以李四光、華羅庚為代表。第三種是崇尚科學、“不問政治”的自然科學家,以竺可楨為代表,他們以平靜的心情迎接政權的更替。第四種是以費孝通等人為代表的深受西方思想影響的知識份子。儘管他們對蘇聯式的政治制度有所顧慮,崇拜歐美的民主政治制度,但認為留下來自身也能在新社會有自己舞臺的。第五種是以馮友蘭、朱光潛為代表的,他們出於傳統的愛國精神而拋棄了黨派之見,接受了新中國。第六種則是以沈從文為代表的,在歷史上既反對過國民黨,又對共產黨不感冒,試圖超越政黨派別,始終保持獨立的知識份子。
而縱觀沈從文一生的文字,我們就會發現這個一直自詡為“鄉下人”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沉默”與“獨立”二詞是其人生的基調。在建國之後,他一直對自己強調“從沉默工作中補救”、“放棄一切希望,來沉默接受”、“學會沉默歸隊”、“學習沉默而忘我”……然而在早年間,沈從文就已經將沉默作為人生的信條,自覺主動地站在邊緣。在1936年發表的一篇雜文《沉默》中,沈從文寫到,“我依然把筆擱下了。人間廣泛,萬匯難齊。沮洳是水作成的,江河也是水作成的;橘柚宜於南國,棗梨生長北方,萬物各適其性,各有其宜,應沉默處得沉默,古人名為順天體道。”不知是一語成讖還是冥冥之中有感,13年後,沈從文真的把筆擱下了。
貌似是宿命,沈從文用和其他知識份子迥然不同的獨特個性走完了一生。對於他的內心世界,註定是一張無法描繪的地圖,只有他自己或許能看清。我湊近去,勉強看到了“沉默”與“孤獨”的書寫。就像他晚年在《〈湘西散記〉序》中寫到的那樣:“或許正如朱光潛先生給我的斷語,說我是個喜歡朋友的熱情人,可是在深心裏,卻是一個孤獨者。”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