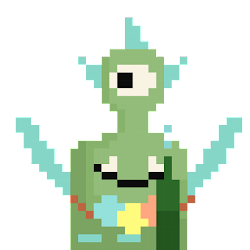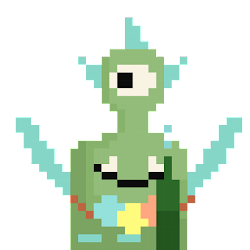讀《煙囪之島》| 願你我在黑夜中,保有熒熒微光
第一次知道《煙囪之島:我們與石化共存的兩萬個日子》這本書,是在幾年前的讀書會上,我們剛結束討論吳明益老師的《家離水邊那麼近》一書,便有朋友接著提議閱讀《煙囪之島》以及攝影集《南風》,然而當時的我並沒有積極地去找書來讀,儘管知道這個議題可能與我所生長的小村庄息息相關;或許是因為不似挨著石化巨獸生活的居民那般窘迫嗎?又或者,隱約之間,我其實並不想去面對這些「事實」呢?
一直到今年年初,有幸參與〈報導者〉贊助者大會,除了決定要提高微薄的定期定額贊助以支持本土獨立媒體外,同時也得到了《煙》這本書;然而還是擱到了近期,自覺身心狀態已準備好,才一掃書上積累的灰塵,靜下心來慢慢閱讀。
在面對特定議題的書時,我總覺得需要在身心狀態妥當的情況下才能「放心」閱讀,唯有如此,當文字在我的腦海裡與任何熟悉的面孔、氣味、聲響產生交集時,我才有勇氣繼續「不麻木地」讀下去。
麻木,是因為「霸權」早已成為日常風景,沉默地一代傳過一代;每當我從居所的窗望下幾百公尺遠,那一排向西延伸而去如衛兵般的高壓電塔時,耳邊竟也響起某日,我因好奇而走近其中一座巨大的「衛兵」底下,令人不安的電流聲響滋滋地擊打著耳膜,似乎在提醒著我,距離愈近,愈凸顯自身的渺小。
「高壓電塔的盡頭就是六輕。」前輩如是說,臉上顯露著無比惆悵;那座石化巨獸,同時也將幾萬畝良田的水搶走,在我們看不見的地底下,以國家之手打造的管線,使命必達;而農民從此背負起「地層下陷」兇手的罵名。
這幾年,在我回到家鄉定居的日子裡,透過親近土地,與長輩交談,甚至去到「現場」;追查「事實」的過程就像拼拼圖,以我的家鄉為中心,擴及台灣島,甚至全球,這些是過往體制內教育所缺失的一塊;住在高雄大社工業區旁的青年吳宗穎曾說:「我完全不知道大社工業區要跟著五輕一起遷廠這回事,二十五年可以讓很多事情被遺忘。」(頁345)
這不禁讓我思考,也許在追查事實之前,我們更應該要問的是:
為什麼不知道?我們的社會或教育現場正在教給下一代什麼樣的環境意識呢?
階級與靜默
夏日南風起,遠方的煙囪一年四季「氤氳」著。這次輪到哪個村庄的窗口緊閉呢?
對於居住在雲林台西鄉的蚵農林進郎而言,此刻是否能夠稍稍大口喘息?在凜冽的冬日裡,南風於他確是奢侈的想像,他曾說 (頁173-174):
「海洋中細小生物對於環境的改變是極其敏感的,它們會用你看得見的語言告訴你這一切的改變。環境不能用想像;它與我們的共生關係,只有到現場親身體會。」
蚵的生態改變只有蚵農最清楚,然而有誰願意來聽聽看呢?原來產業也是有階級的,他問我 (筆者許震唐):「農漁業在產業的階級中排行第幾?」我們彼此靜默良久。
而靜默,不只發生在蚵田。
2015年八月,雲林台西鄉七十四位居民決定對台塑六輕提出汙染傷害訴訟;在法庭上,台塑律師團提出,原告必須指出是「哪一根煙囪」排放「哪種有害物質」,在「何時何地」吸入「濃度多少」的汙染物;台西鄉民委任律師洪嘉呈忍不住反駁:「這可能連神明都做不到啊!」 (頁139)
我總覺得這與性暴力受害者在法庭上的境遇很相似,兩者皆必須奮力維持「完美受害者」的形象,以及「具體」提出如何受害。
權力不對等的情況,亦從法庭延伸至庭外,當大企業的回饋金造成地方分裂,而多數原告仍需背負龐大的經濟壓力。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彭保羅也指出 (頁143):
現有原告因為創傷太深,親人接連死亡,已無法訴說自己受害經驗。
對誰網開一面?
居住在彰化台西村的漁夫許春財,在提到近年來因濁水溪水量不足等因素,而捕不到鰻苗這件事時,他說 (頁178-179):
「有時我們對於大海也要網開一面。」總有海洋也不一定順遂的時候,跟人一樣都要彼此體諒。
這讓我想到家中的舊版戶口名簿上,有以清秀筆跡寫著的「世代務農」四字;當家族中有人因為天災而蒙受嚴重的農損時,他們總是逆來順受地說:「無法度啊,咱就是愛看天公伯吃飯。」
學習面對無常,大抵是長年向大自然討食的人們所必須學會的第一課。然而,表象的因果,背後是否有更龐大的政治經濟因素在角力呢?當第一線的農漁業工作者,選擇對某種不可控的因素「網開一面」時,是否 (在不知情的情況底下) 亦不慎「輕輕放下」過往掌權者的某些錯誤決定呢?
2013 年,為了讓高雄林園區的中油新三輕「順利上路」,經濟部工業區召開專家學者的閉門會議,最終結論,政府連同「專家學者」提出:「新三輕的致癌風險雖然大於百萬分之一,但還在『可接受』的合理範圍內。」(頁394)
「可接受」三字,是政府與專家學者們對重汙染石化工業的「網開一面」;而林園區居民又再一次被「輕輕放下」。
在犧牲的體系中,某些人的利益是從犧牲他者的生活(生命、健康、日常、財產、尊嚴、希望)之中產生並維持下去的。 (頁396)
被犧牲的那方在遠離政經中心的窮困偏鄉被隱蔽起來 (雲林麥寮的六輕),或者在國家經濟發展的大旗下「尊貴的被犧牲」(1970 年代十大建設的大社、林園石化工業區)。(頁396)
發號施令、制定政策的在台北,而被鑲嵌進犧牲體系中的環境難民,位於台灣的中、南部。 (頁396)
掠奪,萬劫不復
2015年,位於高雄的後勁社區,儘管「以人作為最強資本」,在歷經二十五年抗爭後成功使五輕關廠,家鄉卻早已成為全國最大污染場址,受傷的土地是否能在下一個二十年恢復生機,仍是未定之數。
隔年 (2016年),蔡英文總統提出「新南向政策」,力求透過「經濟互惠」鞏固友好國家,然而,若將島嶼的鏡頭朝「更南的南方」特寫;同一年,以「Formosa」之名,在越南中部沿海設廠的台塑企業,因排放有毒氰化物等廢水,爆發長達 200 多公里的沿海汙染事件,一夕之間漁民頓失生計,約20萬人口受到影響——在國際新聞的街頭抗議照片裡,人們高舉著「Formosa Stop Poisoning The Sea」的標語,而一名年僅22歲的越南青年遭判刑七年,只因他在網路上進行相關報導。
「福爾摩沙」自此,從引以為傲的身分認同,墮入一團無法揮去的雲霧裡,如濁水之盡頭那四百根煙囪日日吞吐的「水蒸氣」,又酸又臭,幾要窒息。
如果一切都停在這裡
從六七零年代起,島嶼的石化業從搖籃,一路由黨國母親細心哺育,直到 1980 年代初期,當時的行政院長孫運璿曾試圖推動產業升級,並投入低汙染的石化高值化,然而 1984 年二月,孫因中風退出政治圈;繼任者俞國華以既得利益者之姿,「成功保住」石化業。
如果一切都停在這裡,那麼便沒有五輕、六輕的興建,也不會有日後七輕、八輕 (國光石化) 曠日廢時的抗爭與推擋。 (頁28)
此刻,我想起那位居住在彰化大城鄉台西村的阿嬤,她在那段曾遭瘋狂轉發的一分鐘演說影片裡說道:
我每一次若是想到我們台西村民未來的命運,我就想到那群消失的海鳥。

幾年前,我曾隻身去到彰化大城台西村的出海口,也許因為當時是冬天吧,空氣中並無明顯酸臭味;左顧右盼的我,試圖在這片廣闊似無邊界的地域裡,尋找其他人影,然而天地之間,似乎只剩我一人,與身後不遠處,緩緩朝西流去的涓涓細流,是濁水溪。
不畏刺骨寒風,我脫下鞋子,將褲管捲起,赤腳踩上退潮的泥地,蹲下來觀察地表上無數的孔洞,偶爾看見幾隻螃蟹忙進忙出;像孩子一樣,忍不住伸手把玩腳下的泥砂,試圖感受與家鄉土壤相似的熟悉觸感。
遠方的夕陽即將落下。
我閉上眼睛,想像,在南方的石化巨獸出現之前,這裡曾經是什麼樣的景象呢?
而未來,我並不敢去想。
但是,
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時代,人們還是有期望光明的權利,而光明與其說是來自於理論與觀念,不如說是來自於凡夫俗子所發出的熒熒微光。當眾星火看見彼此,每一朵火焰便更為明亮,因為它們看見對方,並期待相互輝映。 — 漢娜·鄂蘭 《黑暗時代群像》
願你我在黑夜中,保有熒熒微光。
參考資料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