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并不存在的南方小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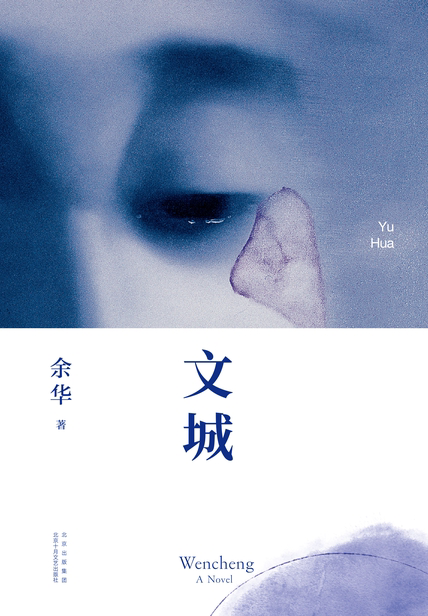
我记得《文城》发行是在 2021 年的春天,或许在其他年份就没有什么不同寻常,但那是新冠大流行、中国“清零政策”下的春天,就有些暧昧,无端承受了所有不合时宜的目光,或者又刚刚好。我不知道,这一切还需要时间来检验。
当时媒体的推荐语是“暌违八年”,人们的期待又好像是数十年那么久。我个人的感知是超过了一个世纪,虽然我第一次读余华是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他最著名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也确实诞生于上个世纪,并曾经入选“九十年代最具影响的十部作品”。

我直到 2024 年新年之初才读到这本小说,那种期待的感觉消退了不少,毕竟“清零政策”下那种惶惶不可终日的集体恐惧也终于消退了一些,我已不再和众人共享一种对生的期待。是的,我感觉余华的小说,也承载着这个期待。他不但是个作家,也一举成为互联网时代的宠儿,媒体的宠儿,他似乎很有这方面的天赋。
于是对于那些从九十年代、零零年代,甚至是上一个十年间一路走来的读者,他们恐怕很难接受这样一个余华。

我看到《新京报书评周刊》在《文城》发行时提出同步批评:“并未重返《活着》巅峰,仍然很平庸”、“从《兄弟》开始,他的写作日渐粗鄙化,就好像一个暴发户,再也不吝惜自己的语言,恣意而放纵。”
说老实话,这个批评有点吓到我了。我自己也不看好《文城》,甚至开玩笑说“足够土”。但我不认同说作家就“必须要珍惜自己的语言”,我觉得这种批评是相当可笑的。
我注意到这篇评论中的一个细节,余华是中国纯文学作家中少有的,甚至有可能是唯一一个,仍然具备强大市场号召力的作者。这也是我自己感同身受的。但我心说,你们都已经这样了,还能指望谁有多大的市场号召力,谁还愿意写啊。
通篇批评余华的平庸,跟不上时代,对过往文学素养的背叛,在我看来就更像是指责亲戚小孩不争气。人就一辈子,怎么可能写的都是《活着》,还不能有点别的写作志趣了。
我也不是要为《文城》说话,我承认确实难看。但我的意思是,为什么不允许这样的作品出现,为什么不允许作者作出尝试,哪怕是糟糕透顶的。说白了,余华哪怕就是玩,就是在混呢,就是滥用自己的语言,那又如何呢,他不能这样做吗。是不是他写什么还得我们说了算,他得对这个时代负起巨大责任。——这就要回到我们这个国家诡异的文学观了,以及男人为主导的文学观,就是强调价值、责任,不在此列的被批得体无完肤,在此列的就要看具体姿态,姿态不好看了也同样完蛋。
我现在已经不觉得写作、文学创作是多么伟大的事,要为之付出生命的事了。我觉得就跟每天出门去买菜,回家做饭一样平常,日复一日,照样是旷日持久、苦心耕耘,且有食粮满足自我,多余的满足家人伙伴。
去年看到《界面文化》写越南裔诗人王鸥行,他在 2016 年因《夜空穿透伤》成为史上最年轻的艾略特诗歌奖得主。在完成《时间是一位母亲》这本诗集之后,王鸥行曾经想过:“我已经写出最好的一部作品了吗?”和大部分的作家不同,他认为,就算是这样也没关系,“我真的不觉得一个作家只要活着就不应该停下笔。我的写作目标不是非得要出版多少本书,而是这本书能不能让我就此对自己满意。我宁愿在写出一本好书后封笔,也不愿意一直不断写下去。”
这个价值观可能是震惊中国人的,就像 2018 年的《创造营》,杨超越不用努力就出道,粉碎了我们中国人的一颗心,你怎么可以不努力,而且不努力还能站在舞台上,那我们努力的人要怎么办。
我觉得回到余华身上来看也是一样的,他首先为他自己写作,哪怕写完《文城》是一本坏小说也无所谓——虽然这话在读者听来格外刺耳,像是背叛了读者似的。但换个角度想,如果一个作者不能首先忠于他自己而写作,我们能奢望他写出什么样的作品呢。
我们的朋友金梨就曾经说过:“奇迹都是在被宽容的时候产生。”读者顶多也就是说句不好看,不喜欢,下次不读了。但中国的文学评论家们,动辄就是“道德伦理”、“时代精神与责任”,实在有点夸张了。我知道,这个“宽容”与否也另有原因在,但至少,以媒体主导的评论还是要怀抱着一种将作品介绍给读者的朴素理念吧。
写作,知识分子,在中国被赋予了两种极端属性,要么就是崇高到让人五体投地,要么就是下贱下到深渊里。你一旦拿起笔,要么承担的是主旋律的那种价值,要么承担反对前者的“有识之士”砌起的另一道价值。中间是广阔,但几乎已寸草不生。实在枯燥。
《文城》是一座已然到了、但似乎永远也到不了的城,不管是在作为起点的北方老家、艰难路途,还是南方暴风雪后的目的地,都是贫瘠的,寸草不生的。只有阿强和小美虚构出来的那个文城是丰沛的,氤氲的,怀着爱意的,就连主人公林祥福对女儿超脱的爱,似乎也是建立在关于文城的谎言中,他确信那里住着他女儿的母亲,找到她,生命将会再次变得完整。
我在叙述这一点的时候,惊人地发现,跳出小说语言的“土”,这个设定折射出一种轻盈,反而是我在诸如《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之中尚未发掘的。以及小说中林祥福的尸骨运回北方,在途中歇息,灵柩正好在小美和阿强的坟墓边停留,《新京报》那篇书评里给出了较为正面的评价,说是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的另一版本。我觉得这一幕是美的,是可以用审美的眼光看待的,就连对这本小说不买账的人,也罕见地想起了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坟前化蝶。
我重新翻了《活着》,余华在序言一开始就表达,他是为了他的内心而写作,但是小说末尾所附的大量评论还是说,“这是一部描绘二十世纪惨淡生活的作品”、“是二十世纪中国的全貌”、“二十世纪中国史”,所以是否可以承认,很多人看这部小说,这部文学作品,仅仅是以“真实”来判断和衡量的。也就是说,你面对《活着》,你点评不出一句“土”,也不敢这样点评。你甚至无法用“审美”的眼光打量它,那样会显得异乎寻常的轻佻,以至于冒犯了中国人的感情。

可是到了《文城》,我就认为可以这样说,实际上我也这样做了。我就是觉得它“土”,因为我在审美它的语言,审美它的一切,文学的角色,文学的感情,而并非它的真实性,也并不在乎它是否还原了小说所依托的那个历史背景,什么剿匪,什么军阀,我不在乎。
而且我觉得有些人批评他跟不上时代,还在写“乡土”,也是不客观的。我自己看下来,就觉得他是找了一个更深的历史褶皱,在坐标上一指,然后开始建立他的故事,玩他的游戏。你以前看他写《活着》,写过时的六七十年代,那他索性再往前走走,一下子就将故事拉回了清朝灭亡后的《文城》。他要为他的内心写作,而不是记录时代,记录历史。
我觉得小说家作出这种尝试,可能才是真的开始写小说了。
我们也不用急着批评《文城》,先学习一下,也尝试“审美”,接受完全的虚构,和一切不合理。哪怕得出的结论是“不好看”、“不喜欢”、“土”。那样或许我们也是真的开始欣赏小说了。
2024 年 1 月 29 日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