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文學書介|七等生〈我愛黑眼珠〉
本文為台灣文學發展基金會(文訊雜誌社),「區域文學史」計畫專稿。
七等生(1939-),本名劉武雄,生於苗栗。活躍於1960-70台灣文壇,創作以小說為主,兼以詩、散文。小說多取材自作者本人的生命經驗。〈我愛黑眼珠〉雖然沒有明確地點得以指認,卻是區域文學不容忽視的一篇。因為七等生活躍文壇的時期,正好是台灣出口導向,也就是快速資本主義化的時期。而各地鄉鎮(包括苗栗在內)都面臨快速現代化,以及人口往都市聚集的情形。像〈我愛黑眼珠〉的李龍第這種到都市打拚卻缺乏存在感的年輕人,恐怕到處都是。此外,〈我愛黑眼珠〉收錄在1969年出版的小說集《僵局》,所涉及的倫理爭議引起當時文壇一陣譁然和討論。有必要簡介情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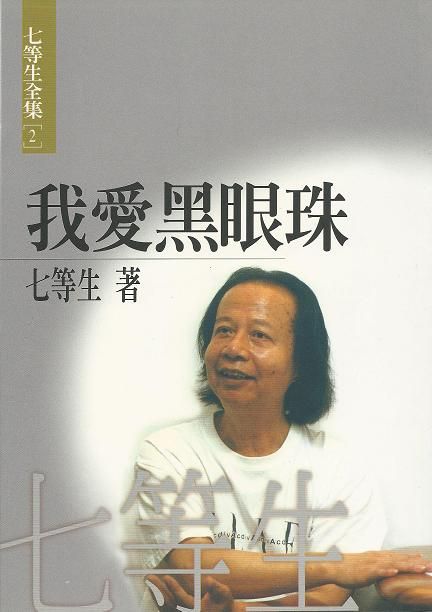
李龍第出門是為了赴妻子的約然後回家,冒著大雨而且不斷錯過妻子。回程路上,李龍第抱怨著這座進步的城市以及冷漠的人群,卻被一名妓女打斷。原來大水淹沒、災難加劇,一名妓女因為體力不支而昏倒。李龍第於是背著她爬上屋頂避難。李龍第抱著妓女的同時,發現晴子在對面屋頂上。晴子隔著暴漲的水流呼喚李龍第,見到他注視著懷中的女人,便怒不可遏地哭喊起來。李龍第在旁人的質問下,莫名自我介紹為亞茲別,並直指對面屋頂的女人是瘋子。直到大雨停了、水逐漸退去,亞茲別將妓女送往車站後,才突然恢復神智般地說好想念晴子,以及他在大雨中要尋回妻子有多疲倦。
過往論者質疑李龍第捨妻子、救妓女的舉動,並不符合人情。張誦聖教授認為,李龍第為了彰顯自己的人道關懷而救妓女,賠上了原本的家庭也無關痛癢,其實出於自私。
把〈我愛黑眼珠〉放在災難文學的框架下思考,我才發現七等生小說也適合理解人與地方的關係。李龍第出門是為了赴妻子的約然後回家,目的地明確,過程卻曲折。途中他遭遇不友善的汽車、天氣與人群,特產店的老闆的羞辱,連公車乘客都充斥鄙夷不屑。這段路簡直李龍第過往人生的縮影,反映他不為這城市所接納從而迷失在人生路上的兩種意涵。如同范銘如教授認為,七等生把角色缺席的過往人生表現在現在的具體道路上,這種做法無非受到現代主義影響。
此外,「在路上下大雨」的設定相當重要。
第一,「道路」作為展示陌生人彼此相遇的舞台,用來合理化主角與各種人物相遇的情節。如同巴赫汀所言:
「在這裡(道路),人們命運和生活的空間系列和時間系列,帶著複雜而具體的社會性隔閡,不同一般地結合起來;社會性隔閡在這裡得到了克服。」
第二,只能發生在道路上的「大雨」,一方面渲染李龍第的悲情,一方面提供他一個表演舞台。李龍第藉由在雨中拯救一名妓女來證明他「被需要」,進而打造英雄救美、凱旋而歸的崇高形象。可惜的是,災難雖然是存在主義文學用來質疑倫理規範的主題,不過在情節上的漏洞卻削弱了這種功能。因為李龍第的這場「征途」並非為了質疑家庭、都市對人的束縛,而不過是他用來贖回個人尊嚴的荒謬演出。
「在大雨的路上遇見妓女」的設定,出現在都市比起鄉村更多批判的機會。但李龍第顯然更在意個人尊嚴的頹喪而非個人對地方的剝削。災難文學通常用來反思人類對自然、地方造成的破壞。〈我愛黑眼珠〉顯示出個人面對災難時所面臨的道德困境,提供災難文學更多思考和批判路徑。
參考文獻:
七等生,〈我愛黑眼珠〉,《我愛黑眼珠(七等生全集2)》(台北縣:遠景出版,2003年)。
蕭義玲編選,《七等生(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47)》(臺南市:臺灣文學館,2013年)。
張誦聖,《現代主義.當代台灣:文學典範的軌跡》(台北市:聯經,2015年)。
巴赫金,〈小說的時間形式和時空體形式——歷史詩學概述〉,收入自氏著,白春仁、曉河譯,《巴赫金全集第三卷:小說理論》(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范銘如,〈小說中的線〉,《臺灣文學學報》第三十期(2017年6月)。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