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0|风沙卷起大国:徐庄骅(Jerry Zee)新书分享会笔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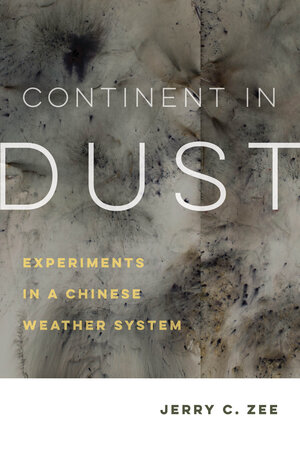
2022年的春天又是一个风沙蔓延的季节,根据气象信息,4月下旬的风沙从西北一直南压,华北的天空泛起肉眼可见的黄色。
中国的气候一直处在变化之中。几十年的改革使这样的气象变化成为了常态。季节性的沙尘暴和空气污染重新界定着中国及其下风地区的土地与空气之间的物理、政治关系。结绳志在1-2月新书书讯中推荐了普林斯顿大学人类学系助理教授徐庄骅(Jerry Chuang-Hwa Zee)的新书《沙尘中的大陆》。这是一项关于异常天气的政治人类学研究,讨论的是国家战略、地形地貌、大气环境和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其内容涉及从试图影响沙丘运动轨迹的内陆地区的国家工程项目,到京城之内被重塑身体和大气空间。
几个月前,徐教授就他在中国进行的这项研究举办了一场面向学界同仁的新书分享会。普林斯顿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生倪燕萍为我们记录并翻译了这场分享会的内容。分享会上,徐教授通过自述与问答环节进一步说明了他的研究过程、与科学家一道的工作方法,以及民族志写作思路。对中文世界的读者而言,徐教授的写作或许并不好懂,但不难发现的是,风沙之于他正如松茸之于罗安清,他要做的不只是在中国研究风沙,而是以风沙为方法来研究中国,探索作为天气系统的当代中国的形成。沙尘扬起,“飘升”(rise)至大气系统,而中国的上升/崛起(rise of China)又意味着什么?
仅以这篇推送,抚慰置身春日风沙中的读者。
记录、翻译 / 倪燕萍
编辑 / 安孟竹
原文發布时间 / 2022年5月5日
01. 新书简介
徐庄骅的自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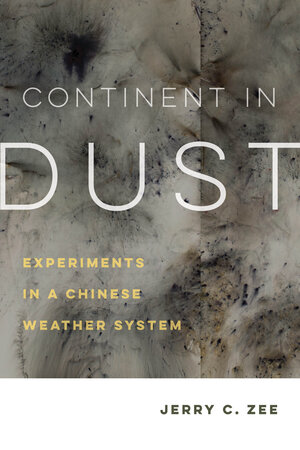
这个研究可以追溯到2007年。当时我刚刚大学毕业,在中国生活了一年,为一个治理沙漠化、预防沙尘暴的政策项目工作。我是少数几个持续、长期关注这个话题的人之一,而同时我的理论框架和对民族志的感知一直在变。我把这本书当成是我在第17次重新展开这个课题之后生成的一个“怪异的文档”。这个课题原是我的博士论文,但我完全重写了这本书,或许是出于对我所接受到的人类学训练的反叛。我希望的是从中获取一些乐趣。那个时候我还在做博士后,对自己和大学这个机构之间的关系有多么不稳定并没有多少概念【注:在北美学术界,拿到终身教职之前的生活往往是不稳定、缺乏保障的】。每当有人问我这本书的受众是谁,我很难给出回答,因为我当时决定的是,这本书就是为了我自己和我三个朋友而写的。现在我重新读这本书、重新翻开不同的章节,我自己都有一些讶异,因为其中很大一部分都只是记录我和各种人之间的对话,以及长远来看这些人如何塑造了我的学术思考。自己的声音和其他人的声音产生联系,这对我来说是很奇妙的感觉。
今天我们可以讨论政治【注:Zee指的是广义上的政治】。这本书是各种不同事物碰撞的结果。我能感觉到我的思考不断被各式各样的想法塑造着。这大概是一个被Marisol De la Cadena称为“汇聚中的差异”(convergent divergences)的过程:事物或想法被挤压到一起,而他们的汇聚点会形成新形式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这是我从“视差”(parallax)这个概念中所学习到的。我希望通过观察一个情境中相似的和有微妙差异的部分,去理解一些看似可望而不可即的事物。我认为,民族志的研究是与揭露差异息息相关的。这些是我思考的比较多的问题。
当每个人都说着相似的内容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当我们开始把一些微观上的区别放置在现有的视角下时,又会发生什么?这是我最初思考的问题,因为它们帮助我重新审视我的田野调查,那些我在林业专业人士、行政人员、环境学家和物理学家帮助下所进行的研究。通过这本书,或说这本书所代表的一种实验,我尝试问我自己一些分析性的问题:当像风沙这样一些边界物质的聚集形成了这些邻近的模式或知识系统,你怎么去思考它们?你的情调(attunement)和关注因这些(物质)得到延展,又返回这些物质中,这究竟意味着什么?现在我在一个跨学科的环境研究所任职【注:普林斯顿大学的High Meadows Environmental Institute】。这让我有机会去思考和环境工程师一起工作可能意味着什么。他们是深切关注着环境问题的、却并不总是能触及到人文层面话题的一群人。那么,对于我们人文社科的学者来说,和他们对话可能产生什么意义?当然,我所说的这个意义不仅限于在公众话语空间里传播科学知识。

以上涵盖了我在田野调查和写作过程中的很多思考。如何与科学家进行沟通?如何思考不同知识的碰撞?分叉点?汇集点?当我重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想到的是,这整本书是围绕着对于同一种事物的不同的(甚至是怪异的)追踪过程展开的。研究沙尘(dust)有一些不寻常的地方。首先,因为沙尘在地理空间里的运动轨迹,我们很容易将其解读成中国的全球化在环境问题方面的一个回响。这些尘精准地勾勒出了环太平洋区域,描绘出中国人(尤其中国的制造商)在各地的运动轨迹。我们如何能在讨论相似性的同时不忽略差异性?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科学家们往往会制定出非常精密的、有学科特征的、有历史政治痕迹的框架来研究物质。我从中汲取灵感,希望能把(思想的)碰撞点当成是一个略有些混乱的交织状态,身在其中的每一个个体的思维都会在受到一些冲击后得到重塑。
与之相关的是,我会使用一些特定的语言或词句。比如,在本书的简介中,“万花筒”这个概念帮助我思考这些问题:做一个关于物质、环境生成形态的民族志到底意味着什么?这其中总是包含着物质的变化。我将其称之为“相移”(phase shift)。同时,关于试验性(experimentation)的问题使我重新思考中国的政治及其针对环境问题展开的一些举措。我觉得不少政治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对于中国的理解无法让人信服。在环境社会学中有两种互为张力的观点,即认为中国的环境问题,要么会带来民主的变革,要么会走向更深的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我认为这两者说法都无法解释现实情况,也没有对威权主义和民主主义进行有效的理论化。
我从2010年代早期开始写作,很清楚地意识到唯物主义的STS(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的基本观点,即我们应该关注到那些非人类的事物,他们很重要,因为他们是置于(各环境中的)。这种关注(noticing)的态度本身就是STS的核心论点,对吧?我想弄明白的是,这种关注在具体的分析中能有什么样的创造力?在沙漠化防治和环境工程领域工作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沙、风、尘是真实存在的。我感兴趣的是,当我们对这些物质的物质性(materiality)感到习以为常时,会产生什么效应?
我是在和一些特定植物【注:如书里提到的梭梭树和肉苁蓉】的种植者的交流的过程中开始思考这些问题的。我们聊了他们如何种植这些植物,而这些植物会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什么,这一切又如何重新定义了他们与市场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一种“植物性的耦合”(botanical coupling)把社会主义重组进了这场试验性的环境危机之中。这难道不怪异吗?我很喜欢这个观察,因为它促使我重新思考我对关于中国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China)并不满意的部分,即每个学者都对“新自由主义主体性的汇聚”(convergence of neoliberal subjectivity)感兴趣。在这种框架之下,我们拥有的常常是一个由消费主导的、理性的行动者(actor),而渴望(desire)变成了政治主体性的基础。这在我看来并不总是正确的。如果你和林业从业人员交流,你就会发现他们对人的行为的理解完全不同。
那么,怎么去想所有的这些事物?怎么去思考这种“植物性的关系” (botanical relationship)?怎么去分析这既是物质性的、又是政治性的关系?我觉得,你得非常仔细地观察,观察大家是如何发现了一些技巧来完成事情。我会把寄生状态想成是一种奇特的转化或转移。在寄生状态下,存在的是一个被损坏的“耦合器”(coupler),一种持续存在的、但也不使一种事物被融合到其他事物中去的状态。我发现那其实也是行政人员讨论经济改革和生态破坏之间关系的方式。如果你读这本书的其他章节,你会发现这种思维也适用于关于社会生活规范和农村问题的讨论。这便是我所说的“植物性的关系”。诸如寄生状态的思维涵盖了很多地方的很多问题。当然,这种关系同时也是地理性的、气象性的。

最后的一个章节,本来并不是我的博士论文的一部分,而是受到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的一些气象学家的启发后的产物。出于科学上的、政治上的兴趣,他们都很想知道有多少的尘是从中国来的。一个气象学的事件(如沙尘暴)是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志/田野调查的边界的。它们是不断跨越边界的。我觉得我必须要追踪这种空间的逻辑及其涉及到的所有事物和过程。因此,最后一章涵盖了整个北半球。我当时在圣克鲁斯(Santa Cruz),很有趣的一个地方,总有人告诉我一些奇闻异事。这对我来说再好不过了。我觉得这是在各种环境议题中我们都应该汲取的学术“养料”。我碰到了兴趣迥异的人,有人对水银的甲基化感兴趣,有人对鲸鱼感兴趣,等等。当我告诉他们关于尘的漫长移动轨迹时,他们都会说:“哦,对,那种尘雾!”
这些经历都不断给我灵感。我一直问自己:你想要做什么?你怎么去看待这些复杂的问题?思考本身的意义又是什么?这本书想要完成的其中一件事情是,偏离环境研究总是以生物学为主的这一倾向。地理学和生物学之间的交流其实可以带来另一种思考身体(广义上的body)的方式。我喜欢那些云和鲸鱼进行类似的生物化学反应的时刻,那些雾云和尘云出于不同的原因互相影响的时刻。当然,所有这些问题都会归结到这样的一个点:我们如何把这些问题和观察表达出来?有多少关于中国的社会变迁的知识被创造出来了,而这个研究又将带来什么?作为社会科学家,我们如何不断突破边界、提高我们的思考能力?以上便是这本书。
02. 问答环节
关于沙尘暴的起源,关于工业化和现代化
沙尘暴的起源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有不少地理学家也都在研究这个问题。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很难精准定位沙尘暴的起源究竟是什么,而与之相关的政治问题也比较庞杂。中国政府认为,沙尘暴频发及相关的内陆沙漠化和土地退化问题是有一系列的源头的,而这些源头又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变化。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不合理的土地使用常常被认为是一大原因。我把这解读为自70年代引进了市场政策之后的一种效应,就像我在书里所分析的。同时,我觉得这也和土地权/土地使用相关的立法有关,与社会主义高度发展时期到后来的过渡有关(后者是围绕集体的游牧来进行的)。最初是由来自不同家庭的生产队在大片的牧区上放牧,但到了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文革之后及改革开放初期),大量出现的土地改革,促成了一系列转折。第一,大片的草原被划分,被再分配给了家庭单位。但这些被划分的、小块的土地很难满足季节性的放牧,于是这时候就出现了更密集的放牧。这是土地改革的结果。第二,这些地区改革早期的一大特点是,为羊绒等产品开放市场。但突如其来的市场压力(和急剧缩小的放牧面积)给这个早已适应社会主义制度的地区带来了别的问题。很多牧人回忆起来都觉得那是一个很困难的时期,面临着市场和生态的双重压力。一些人回忆说,他们不得不在几年内让自己的牧群增长十倍,从而去补偿社会系统的供应(过去是社会系统自动补足)。总之,这些问题与中国的现代化改革有紧密联系。
关于城乡(距离和联结)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中国的城乡变化所带来的张力是很强的。一部分的背景是,乡村几乎都被“挖空”了,因为很多人搬去了城市,在各种制造业工作。如果你走过中国的很多乡村,你可能只会看到孩子和老人,因为其他劳动适龄人群基本都离开了。这是90年代、甚至今天都很典型的一个趋势。在我调研的阿拉善高原,大型的环境政策或说环境实验得以推行的一大原因是,沙尘暴指向了城市及其内陆腹地之间的关系,并且这关系是公共的。我对阿拉善高原的兴趣,不仅是因为其地域上的偏狭性,更是因为其与北京之间的“中心-外围”(core-periphery)的远距离的关系【注:Zee特别提到从北京出发到其调研点约需48小时的远途大巴】。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在中国,沙尘暴常被当成本国的问题来讨论,虽然风并不会随着国界线停止,也的确有不少尘土也来自于其他地方。在中国沙尘暴就果断是一个国内的问题。然而, 如果你问任何一个韩国人,他们都会说这是一个国际问题,甚至会点出内蒙古作为一个更具体精确的来源。这种区别是很重要的。最后,我想强调,我所讨论的一些林业的实验是有历史的,其背后有几十年的共产主义的试验在不断尝试弄明白什么样的政策应该在乡村得到推行。这些试验对于我们现在理解中国乡村的现代化也是不可或缺的。
关于概念化和理论化,语言和写作,以及民族志的探索与突破
我会思考,相较于正统的、准哲学式的人类学而言,这本书可能会是什么样的。我在伯克利接受的训练是很福柯式的,而学生都像是后福柯式的学者,思考着知识在什么影响下产生等问题。我当时学习的也是受此浸润的STS领域。然而,在这种框架下去思考尘这样一个自由移动的物体是很困难的,因为你会局限于权力(power)在这种情境里的具体呈现。我很幸运,我的博士委员会中一半都是地理学家,所以他们并不(以这种框架)限制我的研究,我也不需要用某种特定的语言来为自己辩护。这给了我很多空间去探索。我希望呈现的是,对尘的研究并非偶然,而是真的可以打开某种学术思考。同时,这不是诗歌,这更像是提供一个隐喻,而这个隐喻可以形成一种思考框架。我想证明的是,与尘有关的思考不只是一种话语空间(discourse)。这也是我对于2010年代一切关于物质性的学术讨论的一种特殊的回应。我最初设想的博士论文甚至是没有任何人类行动者的(human actors),虽然这个设想出于种种原因没能实现。
“风沙”为我提供了一种思维方式。我开始思考各种人是如何讨论和看待风沙的,一系列关于物质转移的语言(即便不成熟)又是如何产生的。同时,我自己需要一个介于抽象和具体之间的中间状态来作为我的“脚手架”,帮我探索不同层面的事物。这可以延伸到很多点。如果风沙是一个瑰丽的图景,包含了各种关系庞杂的、不可删减的、具体可感的事物的成形过程,那么我的民族志思考也是如此。我没有试图去开创什么新的东西,更多的是在尝试搞明白一些成形过程。比如,第二章涵盖了各种国家运作机器,但是它们是以一种不常规的方式被组织在一起的。我尝试通过事物的成形过程来思考,而这种思考只有在我找到了一些与物质转移有关的语言之后才成为可能。总之,风沙这个概念为我提供了很多很多,赋予了这本书一个便于理解的结构。还有一个方面是,对于国家中央政府来说,这种形状/结构也是政治地理学的结构。追踪物质转移的过程,也是看到“汇聚中的差异”(converging divergence)的过程。我有幸记录下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得以暂居在一个正在经历严重土地退化的地方,我看到的沙尘暴就是那种物质转化的一个直观的结果。
在写作中,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是,如果你观察的是一个正在发生的环境事件,而你又不想简单地把国家看成是主体(subject),把地球看成客体(object),你可能会陷入一种混乱,因为你发现语言不再履行其本来的职能。英语中没有什么动词可以用来描述风沙,因为风沙并不按照我们所想的那样在运动。我最近读到Jane Bennett的新书《涌入与流出》(Influx and Efflux: Writing Up with Walt Whitman)。她讲到的一些东西帮助我重新思考语言这回事。对我来说,这个问题关乎学术分析,也关乎民族志写作。我们并不是在发明一种崭新的语言去实现什么,而要去看到,经过了交流和碰撞后,现有的语言获得了它们本来所不具备的新的含义。因此,这本书也意在让读者产生一种(和他们原本熟悉的语言之间的)疏离感。这是全书的论点之一。比如,在第二章中,市场是市场,但又不完全按照一个市场的逻辑在运作。它仿佛具有市场的很多特征,又好像不完全一样。
规范性的学术写作对我来说一直都不是容易的。总是有很多人告诉我,这种写作应该是“直率”的。你可以会发现这本书没有什么(传统意义上的)学术论点。如果有的话,那也是被逼迫的([笑])。我觉得论点是内置于排列不同事物的过程之中的。这本专著自身就是一个论点,只是这论点体现在形式上,而非内容上。我读博士的时候,很多朋友都是英文系的,所有我的很多想法也受到他们的启发。他们时常讨论文学形式和写作样式的问题,因此关于体裁/流派(genre)的问题也常常围绕着我。我想明白,什么样的体裁能帮助我们开启另类的关于民族志范式的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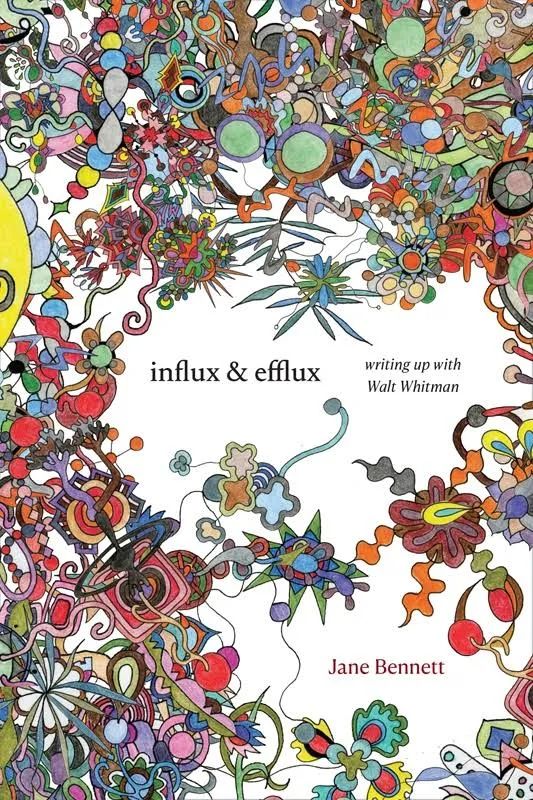
Jane Bennett的《涌入与流出》借助惠特曼的一句诗提供了在充斥着强大的非人事物影响的世界里思考人类能动性的精彩分析。
关于不同的尺度,及人类学家在其间的穿梭
这回归到了关于尺度(scale)的问题。我从罗安清(Anna Tsing)那学到了很多关于尺度的思考。这对我的课题来说很重要。从气象学上说,研究尘绕不开规模的问题。比如,一个沙丘和一个沙尘暴涉及到的就是不同尺度/规模的颗粒。对我来说,尺度还涉及到一种浪漫化的倾向,但我不停训练自己抵制这种倾向。在做这种民族志的过程中,我容易对长期呆在一个地方感到厌倦。我需要不断移动,去到新的地方。跟踪一个环境事件其实满足了这个需要。其本身是一个大规模的事件,但我需要找到一个着陆点。这便体现了民族志的重要性。我常常和做环境人文(environmental humanities)的学者交流。我们发现追踪环境问题能提供一个契机,让我们去思考以前无法被思考的问题。比如,我们应该如何去讨论那些庞大的事物,并认识到他们的重要性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庞大?在我的研究中,关于规模的问题经历了一个倒置(invert)的过程,因为很多庞大的问题都落到了小的微观层面的问题上。
关于生态政治学,关于“污染”的话语
另一个我尝试思考的问题是,我的研究和政治生态学(political ecology)这个领域之间是什么关系。一旦涉及到环境问题,政治生态学似乎是社会科学中默认的一个方法。我读了相关文献,同时也有一个政治生态学家在我的博士委员会里。我有时候喜欢政治生态学,有时候又不喜欢。在这本书的很多个章节里,我都在试图搞明白为什么(我对其是这种分裂的态度)。政治生态学往往提供一种很清晰的叙述方式:国家政府参与进来了,提供了由市场逻辑引导的动力机制,而这种运作又适用于其他很多地方,等等。
当我跟别人描述我的课题时,他们会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接着说:“哦,所以你是研究污染问题的?”或许吧。但这更多是一个季节性的问题(如沙尘暴),是与政治经济的运作密切相关的问题。这也回到了关于物质的思考。当你研究的物质是一种悬浮微粒(aerosol),你如何确立你对于能动性的定义和理解 —— 不仅是物质的能动性,还有尝试解决这个物质的政治系统的能动性。我想要有一个不同于“污染”的词来帮助我思考。否则,一旦说到污染,你很容易就被框定在预设好的论点中。我想做的是与之不同的研究。在这两百多页的写作中,我想探索一些没有被预设的事物。
关于本书的未来(与知识生产)
关于这本书是否将过时的问题……欢迎!我是说,如果这本书能起到什么帮助,那对我来说真的很棒。这个问题上我想到最多的人是罗丽莎(Lisa Rofel),她对中国语境下的欲望/渴求(desire)问题做了很多的理论化探索。她是我的导师之一,也帮我一起研习、改进了这本书。我最开始把手稿给她看的时候,特别紧张,但是她跟我提了很多建议,其中包括:“我的研究显然是在你的研究的背景之中的!”我想,这是成为别人的导师才会获得的惊喜。你会看到自己写的东西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启发甚至塑造了其他人的思考。我自己的这本书,现在或许是重要的,但如果有人读了之后,探索出了一种富有创造力的方法去推翻它,我会非常感恩。这是一件很酷的事情,不是吗?我反而不明白为什么会一些人花费上漫长的几十年来捍卫自己的作品,认为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给我五年时间,五年之后,你就可以说,这本书真烂![全场笑]毕竟我还是非常费了好大的功夫的。
延伸阅读
Bennett, Jane. 2020. Influx and Efflux: Writing Up with Walt Whitma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Callison, Candis. 2014. How Climate Change Comes to Matter: The Communal Life of Fact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De la Cadena, Marisol. 2015. Earth Beings: Ecologies of Practice Across Andean World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Rofel, Lisa. 2007. Desiring China: Experiments in Neoliberalism, Sexuality, and Public Cultur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Tsing, Anna Lowenhaupt. 2015. The Mushroom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On the Possibility of Life in Capitalist Rui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作者简介】
徐庄骅(Jerry Chuang-Hwa Zee),普林斯顿大学人类学系助理教授、高草甸环境研究所研究员,研究兴趣涉及环境人类学、女性主义科技、中国文化和政治人类学;政治生态学、气象学和空气、治理、工程、美学、物质主义。文章见于American Anthropologist,Cultural Anthropology, HAU等期刊。
【译者简介】
倪燕萍,普林斯顿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生。研究兴趣:物质、空间、生态。见刊于China Information, Asian Bioethics Review。
相关阅读
最新文章(持续更新)
风沙卷起大国:徐庄骅(Jerry Zee)新书分享会笔记
欢迎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保持联系
独立网站:tyingknots.net
微信公众号 ID:tying_knots
成为小结的微信好友:tyingknots2020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