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9|中东史的环境转向
我们所寓居的世界既是社会的,也是自然的,二者揉杂交织,共同塑造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然而,人文社科在过去很长时间内,都未对这种混杂性给予足够的重视。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法国一批著名史学家共同创办了《历史与社会科学年鉴》(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以人类与自然地理的交互作为切入点,研究历史发展过程。在英语中,“环境”(environment)一词并非现代创制,但将其推向政策和知识关注中心的,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主导者则是科学家或有科学训练背景的学者。
生态学家威廉·沃格特(William Vogt)在其1948年著作《生存之路》中写道,“在生态意义或者说环境意义上,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这句虽预兆了九十年代以来流行的全球化话语(“同一个世界”),但在提出的当时,其关注的视角却是“环境”——包括人口增长、土壤侵蚀、荒漠化、污染、食物安全、贫困、饥饿。及至六七十年代,随着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于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以及其它作品持续发酵,更多人文社科学者的研究和作品中开始出现了“环境转向”。
根据已故的环境史学家琳达·纳什 (Linda Nash)于2013年的总结,历史学科中的“环境转向”既受到自身学科的传承影响,更在过去二三十年中,深受科学技术和社会研究(STS)与女性主义理论的浸润。譬如,人类学家唐娜·哈拉维 (Donna J. Haraway)对灵长类生物学的研究,揭示了以动物为研究对象的生物科学研究中存在着各种性别化、 种族化的话语和范式,从而也批判了启蒙时期以来对科学理性和客观性的欧洲白人-男性社会的体制性偏见。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也进一步为人文社科学者提供了新的词汇库,打破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的边界。
尽管如此,真正全球意义上的“环境转向”还远远未完,或者说,还只是起步阶段。以上总结基本还是以全球北方为中心,而支撑其不断自我复制的除了其理论体系、逻辑法则,还有建立在全球殖民历史上的当代经济体系。我们需要从全球南方的视角出发,不断审视在地的演变,通过“环境转向”,帮助我们去看到中东、东亚、南亚、中亚、拉美、非洲等地域之间历史性、跨区域的联系。
本文正是从“环境转向“和对欧美中心主义的反思出发,评述了发表于2010年至2015年的五本中东史方向的著作。正如评议者乔治·R. 特朗布尔四世(George R. Trumbull IV)所说,这些作品“的丰富与成功,证明了中东环境史研究的活力”,它们“既无意建设一个狭隘孤立的历史学分支,也无意提供一系列封闭的对话……相反,它们重新激活了那些讨论,重新界定了那些问题,并挑战了中东史领域内许多论证的核心假设。”
本文评述的书籍列表如下(按照文中出现顺序排名):
努克赫特·瓦利克(Nukhet Varlik):《早期现代地中海世界的瘟疫与帝国:奥斯曼的经验,1347-1600》(Plague and Empire in the Early Modern Mediterranean World: The Ottoman Experience, 1347-160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
山姆·怀特(Sam White),《早期现代奥斯曼帝国中叛乱的气候》(The Climate of Rebellion in the Early Modern Ottoman Empir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
阿兰·米哈伊尔(Alan Mikhail) ,《奥斯曼埃及帝国的自然与帝国》(Nature and Empire in Ottoman Egypt),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
阿兰·米哈伊尔,《奥斯曼埃及的动物》(The Animal in the Ottoman Egypt),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
托比·琼斯(Toby Jones) ,《沙漠王国:石油和水是如何塑造现代沙特的》(Desert Kindom: How Oil and Water Forged Modern Saudi Arabi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原文作者 / 乔治·R. 特朗布尔四世(George R. Trumbull IV)
原文出处 / 《国际中东研究学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49 :173-180页。
原文发布时间 / 2017年
译者 / 王立秋
编者 / 王菁
原文發布时间 / 2022年5月3日
01. 序言
如果说与在其他领域的历史学家相比,研究中东的历史学家把注意力转向环境要晚很多的话,那么,最近出版的一批著作则表明,新一代的学者,也在这些地方的环境史上花了不少时间。
本文评论的这些书的一大特征在于,它们都坚持把中东的环境同时当作:(1)生态的事实和(2)再现的空间来考察。这些书一致表明环境史在中东史这个领域的活力。而且,它们对方法论的关注和对各种资料来源的创造性使用,也为以环境的管理和再现为中介来进行,并为政治、文化和宗教的新研究开启了空间。
紧接着戴安娜·K.戴维斯 、埃德蒙·伯克三世等人最近的工作,这些历史学家收集和整理了大量的环境的、气候学的、流行病学的、生物学的和地理学的数据来支持历史学的论证。因此,在最终完成的作品中,他们都深陷于各自的史学叙事之中,但同时,他们也打断、重述、动摇了那些叙事的假设。
因此,在最好的情况下,所谓的中东史的“环境转向”代表的,并不是一种学术时髦,而毋宁说是一个重大的方法论转向,这个转向将重塑我们理解这个领域之形成的框架。
02. 瘟疫与帝国
早期现代环境史特别繁荣。在费尔南·布罗代尔的长影下,研究欧洲及欧洲早期现代帝国的历史学家们已经详尽阐述了国家形成和帝国形成的环境基础。奥斯曼史也受益于它为补充和修正早期现代世界的全球环境图景而进行的,向关于帝国形成的比较研究的转向。
在这里评论的四本书中,努克赫特·瓦利克、山姆·怀特和阿兰·米哈伊尔都把奥斯曼的环境史描述为既是地方的、又是全球的:小社群和更大的城市里发生的环境政策及变化,都反映了帝国内部、以及作为一个整体早期现代地中海世界内部的更大的模式。
瓦利克的《早期现代地中海世界的瘟疫与帝国:奥斯曼的经验,1347-1600》从长时段追溯了黑死病的历史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作者认为,因为在关于奥斯曼帝国的研究中相对处于边缘的位置,瘟疫史作为一个整体,在很大程度上只反映了欧洲人(特别是基督徒)对瘟疫的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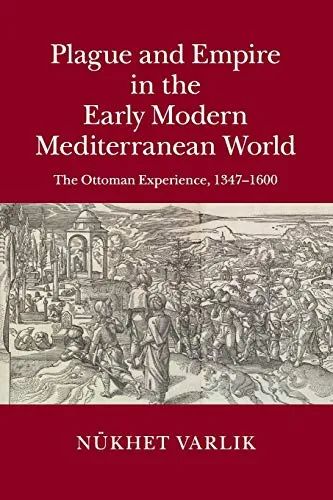
努克赫特·瓦利克(Nukhet Varlik):《早期现代地中海世界的瘟疫与帝国:奥斯曼的经验,1347-1600》(Plague and Empire in the Early Modern Mediterranean World: The Ottoman Experience, 1347-160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她解释说,特别地,奥斯曼对瘟疫及其后果的理解,就表明,“奥斯曼帝国的成长,与流行瘟疫的蔓延,是密切交织在一起的。”早期现代奥斯曼史专注的那些问题——集权化、扩张、伊斯坦布尔与外省的关系——也正是以那些因素(那些促进瘟疫传播,但也是随瘟疫的道德性及其恐怖决定的轮廓而来的因素)为中心的。
因此,瓦利克并非简单地把瘟疫插入到奥斯曼史学已经确定好的轮廓中去。相反,《瘟疫与帝国》从根本上翻转了我们对奥斯曼帝国的形成与扩张的影响。瓦利克所谓的“瘟疫网”和随后而来的人口变动必然——就像她本人充分证明的那样——形成对帝国中的政治和社会网络的新理解的基础。
这一创新直接出自于瓦利克成熟的论证方法。她深入地思考了奥斯曼关于瘟疫的认识论,这些认识论在档案中的反映,以及疾病的生活经验。“与把更多的瘟疫vs更好的记录定位为”一个史学的启发式的(以及从根本上说无法解决的)问题相反,她强调,有利于更好地记录的那同一个网络,也传播了瘟疫。
她中肯地解释说,与先前的种种解释相反,早期奥斯曼历史记录中瘟疫的“阙如”与其说是档案上的空白,不如说更多地是认识论上的空白:她的史料使她能够追踪作为一个理解范畴,而不是一个现象的瘟疫的出现。很简单,疾病在具体化为某种特定形式的疾病之前,当然是不存在的。“史料很少提到瘟疫且几乎没有任何关于瘟疫的描述……是一种理解瘟疫的思维模式的产物。”这一论断提出了关于更加广泛的,对奥斯曼认识论的历史理解的重要而有趣的问题。
对瘟疫的构想的改变,也会引起对瘟疫的不同经验。与瘟疫相关的灵修实践的集中化,是依照我们熟悉的奥斯曼的巩固和规范化的模式来进行的,但它也反映了瓦利克所谓的,瘟疫作为(无人居住的)安纳托利亚的风景,和越来越要命的城市风景的一部分的“自然化”。作为一系列网络、和一系列中介性的社会与政治关系,奥斯曼帝国既传播了瘟疫,又是瘟疫传播的结果。《瘟疫与帝国》不仅矫正了奥斯曼帝国在黑死病史上的阙如,还从根本上重构了我们对帝国的形成与功能(通过疾病的各种经验与其后的人口移动)的历史理解。
03. 叛乱的气候
山姆·怀特的《早期现代奥斯曼帝国中叛乱的气候》做了一件类似的,但也许,野心没那么大的工作。怀特把帝国放到早期现代的更广泛的语境——小冰期——中去看,并把这个重大的气候学的干扰,读进了对奥斯曼世界的史学理解。
气候学的变化及其后的饥荒、国家供给系统的失败及叛乱戏剧性地改变了奥斯曼的历史进程。“环境进路”,怀特认为,“为奥斯曼的危机和转变提供了最自洽的、也是最有解释力的范式。在不诉诸像‘衰落’和‘去中心化’那样的模糊概念的情况下,它实际上论述了为什么以及何以十六世纪的高速增长会戛然而止……以及为什么帝国在接下来的那个世纪里会遭受这样巨大的挫折”(p.226)。人口的衰减、城市化、城市死亡率的上升、和叛乱都是随小冰期而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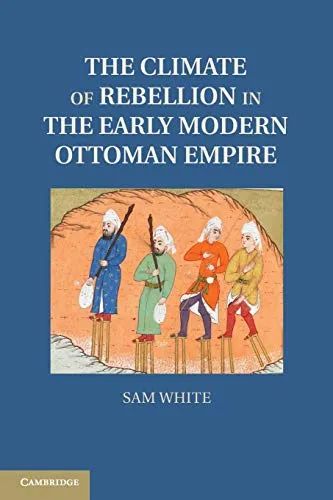
山姆·怀特(Sam White),《早期现代奥斯曼帝国中叛乱的气候》(The Climate of Rebellion in the Early Modern Ottoman Empir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怀特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奥斯曼在处理杰拉里叛乱上的成功,是如何使那些在其他地方,引起更多对政治秩序的冲击的政治形式固化下来的。而且,小冰期也通过促使政府重新组织土地归属和供给,而促成了一种向出口导向的经济的转型。
怀特充分证明了,小冰期的旱灾、饥荒和叛乱,再造了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契约,“不仅促进了供给系统的崩溃,也打破了那个含蓄的、把reaya(民众、被统治阶层)和帝国征服绑在一起的正义之圈”。面对兽疫、饥饿和长期的动乱,“reaya没有理由在像和平时期的纳税人一样为苏丹服务了”。小冰期也再造了个体与土地的关系,但怀特海说明了它更加惊人的,对纳税人与帝国之间的联系的重构。
同时发生的人口统计学上的变化,要求我们进一步从奥斯曼臣民和政府的角度来重新思考那些关系。环境的改变不仅导致了游牧生活的复兴,也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正如瓦利克指出的那样,城市变成了存放尸骨的地方。“到十九世纪的时候”,怀特称,“很可能有数百万人死于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和瓦利克的“瘟疫网”放到一起来看,这种看法邀请我们来进一步思考,是什么构成了奥斯曼帝国中的城与乡、中心和边陲。这两位作者指出,瘟疫的网络和载体,也是更加宽泛运动和交换的网络和载体,要求一种更加深刻的年代学和地理学。
尽管《叛乱的气候》在把小冰期解读为奥斯曼史的一部分上做的相当出色,但怀特时不时地也会发明一些史学稻草人,与它们争论。他的材料的确“说明了,饥荒后接踵而来的绝望情绪,在生态与经济的压力下,为[杰拉里]叛乱的火焰提供了燃料”,但没有一个严肃的奥斯曼帝国史学者会反驳这样的论证,就算学者们把这个工作交给了怀特,这也不意味着,他们就不会持同样的看法。
怀特对早期现代帝国失序的环境的解读,与其说改变了,不如说是补充了我们对那个时期的理解。他正确地坚持“把十七世纪帝国的问题都归咎于旧制度的衰落或新兴的欧洲的挑战这种做法不再可行了”,但研究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学家们早就抛弃了对帝国的“衰落”及其延续的简单化的理解了。怀特填补了奥斯曼史学中的一大空白,并进一步加强了一个关于帝国在长时段里经历的变革的性质的、逐渐浮现的共识。《叛乱的气候》把环境危机及对此危机的回应放进了关于奥斯曼帝国变革的、已然丰富的史学。
04. 自然与帝国
阿兰·米哈伊尔一直通过撰写专著、编辑文集和发表文章,在环境史领域辛勤耕耘。《奥斯曼埃及的自然与帝国》重写了那个以开罗为中心,取代了穆罕默德·阿里帕夏之前的奥斯曼时期的那个松散政府的,更加集权化的政权的形成。
此前,学者们已经就埃及通过官僚化进程、融入世界经济、和形形色色的社会与政治改革完成的“现代化”——特别是在十九世纪——展开了全面的研究。然而,米哈伊尔则用他对(该政权)十八、十九世纪环境实践的分析,扩大了了这个年表。他把埃及的现代化一直追溯到了十八世纪,“一个更加集权化和威权主义的多的管控环境资源的政权”的引入,并在此过程中指出,其他学者所谓的“现代”埃及的集权化和官僚化发生的时间比他们认为的要早,而且是发生在出乎他们预料的地方。

阿兰·米哈伊尔(Alan Mikhail) ,《奥斯曼埃及帝国的自然与帝国》(Nature and Empire in Ottoman Egypt),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地方知识、对使用的管制、以及冲突解决机制,都让位于一个汲取能力日益上升的中央政府。官僚制的扩张,对埃及环境的压力日益增加,并使农民变得边缘化,甚至把他们变得一无所有。
和瓦利克与怀特一样,米哈伊尔的目标也是揶揄奥斯曼史的“衰落理论”。他把这个理论替换为“两个互相关联的衰落……第一个是埃及农民的生命与生活水准的缩短、下降……第二个……则是对埃及农村环境的持续使用的稳定侵蚀”。米哈伊尔这么说不仅仅是在玩史学的文字游戏。相反,他对农村环境系统的损坏的透彻说明,纠正了一种经常隐含着胜利主义的诗学,这种史学赞美埃及中央权威的出现,认为它是埃及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必要的一步。米哈伊尔,相反,则认为权威是专制的、汲取性质的,它更多地扎根于帝国命令形式的重新整顿,而非现代的治国之书。
米哈伊尔把各种形式的环境管理放到了这个重新整顿的核心。奥斯曼帝国把水的使用(特别是水利灌溉)权分给埃及的fellahin(农夫,务农的人),这件事情反映了一种既有效、又在环境上说合乎逻辑的政治实践。埃及农民的知识、劳动和意愿使帝国能够有效地利用该区域稀缺的水资源。结果,埃及的食物生产供养了大半个帝国,但它也要求几乎于源源不断的,木材与水资源的输入。木材被用来造船以运输粮食,供水系统则是用来防止海水的渗入。
然而,在默罕穆德·阿里的统治下,切断埃及与奥斯曼帝国木材资源之间的联系这一举动,重构了国家与个体环境行动者的联系。于是就有了大规模的植树计划,顽抗的农民则遭到了严厉的处罚。穆罕默德·阿里的埃及要求农村劳动者发挥的功能,与其说是当地环境的管理者的功能,不如说是受管制的、严格遵守规定的劳动者的作用,他们被要求生产特定数量的特定商品,而无论这样的生产是否可持续。“以奥斯曼的行政为代价的,集权化的、垄断埃及政治权力的一切努力,都导致了对埃及农民的巨大要求”,并不断地侵蚀、破坏他们对环境世界的控制。
学者们已经全面地说明了,埃及与奥斯曼帝国的持续分离、其在集权化方向上的努力、及其不断增长的对食物和农产品及木材的需求,再造了埃及政权与埃及农民的关系。米哈伊尔推翻了“埃及史的民族主义叙事”,这种叙事认为“随着与奥斯曼帝国的进一步分离,现代性也来到了埃及”。与再现地方、即埃及和埃及“民族”不断增长的,对劳动与资源的控制相反,这些变化开启了一种越来越集权化的、越来越威权主义的、越来越汲取式的,对劳动和环境的使用,一种来自开罗的更加严厉的控制,而非来自伊斯坦布尔的更加入侵式的控制。
米哈伊尔证明了,奥斯曼帝国的官僚在很大程度上是允许埃及农民管理自己的环境的,而在阿里的埃及变得越来越自主的同时,也在严格地限制地方的自治,并让农民,像他们的动物一样,进行强迫劳动——这是一种近乎于福柯式的统制、管制和组织。这样的管制水、食物、劳动和身体的模式,在集中的欧洲帝国的管理到来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它们是出自于由埃及自主而带来的那个集权化的过程的。
于是,普遍意义上的身体,而不仅仅是劳动者的身体,成为了国家干预的场所。米哈伊尔认为,在穆罕默德·阿里的统治和欧洲顾问的影响下,瘟疫也从埃及的生活与环境的一个自然特征,变成了一个需要从欧洲帝国借鉴管理技术,也即通过暴力来强制执行的隔离,来处理的问题。
米哈伊尔关于隔离的论述,构成了对南希·加拉格尔(Nancy Gallagher)的经典《突尼斯的医学与权力,1780-1900》(Medicine and Power in Tunisia, 1780-19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的有趣的补充,这两部作品一起说明了欧洲的医学,和新兴的、支配北非不同区域的帝国威胁之间的各种关系。把突尼斯对隔离的只是偶尔的、部分的接受,与埃及对隔离的严格执行放到一起来看,我们会发现,这些政权的相对的“集权化”既是从这些实践中浮现出来的,同时确切地说,也是被这些实践给生产出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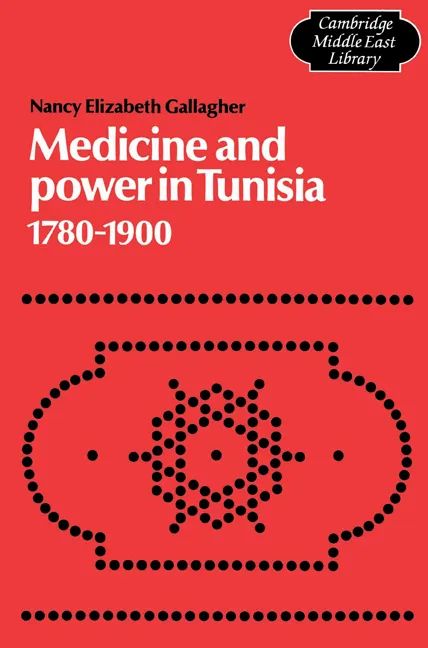
南希·加拉格尔(Nancy Gallagher),《突尼斯的医学与权力,1780-1900》(Medicine and Power in Tunisia, 1780-19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当然,对于这个新生的、集权化的埃及政权来说,尼罗河才是最大的对环境、农业、劳动力与官僚的挑战。人们曾试图通过马哈茂迪耶(阿什拉菲亚)运河给亚历山大里亚供水,并把它改造为现代国家的中心。为了解渴,奥斯曼人在十八世纪末试图开凿各种运河。在这些工程紧锣密鼓地进行的同时,大量的农村劳动者也被迫到那些条件极差的施工地点去工作。
米哈伊尔指出,在运河的开凿过程中,一共死了十万人,占当时埃及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在很大程度上说,运河并没有减轻亚历山大里亚的饮水问题,或者说,它还在运河沿岸创造了新的、繁生的定居点。米哈伊尔认为,运河的遗产,不在于其成效,而在于其野心和付出的代价。埃及政权成功地创造了一个专制的、威权主义的命令系统,这个系统以标榜此举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好的名义,无视了为此而付出巨大的人力、生命代价。农民劳动者变成了另一种可消耗的资源。
《自然与帝国》推翻了奥斯曼政治史中的许多史学范式。米哈伊尔以地方(主要是农村)为焦点的视角,消解了中心与边陲,或下至一系列更加微妙得多的,对带来大规模影响的,偶然的、地方的关系和变革的描述的宏观问题。那些创造出集权化的、经常是专制的、汲取的埃及政权的变化,首先是在奥斯曼时期出现的,并在后来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呢。环境管理及环境管理的失败创造了后来的埃及。
05. 帝国的动物
《自然与帝国》和《奥斯曼埃及的动物》形成了一幅双联画,一个由两部分构成的,对埃及管制性政权的形成的研究。人与动物之间的密切互动的变化,反映了一种管制身体的基础设施,和一个管理那个基础设施的政权的出现。和学校、军队、劳动者的身体和健康一样,动物,也提供了追溯国家控制史的理想场所。
米哈伊尔把动物视为那个后来波及人的进程的先声。“就像十九世纪初,牲口、狗、大象被剥夺了它们建构性的社会与经济功能那样,十九世纪末,埃及的农民、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残疾人、穷人、病人、罪犯和流动人口,也被切除到埃及生产性的社会与经济领域之外了”。埃及的动物不仅是一个隐喻,更起到了试验对象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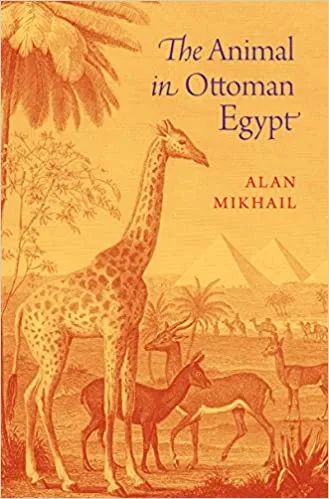
阿兰·米哈伊尔,《奥斯曼埃及的动物》(The Animal in the Ottoman Egypt),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牲口即财富这一概念定义了米哈伊尔所为的“早期现代的人与动物”。在十九世纪,埃及经济向出口生产的转型,使土地代替动物成为财富的单位,并使人的身体代替动物的身体成为劳动力的单位。随着土地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动物在瘟疫中大量死去,以及人类劳动力的大量涌现,使人的身体成为农业社会的基本功能单位。没有动物的穷人难以耕种自己的土地,并因此而变成劳动力,在政治上越发的边缘化,也越发地赤贫。牲畜与财富的分离,预示着赤贫的农民与土地和权力的分离。在追踪牲畜所扮演的角色的变化的同时,米哈伊尔也凸显了埃及经济剧变带来的日常的、在地的影响。
尽管扮演着牧羊者、朋友、战友和(很多人会为此而感到失望)废物处理者的角色,狗,也成为了新出现的管制国家管理的对象。与城市生活有用的助手相反,在十九世纪的埃及,狗被认为是失序与不洁的标志。米哈伊尔论证道,主导狗-人关系的,不再是情感而是效用,但在国家坚持管制埃及生活的更多方面的同时,狗(特别是野狗)也变成了需要管制的对象。开罗的除狗行动不过是加剧了垃圾问题而已,但从官僚的角度来看,这一举措也创造出一个更加干净、守序的城市。再一次地,一系列针对动物的控制技术,在后来,又延伸、应用到流浪汉、病人或有害的人身上了。
最终,米哈伊尔转而把注意力集中到那些有超凡魅力的动物之上。这里,一样的,国家对之前被认为是地方行动者自己的事情的各种事务的不断扩大、加深的控制,也引起了对这些动物的管制。
珍奇动物的贸易则见证了这个过程:苏丹的伟大与神秘(狮子、大象),让位给了动物园的正规化的逻辑,而动物的国际贸易本身,看起来也带来了引进动物流行病的危险。曾经,狮子是帝王威严的化身,而如今,珍奇动物越来越成为正规化的贸易品,被卖到奥斯曼帝国之外,以满足那里的人们的好奇心。米哈伊尔所谓的动物的“笼装”又把这些动物放到了商业和商品的关系之中,并且确定无疑地,把这些动物移出了超凡魅力的领域。
《动物》的核心论证是:“在奥斯曼埃及,发生在动物身上的事情,不久之后也在人身上发生”。米哈伊尔因此拓展了我们对埃及的管制的出现的理解,并且,就像在《自然与帝国》中那样,他也对此过程的年代学发起了质问。就像从更加有益的角度来说,在英国,先有了对虐待动物的限制,才有了儿童权利的概念那样,在埃及,对动物的管制,也预示着对人类身体的越来越多的控制。
通过坚持严肃对待不断变化的人与动物的密切联系、并阐明被用来控制动物与人的那些共通的技术,《动物》为未来中东史中关于动物的研究指明了道路。比如说,看起来,是时候对城市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伊斯兰城市中,围绕宰牲而出现的管制装置做一番研究了。
06. 沙漠、石油和水
与米哈伊尔类似,托比·琼斯也是为了概述政治形式的创造过程,才转向环境史的,在琼斯这里,他还就此进行了争论。琼斯的里程碑式的著作《沙漠王国:石油与水是如何塑造现代沙特的》不仅展示了何以环境管理及环境管理的失败是沙特治国方略的核心,还展示了何以我们可以用环境史来阐明政权最隐晦的一面。
沙特意识形态的发展及其表达,什叶派运动的出现及其后来受到的压迫,以及是有政治复合体的操纵,依然——按沙特王国的设计——是难以研究的课题,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当前的状况入手。《沙漠王国》提供了一种对这些问题的范例式的分析,同时也为未来的研究指出了一种有前景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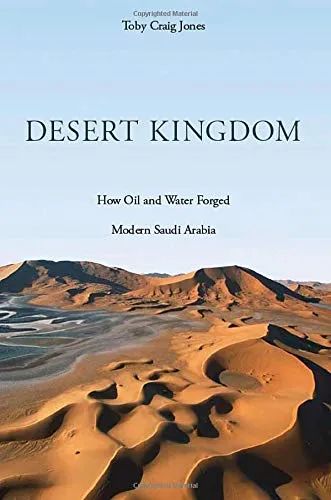
托比·琼斯(Toby Jones) ,《沙漠王国:石油和水是如何塑造现代沙特的》(Desert Kindom: How Oil and Water Forged Modern Saudi Arabi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琼斯认为,对水、石油和环境的管理,是沙特奉行的那套支撑其威权主义政权(特别是在经济方面),并使什叶派和其他与王室没有密切联系的派系边缘化的治国方略的一部分。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科学的知识及实践——无论是水理学的还是地质学的——一直是沙特合法性的一个关键指标,它把沙特塑造为一个现代的、提供社会进步的恩主和供给者,而非一个前现代的、威权主义的君主国。
尽管石油经济的诞生为促进科技进步的投资提供了收入和理由,但沙特对科学的投资,却早于石油的发现。美国的地质学家就曾为寻找有用的地下资源而咨询过沙特王国。因此,琼斯指出,科学的知识,技术的进步,和财富的前景,构成了沙特王国政治语言的一部分,使它能够合法地宣示自己的主权,并合法地控制这个国家。在这方面,沙特绝非孤例;战间期,类似的实践在殖民政权那里可以说是遍地开花——特别是撒哈拉的法国殖民政府。控制了科学知识——甚至在石油之前——就意味着控制了那片土地本身。不过,后来,“政权……用去政治化的科学语言,来为它对臣民生活的日益入侵辩护”。
在沙特王国及其他类似的地方,二十世纪科学话语(这种话语使得政权可以声称自己在政治上是中立的)的创造,不过是促进了政权把它当作手段,来服务自己的政治目的罢了。地方的技术现代化、水利控制、工业环境管理计划,也是关联臣民与政权的手段,这意味着,政权可以在绝口不提实际参政权的情况下,获得臣民的忠诚。
而且,正如琼斯仔细地证明的那样,同为沙特治国政治计划的一部分的,发展的福音主义,与伊斯兰的核心地位,二者之间并不冲突。相反,作为合法性标志的它们还会彼此强化。二者的目标都在于:一方面,促进(臣民)与政权的整合;另一方面,促进(臣民)对政权的依赖。在沙特的技术官僚心里,这两方面是连在一起的。那些被自己的牲口绑在土地(在沙特,土地大多是集中的)上的人开始对国家的计划产生需求,并且认为这样的计划当然需要强政府。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管理变成了这个政权的核心任务之一,臣民指望着它们,并认为它们是政治体制的一部分。
琼斯也概述了相应地,那些臣民放弃了什么。发展计划和意识形态起到了公开形象的作用,它们掩饰的,是政权为维持稳定而打造的一整套侵入臣民生活的监控系统。在桀骜不驯的贝都因人侵扰阿美石油公司设施的时候,沙特政府的应对方式是建农场。当1962年,一些沙特人表现出宗教和政治异见迹象的时候,费萨尔国王马上加大了发展计划的力度(第三章)。这样的发展要求管理、监控和问责。在默许地方对水或有效的水井的要求的同时,沙特也在试图以此来确保地方的忠诚,为对地方的监控提供理由。
富有石油和水的东部省份吸引了沙特发展的大部分的、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断断续续的关注。琼斯令人信服地展示了,在很大程度上说失败了的、再造哈萨(al-Hasa)绿洲的努力带来的后果,以及,越来越紧张的石油经济是如何加剧外省什叶派与中央权威之间的张力的。
创富(对少数精英来说)、发展和瓦哈比派伊斯兰,这个三分体(沙特家族的政治合法性便依赖于此)在很大程度上把广大什叶派人口排除了出去。的确,什叶派活动家早就开始呼吁变革了,他们请求政府更好地管理石油工业对环境的破坏,更公平地分配石油财富。琼斯正确地把这些要求诠释为“一种新的沙特公民权、和一个新的沙特民族/国家的条款”。然而,这些活动家的假设——他们认为利雅得会为一个更加公平的民族/国家而牺牲之前打造好的王国——是错误的。什叶派进一步的边缘化使其他活动家开始疏远沙特政权并变得激进化,这一过程的顶点就是1979年的叛乱和沙特政府对这场叛乱的残酷镇压。琼斯强调了这场暴动的复合特征(参与暴动的既有宗教人士也有左派人士),并正确地认为,在这场暴动中,来自德黑兰的外部影响并不那么重要。他认为,这场叛乱导致的结果,是沙特王国的主导意识形态开始远离发展,而向伊斯兰回归。瓦哈比派、忠诚与权威,构成了1979年后沙特政治意识形态的主干。
在他撰写这部沙特石油与水的环境史中,琼斯也提供了对沙特政权不断变化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全面描述。为从各种计划和风景中找出政治史,他熟练地克服了在档案上重建沙特政策辩论的各种挑战。在没有合法的政治文化可供研究的情况下,琼恩从各种物理和环境的踪迹,证出了政治的工程,并通过这些政治工程,发掘出过去沙特政局的紧张——过去的学者们,都没有怀疑过沙特竟然曾经出现过这样的紧张局面。这样熟练、充满创造性、且有深入研究的政治史,应该成为对重建威权政权中不通过这样的研究就发不出声音的政治形式感兴趣的学者的方法论上模范,无论他们想研究的是卡扎菲的利比亚,还是沙特王国。
尾声
本文评论的这些作品的丰富与成功,证明了中东环境史研究的活力。这些在方法上有所创新、研究细致(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且擅长在细节处着力)、且精于诠释的著作,都致力于理解人类历史的自然参数。
不过,它们既无意建设一个狭隘孤立的历史学分支,也无意提供一系列封闭的对话。它们也没有回避各自史学框架内的其他重大问题。相反,它们重新激活了那些讨论,重新界定了那些问题,并挑战了中东史领域内许多论证的核心假设。
每一部作品——作为环境史——的成功,无疑都会大大丰富关于中东与北非的文献(目前,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依然匮乏)。任何对政权形成和集权化问题感兴趣的、以任何区域的研究对象的、从事环境史研究的历史学家都会发现这些作品从比较的角度来看非常有用。研究中东的学者——甚至那些自己的研究与自然世界无关的学者——也会在这些作品中得到启示,从而更好地理解中东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各种基本要素的形成与功能。
【作者简介】
乔治·R. 特朗布尔四世(George R. Trumbull IV),目前担任达特茅斯学院的历史学副教授。他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在耶鲁大学获得硕士学位、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并曾在耶鲁大学、杜兰大学、纽约大学和达特茅斯大学任教。除学术工作外,他还为各种媒体提供评论。
【译者简介】
王立秋,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比较政治学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若要转载本译文,请在本文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或者邮件联系。
注释:
1. 乔治·R.特朗布尔四世(George R. Trumbull IV),目前担任达特茅斯学院的历史学副教授。
2. 托比·C.琼斯(Toby C. Jones),美国罗格斯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专攻环境、能源与科技史研究。著有《日渐枯竭:论能源、水与环境危机》(Running Dry: Essays on Energy, Water and Environmental Crisis,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15),《美国的石油战争》(America’s Oil Wars, Harvard University, forthcoming)。
3. 阿兰·米哈伊尔(Alan Mikhail),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专攻中东、早期现代穆斯林世界、奥斯曼帝国、环境史、早期现代史、医学史研究。著有《在奥斯曼的树下:帝国、埃及与环境史》(Under Osman’s Tree: The Ottoman Empire, Egypt,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7)、《沙子上的水:中东及北非环境史》(Water on Sand: Environmental Histories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4. 努克赫特·瓦利克(Nukhet Varlik),美国罗格斯大学纽瓦克分校助理教授,专攻奥斯曼帝国、疾病史、医学史、环境史研究。著有《伊斯兰地中海的瘟疫与传染》(Plague and Contagion in the Islamic Mediteranean, Ashgate, forthcoming),《奥斯曼的医疗技艺:治疗者、病人与早期现代的国家》(The Ottoman Healing Arts: Healers, Patients, and the State in the Early Modern Era, forthcoming)。
5. 山姆·怀特(Sam White),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专攻过去的气候与天气及其在历史上的影响方面的研究。著有《冷遇:小冰期及欧洲的遭遇》(A Cold Welcome: The Little Ice Age and Europe’s Encount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6. 戴安娜·K. 戴维斯(Diana K. Davis),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历史系教授,专攻政治生态学、环境史、殖民主义、游牧社会与干旱地区、中东与北非、环境变化与公共卫生、传统医学研究。著有《发掘罗马的谷仓:环境史与法国在北非的殖民扩张》(Resurrecting the Granary of Rome: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French Colonia Expansion in North Africa,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07),《对中东和北非的环境想象》(Enviromental Imaginaries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11,与后文提到的埃德蒙·柏克三世合著),《法国在马格里布地区殖民的环境神话》(Les mythes environementaux de la colonization francaise au Maghreb, Editions Champ Vallon, 2012),《干旱地区:历史,权力,知识》(The Arid Land: History, Power, Knowledge, The MIT Press, 2016)。
7. 埃德蒙·伯克三世(Edmund Burke III),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荣休教授,专攻现代中东和北非史、地中海史、法国史、东方学、欧洲帝国主义、环境史和世界史研究。著有《摩洛哥受保护国的先声,1860-1912:殖民前抗议和抵抗的模式》(Prelude to Protectorate in Morocco, 1860-1912: Patterns of Pre-Colonial Protest and Resisitance,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76),《环境与世界史,1500-2000》(The Environment and World History, 1500-200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东方学的谱系:历史,理论,政治》(Genealogies of Orientalism: History, Theory, Politics,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8),《现代中东的斗争与幸存》(Struggle and Survival in the Modern Middle Eas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重新思考世界史:论欧洲,伊斯兰与马歇尔·G.S.霍奇森的世界史》(Rethinking World History: Essays on Europe, Islam and World History by Marshall G.S. Hodgs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全球危机与社会运动:工匠、农民、民粹主义者与世界经济》(Global Crises and Social Movements: Artisans, Peasants, Populists and the World Econom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8)和《伊斯兰,政治与社会运动》(Islam, Politics and Social Movemen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等。最新文章(持续更新)
中东史的环境转向
欢迎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保持联系
独立网站:tyingknots.net
微信公众号 ID:tying_knots
成为小结的微信好友:tyingknots2020
Like my work? Don't forget to support and clap, let me know that you are with me on the road of creation. Keep this enthusiasm togeth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