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仅20岁”时感染了HIV,我想挑战主流防艾话语
写在前面:这篇文章写在去年12月初,最初发布于706青年空间的公众号。因为需要终身服药,所以我为自己取名“药罐儿”。除去接受一位记者朋友的采访,这篇文章也是我第一次以感染者的身份面向公共空间发声,非常感激我的两位朋友在我写作前后提供建议和帮助。
2019年12月1日我度过了我的第4个世界艾滋病日。在我醒来时,就一如既往地从朋友圈的照片、订阅号的推文中感受到扑面而来的节日气氛。如今的防艾宣传已经十分普遍,尤其在世界艾滋病日左右,各方也都卯足了力气。但我认为,其中广泛使用的一些话语仍然值得商榷。
今年也是特别的一年,在它到来前,我刚好度过了确诊感染后每天按时服药的一个月。

当我亲身经历了确诊、用药和向信任的朋友出柜,过去那些零碎的思考,重又被唤起。但因为感到自身在逻辑与专业上的局限,便在约了位社工背景的朋友聊了聊。在此,便通过这篇文章对我们的讨论成果进行梳理与阐释。
"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安全性行为是防艾宣传的核心倡导,因而“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一直有相当高的“出镜率”;与此相对的,那些试图通过不戴套来获得更多性愉悦的行为,则被批评为“寻求刺激”。在公共卫生视角下,将安全视作第一位的,似乎具有天然的正义性。个体把安全作为个人价值观中发生性行为的前提、底线更无可非议。但不容忽视的是,从其它视角看待性,或许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例如,从反性骚扰的视角出发,“同意”是第一位的也完全成立。而个体因为对性不同的认知与多元的价值观,更会为“发生性行为时,什么是第一位的”提供丰富的解答。那么这些不同的视角,又有谁应当作为首要的考量?
更需要注意的是,对安全的片面强调,常与将性视为禁忌、危险的文化合流,树立起“安全”与“刺激”的二元对立。其中,遭遇贬斥的不仅是人们对情欲解放的追求,性对于个体的其它意义——构建性别身份、表达爱与亲密、找寻认同与归属、释放压力等,也都难以得到正视与讨论。
事实上,性安全和性愉悦也并非互为正反、彼此对立的存在。就如避孕手段的持续发明,为人们带来了性爱与生殖的分离,安全的保障可以让我们免于对风险的忧惧,带来情欲和身体的解放。而为我们对性愉悦的需求正名,建立对它的客观认识,也可以为安全的落实带来更多的动力。安全套的不断改进,将情趣和愉悦纳入考量的各种特殊套的出现,都是对此最好的证明。反观“寻求刺激”的批评,反而可能强化一些人“不戴套更爽”的刻板认知,变相鼓励了ta们带有侥幸心理的“越轨”实践。
"安全=负责"
“安全=负责”的防艾话语同样常见。生活中的确有很多人会因为责任意识的缺乏,在发生性行为时没有全程使用安全套。尤其在异性性行为中,女性相比男性更直接承担了意外怀孕的风险,让部分男性觉得避孕与自己无关。因此对自身与性伴侣的安全责任必须得到充分的强调。
然而,安全与负责的捆绑让我们时常架空性行为发生的具体情境,对我们身处的性别文化与情欲文化也缺乏探讨。个体的行为选择被简单粗暴地归因为道德失范,ta们的需求与境遇,以及和性伴侣之间的权力关系都常常被忽视。潘绥铭、黄盈盈和李楯在《中国艾滋病“问题”解析》一文指出,只有关注到个体行为、意识和特定社会文化里的具体情境的相互作用,我们对“高危性行为”的理解才可能具备深度与广度[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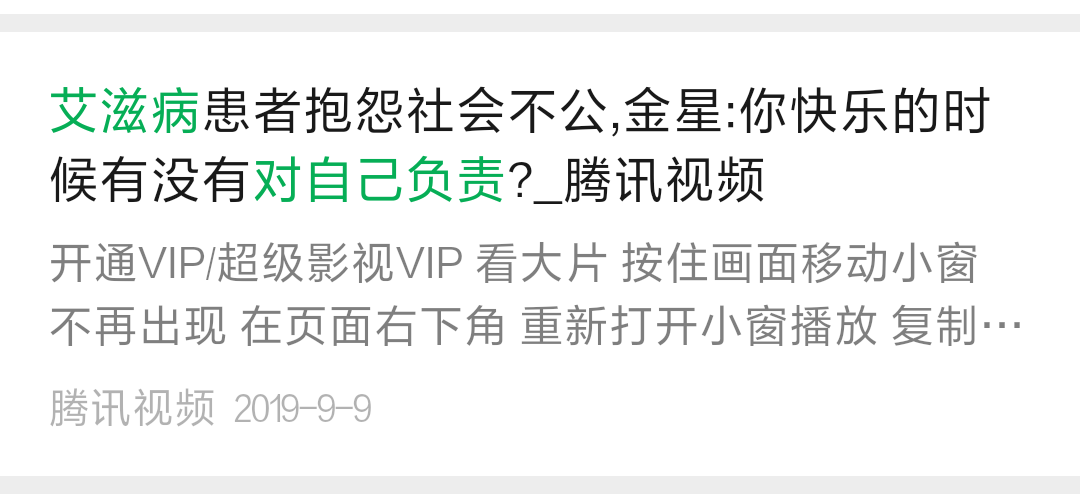
在避讳谈性的文化中,人们不仅戴套的意识淡薄,也往往并不具备“性前商议”的意识与习惯,更难以在性行为发生的过程中严肃、坦然地表达意愿。一旦其中一方提出“不戴套”的邀请,更以“爱”与“信任”为由,另一方很可能会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在实际的生活情境中,“爱”与“信任”也并非都是出于主观意图的情感绑架,要被归咎于舆论广泛诟病的“渣”和“虚伪”。当我们仅仅强调安全套避孕、防病的作用,长期的宣传中又在社会意识层面构筑起“正常人/普通人”与“艾滋病相关群体”(携带者、易感人群)的区分与隔离,确实容易造成个体对自我与性伴不论在健康还是德行上没有“缺损”的盲目相信。这样,出于疾病预防的戴套行为,反而会被视为对双方信任与“健康”“正常”的自我认同的破坏。根据张有春2009-2011年间在西南龙城市开展的社会调查,受访的性工作者表示在与客人发生关系时能够坚持戴套,但与男朋友或配偶发生性关系时则很少使用[2],或许能为以上论述提供例证。
如何面对对方的信任、撒娇、示弱与软磨硬泡,处理自我在内心的健康焦虑和道德焦虑,我们都缺少经验与思考。即时的灵活应对经常是奢侈的幻想,柴干火烈之际开展一场“戴不戴套”的辩论持久赛对于很多人来说同样难以实践。这其中不仅需要表达的技巧、应变的能力和拒绝的勇气,更加蕴含着难以应付的情感和权力层面的较量。不对等的性别权力束缚着弱势一方的性自主权,让ta们的意愿无法被真实地表达,也无法被对方认真地对待。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如何认识自身面对的责任与风险,性安全在ta的价值排序中又会被置于怎样的位置,都可能是作为旁观者所难以想象与共情的,同样也难以被“不负责任”这一道德归因所解释。
而当安全与负责的捆绑转化为感染者自身的悔恨与自责,以及外界针对ta们“自作自受”“不自尊、不自爱”的道德审判,感染所要承担的不仅是疾病本身带来的影响,更是由社会转嫁的责任与施加的羞辱。于是,艾滋病蔓延的社会问题一面被各方大肆渲染,一面又在不断与个人德行的捆绑中被囿于私人领域,最终造成的将是解决路径的曲折与防艾工作的低效[1],社会也将因此负担起更多的代价与高昂的成本。
更令我心痛的是,一些感染者对自身的反思甚至责问,那些被塑造、筛选和引以为鉴的个人书写,最终成为媒体与社群进行公众教育的经典文本。ta们并没有被视作完整的“人”,而因为健康与道德的“缺损”被作为宣传工具,成为主流防艾话语的共谋。
较为常见的就是“一次不戴套就感染”的故事。虽然出发点是希望受众减少侥幸心理,然而一旦脱离了情境和前提,这一叙述既是对受众恐艾心理的利用与强化,也会因为对故事主人公行为逻辑的简化,增加人们对感染者的误解与防艾及反歧视宣传的阻碍。
“传染”与“被传染”
此外,我们也要对“传染”与“被传染”的医学话语保持谨慎。王浩在《“有色”眼镜里的“变色”——论一个防艾研究与报道中的“七宗罪”》一文中指出:“其实每一个经过性传播的艾滋感染者都可以说是被人感染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向上追溯,于是艾滋病来自非洲等等带有价值偏见的判断一度满天飞。其实,按照这个模式,每一个艾滋感染者在被感染之前都是‘无辜’的,都是被‘坏人’传染的。于是,这样一个荒唐的逻辑出现了:艾滋病传播基本上就是坏人恶意传播坏人并继续恶意传播坏人的过程。”[3]
医学视角下,病毒传播的确存在方向,然而这一话语已被赋予更多的社会意涵。不仅是性传播,还有经常引爆舆论的职业暴露,感染双方的责任往往难以划定,背后更可能存在社会结构、管理体制与职业规范等深层的原因。然而,病毒的传播方向已经在向人们揭示,不论在道德上失范与否,最初携带病毒的人就是“原罪”。而当这种认知与其它刻板印象合流,不仅是“艾滋病来自非洲”的种族偏见,“大叔传染小鲜肉”“社会人士传染学生”的文本也都得以流传。因此,建议在防艾宣传乃至日常表达中更多使用“感染了”而不是“被传染”,避免造成对感染者的进一步污名。
“要爱不要艾”"远离艾滋病"
最后,我想聊一聊我们对艾滋病的“不要”和“远离”。当这些口号被人们高呼着,似乎我们就真的可以把它永远隔绝在自己的生活之外了。
但你有没有试想过,如果自己有一天要面临被确诊感染的可能?
前天有位朋友问我,确诊后心态这么好是不是因为之前曾想过自己会感染。突然的一问让我有些错愕,旁边的朋友也立即提醒她“谁会想过这种事呢”。然而,我在之前确实觉得“‘感染了’其实是一种可以接受、可以拥抱的状态”。不可否认,我在确诊后没有经历痛苦,是因为获得了足够的社群支持,拥有可以讲述的伙伴;虽然自己也拥有多重边缘的社会身份,却依然在不同的阶层维度享有特权。但也像一位朋友所说,“你本来对这个就比较有思考,这些年也算是有一些成果了”。
如今的心态,该是最大的成果了。

而在当下的防艾宣传中,我们千方百计地告知受众如何防艾,却没有告诉ta们存在防不胜防的万一——就像我确切地知道自己是在全程使用安全套的情况下感染的。同样,我们也很少告诉ta们一旦感染了HIV,要如何进行心理建设、获取友好的同伴支持,更极少讨论要怎样用今后一生的时间与病毒共存,如何在十来岁、二十来岁这些所谓“人生刚刚开始的时刻”就要开启坚持每天固定时间服药的日常。我们“重在预防”,也常常程式般地讲述着“艾滋病没那么可怕,如今已经成为一种可防可控的慢性病”,但很少真正体味过这句话的分量,接受它要为我们关于疾病的认知与价值观带来的变化。我们心底还在发出恐惧的尖叫,生活里仍缺少对疾病本身无所避讳的直视与探讨。我们的宣教与文化仍试图用一层薄膜的力量,固守住旧的关于“健康”与“疾病”的等级和秩序——当那些恐惧的信号借由“远离艾滋”“要爱不要艾”的话语传递,不仅会加重个体面对感染的病耻感,更可能加剧社会对感染者的歧视,在“不要”与“远离”中筑起针对感染者的社会壁垒[4]。
所以,当我成为一名新发感染者,艾滋病病毒就此让我们变成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类。也不论我们谁更注重养生和保健,谁更主动或被动地消耗着自己的身体——熬夜、吸烟、酗酒、被资本与制度奴役......艾滋病带来的“缺损”让我永远更加远离所谓“健康”的完美定义。当我接受着医院与疾控不够专业、友好的服务,在接连的盘问、训诫与惋惜中遭受凝视,最终被医学话语的霸权与人类关于健康的理想拒斥在“正常”的定义之外。
年复一年的“反歧视”,我们又立足于怎样的立场呢?
结语
朋友提醒我“批判只是手段和过程”,当我写下这篇文章,固然有混杂着委屈、愤怒的诸多不满,但也更加希望当这些问题能被看见,更加多元、更侧重赋能、更少的道德绑架、也更能让受众共情的防艾话语可以被创造。

作为行动者,我曾数次发出微弱、稚嫩的声音。如今,当我拥有新的身份,更能感受到那些随时要冲破这躯壳的倔强。我无法代表更多人,虽然从未放弃对自身特权的反思,但也难以全然挣脱个人境遇与阶层造就的局限。我亦无力改变更多的现实,但仍然寄希望于每一次拼尽全力的呐喊,愿能一直为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尊严而战。
参考资料:
[1]潘绥铭,黄盈盈,李楯.中国艾滋病“问题”解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6(01):85-95+207.
[2]张有春.艾滋病宣传教育中的恐吓策略及其危害[J].思想战线,2017,43(03):18-24.
[3]王浩.“有色”眼镜里的“变色”——论一个防艾研究与报道中的“七宗罪”.
https://mp.weixin.qq.com/s/T95eVCZf5cd4n8-f-jinCw
[4]徐若菲.高校防艾宣传活动中的隐性社会排斥与消解策略——以北京N大学为例[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9(04):91-98.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